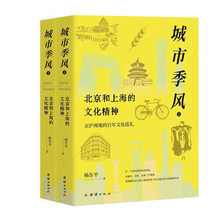罗孚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罗孚先生是香港报人、作家,但我认识他却在北京,时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间,也即他蛰居北京的第五年。
那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大概因为我已辑印了《知堂杂诗抄》(一九八七年一月岳麓书社初版),又在编选《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因此邀请我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周氏兄弟学术研讨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与会者中有罗孚先生,一位目光炯炯、笑容可掬的和蔼老人。
罗先生在会上作了《回想〈知堂回想录〉》的长篇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散会时我冒昧地提出能否会后拜访他,能否与他通信,因为我有许多关于周作人的问题要向他请教。他一口答允,并当场写下他的住址,只是告诉我,如果去信,收信人必须写“史林安”而不是“罗孚”。
其实,罗孚也好,史林安也好,对我而言,都是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我对他的辉煌的过去只略知一丁点儿,或者说一丁点儿也没有,不能说不感兴趣,但我深知,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不该说的也不必说。老人家已答应我可以写信,也可以拜访请益,夫复何求?
于是,我第二天就出现在他寓所的客厅里,也即他在《北京十年》开头几章中详细描写过的双榆树南里寓所。如果不是这次重读《北京十年》,当时室内的情景真的已不复记忆了,只记得我们一老一少,谈得很随意,也很尽兴,谈周作人、谈曹聚仁、谈叶灵凤、谈香港文坛的人和事……总之,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如沐春风,受益真的是匪浅。记得在离京返沪前,我还拜访过他一次,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他还保存着不少周作人一九六○年代的手稿,这对我编选《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不啻是个福音。但是手稿在香港,他人却在北京,不知何时可南返,我想看到这些珍贵手稿的话,只能耐心等待。
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九二年他返回香港,前后五年多时间里,我与罗先生鱼雁不断。我每次进京,只要时间允许,一定去拜访他,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不受拘束。当然,他为何在京蛰居,我始终不触及一字。他离京南返前夕,特地到上海访友叙旧,先在万航渡路原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楼前新建的宾馆下榻,后又移至柯灵先生的“工作室”小住。这段时间里,我也曾多次陪同他。罗先生知道我爱书如命,不断赠我他在北京三联以“柳苏”笔名出版的《香港,香港……》等书,尤其是他送我三大卷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毛边本,在第一集扉页上题字:“借故友著作送子善先生 罗孚 一九八八、四”,令我如获至宝。罗先生离京前一个月,我恰巧有事到京,刚走进他家门,他就埋怨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的书已有不少被别人捷足先取了,你赶快挑选需要的,再不拿就来不及了。记得我当时捧走了几乎全套的香港《博益月刊》等一大堆书刊。
那晚罗先生特地在他住所附近那家《北京十年》中提到的颇有“来头”的饭店里请我吃饭,罗先生在席间谈笑风生。虽然后来在香港我还多次受到他盛情款待,但这顿饭至今还仿佛齿颊留香。我一九九三年二月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罗先生结束“北京十年”蛰居返港刚满一年,我们在港再次重逢,倍感亲切。根据我的访学日记,在旅港三个月的时间里,与罗先生见面竟达十三四次之多,不妨摘录数则如下:
二月十四日上午访罗孚,畅谈文艺,中午罗孚宴请。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与罗孚、冯伟才见面,观罗孚所藏《药堂谈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小品和译作),大部分未发表,为意想不到之大收获。
三月二十日上午访罗孚,拍苏曼殊手迹照片,中午与吴其敏、罗孚、罗琅茶聚,与吴其敏笔谈。
四月八日晚出席新亚书院云起轩的聚餐,并听罗孚演讲。
四月十七日晚鲍耀明兄妹宴请,罗孚、罗海星夫妇、陈胜长等同席。
五月二日下午访罗孚,欣赏罗孚藏画(张善孖等)。
五月十一日晚罗孚宴请,见曹景行谈知堂致曹聚仁书信事。
五月二十八日晚常宗豪宴请,同席柯灵夫妇、罗孚等。
日记中提到的吴其敏先生、罗海星兄、常宗豪先生和柯灵先生夫妇都已经作古了。吴其敏先生也是香港前辈作家,正是罗先生的引见,我与他有此一面之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罗先生一诺千金,我终于见到了他珍藏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即《药堂谈往》)手稿和一九六○年代的著译手稿多份。《知堂回想录》手稿厚达一尺余,他沉甸甸地亲自拎到茶餐厅,让我仔细翻阅。后来他把这部珍贵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周作人一九六○年代的其他著译手稿则全部复印赠我。其时拙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早已问世,我就把手稿中还没有发表过的十余篇提供给钟叔河先生编入他的《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了。当时我写了一篇《知堂晚年佚稿》记其事,我认为罗先生精心保存周作人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对周作人研究更是“功莫大焉”。
自一九五○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借用罗先生自己在《〈香港人和事〉编者的话》中的话)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我一九九三年在香港访学时就知道《北京十年》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颇受欢迎,也拜读过其中的部分章节。以后每次到港见罗先生,都会问起《北京十年》,建议早日结集出版。而今,翘首等待多年的《北京十年》终于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经过整理的内地版也终于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付梓了,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北京十年》是一部回忆文集,虽然还未写完,但已自成系统。罗先生以连载随笔的形式记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同时不断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经历、交游和他对中国现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作为一位外来的、特殊的观察者、体验者,罗先生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现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忆录和论述已经出现不少,《北京十年》是当时情景的一份难得的实录,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罗先生这部回忆录是很值得一读的。
罗先生交游广阔,《北京十年》中记录最多最吸引人的就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来,包括访谈、聚会、酬酢和唱和等。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萧乾、周而复、启功、范用、黄永玉等,哪怕只有寥寥数笔,都是栩栩如生,音容笑貌呼之欲出。这些文坛前辈八十年代的思想、情感、个性、言谈,乃至种种有趣的细节,通过他的妙笔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存,很有研究价值。至于他以较多篇幅叙写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其人其事,在我看来,也是大有深意在矣。
罗先生的散文是别具一格的,他是香港众多散文家中引人注目的一家,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论者指出:罗先生散文“以史料的丰富和准确,见识的精当和新颖,叙述的晓畅和有趣为特点,在可读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路数上进行了尝试”(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一九九九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对《北京十年》,我以为也应作如是观,而且锋芒更为犀利,文笔更为老到了。纯净如行云流水,平实中见机智幽默,本是罗先生散文的一大特色,在《北京十年》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我一个晚上就一口气把整本书读完,那些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书、事一一生动地浮现眼前,真有爱不释手之感。
值此罗孚先生九十大寿之际,随着《北京十年》的问世,内地版《罗孚文集》出齐了,厚厚七大卷,集中展示了罗先生在文学长途上努力精进,不断反思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不仅为研究香港文学史,也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拉拉杂杂,写下了以上这些“北京十年”期间与他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往事以为贺,并祝罗先生长寿颐年,身笔双健!
二○一一年四月十八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二○一一年五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初版《北京十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