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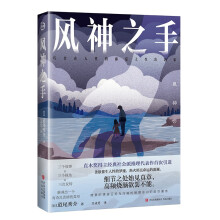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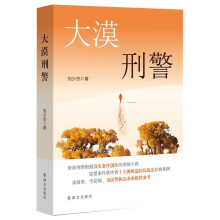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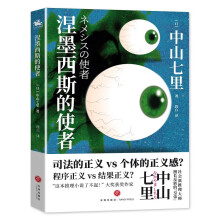
继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之后成功的英国侦探小说
英国侦探推理小说诺贝尔奖——钻石匕首奖得主
英国古典推理三大巨匠之一 当世“谋杀之王”
牛津观光的超级指南,角色与景色的完美融合
莫尔斯因严重胃溃疡住院治疗期间,意外得到了一本名为《牛津运河上的谋杀案》的小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一桩一百四十多年前的谋杀案:一位年轻妇人独自前往伦敦与丈夫团聚,在乘坐牛津运河船的途中,她遭到三名船员的无端骚扰,并最终命丧黄泉。那几名船员被法庭以谋杀罪判处死刑。
莫尔斯在阅读过程中,很快发现案子存在诸多疑点:为什么法庭最终放弃了对船员的盗窃罪和强奸罪指控?为什么那位妇人在抱怨船员对她有下流行径后仍没有弃船另择交通工具……
思想完全取决于胃口;尽管如此,那些胃口最好的人却不是最优秀的思想家。
——伏尔泰致达朗伯 的信
星期二,他感到阵阵恶心。星期三,他一直在呕吐。星期四,他一直感到恶心,不过只呕吐了几次。星期五清晨,他感到行动困难——筋疲力尽,无精打采,而且极为疲惫——他用尽力气把自己从床上拖到电话旁边,想给基德灵顿 警察局总部的上司打电话,为自己很可能无法上班道歉。现在是十一月末的一天。
星期六早晨醒来的时候,他欣喜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多了;他坐在牛津北部自己单身公寓的厨房里,穿上印着海滨浴场躺椅那种条纹的俗气睡衣,盘算着自己的胃还能不能应付一块维他麦 薄饼——就在这时候,电话响了。
“我是莫尔斯。”他说。
“早上好,长官!”(悦耳的声音!)“请您稍等一分钟,警督想和您说话。”
莫尔斯只好等待。没有其他选择,不是吗?别无选择,真的;他扫了一眼刚从狭窄门廊的投信孔里塞进来的《泰晤士报》头条——送晚了,星期六经常这样。
“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警督。”还是那个悦耳的声音——“您稍等片刻!”
莫尔斯什么也没说,可是他几乎在祈祷(这对一个低教会派 的无神论者来说是件大事)斯特兰奇赶快过来接电话,把他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把左手伸进睡衣胸前的口袋,摸索自己的手帕。
“啊!莫尔斯?是吗?啊!很遗憾听说你有点不舒服,老伙计。最近有不少人都这样,你知道。我内弟也不舒服——有多久了?——两个星期左右?不!我说错了,肯定至少有三个星期。当然,这些都无关紧要,不是吗?”
莫尔斯的额头上又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而且越来越大,他又用胳膊肘擦了擦汗,然后对着电话咕哝了几句恭敬的客气话。
“希望我刚才没有把你从床上叫起来吧?”
“没有——没有,长官。”
“很好,很好!就是觉得我应该问候你一下。呃……听着,莫尔斯!”(斯特兰奇的想法显然已经变成了结论。)“你今天不需要来上班——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说,除非你突然感到好了很多。我们这里的人手刚好能应付。墓地里都是不可或缺的人——嗯?哈!”
“谢谢您,长官。您能来电话真好——我非常感激——不过不管怎样,这个星期我正式休假——”
“真的?啊!很好!那,呃……非常好,不是吗?你有机会卧床休息。”
“可能是的,长官。”莫尔斯疲倦地说。
“你是说你起床了?”
“是的,长官!”
“那么回到床上去,莫尔斯!这样你就有机会好好休息——我是说这个周末——不是吗?只是——休息一下——当你觉得有些不舒服时——嗯?这就是医生跟我内弟说的——什么时候来着……”
随后,莫尔斯记得自己礼貌地结束了这通电话——对斯特兰奇正在调养的内弟表达了适当问候;他记得自己又用手擦了擦额头,那只手现在很湿,而且非常冰凉——用力吸了几口气——然后飞速冲向洗手间……
格林夫人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六早晨都来帮他打杂,是她拨打九九九叫了救护车。她发现自己的雇主坐在门廊里,背靠墙壁:意识清醒,还算体面,除了他的躺椅睡衣前襟的深栗色斑渍——这些斑渍的颜色和纹理都让她立即想到了咖啡过滤器底部的残渣。她非常清楚这些是什么,因为那位轻率而冷酷的医生说得非常直白——已经是五年前了——要是她当初立刻给他打电话,格林先生可能还……
“是的,没错。”她听到自己这样说——出乎意料、斩钉截铁的命令语气,“就在班布里路环岛南侧。是的,我会等您来的。”
当天上午十点一刻,略显勉强的莫尔斯屈尊被人搀进救护车后座,他穿着室内拖鞋,干净的睡裤上盖着一快让人发痒的灰色毯子,满腹狐疑地坐在一个穿制服的中年女人对面。这个女人好像认为他拒绝躺在担架床上是对她个人的侮辱,而他再次大声呕吐的时候,她绷着脸、一言不发地把肾形搪瓷碗推到他膝盖上。救护车爬上海德利路,左转驶进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建筑群的空地,最后停在事故、伤病和急诊部门口。
莫尔斯仰面躺下的时候(现在是在医院推车上)突然想到,他可能已经死过很多次了,而且没有人记录他的离去。不过他从来都不安分,特别是在宾馆里等早餐的时候;他的遐想还没有持续多久,就有个穿白大褂的护工不紧不慢地让他填写一份表格,里面的问题从近亲属的姓名(莫尔斯的情况是现在没有)到他的宗派倾向(唉,现在也没有)都有。不过,一旦完成了这些初始仪式——或者说,一旦加入了俱乐部,签署了参加表格——莫尔斯就发现自己的注意力显著提升。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位克尽职守的年轻护士,左手从上浆的硬领上取下手表,右手把住他的脉搏;用对莫尔斯来说毫无必要的蛮力把他上臂的黑色包布拉紧之后,开始测量他的血压;然后把读数认真地记录在表格里,抬头是E•莫尔斯。这种冷静好像是在说只有极端不正常的情况才值得担心。这个护士最后又把注意力转向体温。莫尔斯发现自己有些愚蠢,他躺在那里,嘴里插着体温计,随后体温计被拿了出来,护士读了刻度,读数显然不让人满意,于是她用力甩了三下——好像是乒乓球比赛里的反手推挡——又像刚才那样塞到他的舌头下面。
“我能活下来吧?”莫尔斯试着问道,护士正把更多的读数填进表格上的数据栏里。
“您有体温。”这个不善交际的年轻人回答道。
“我觉得人人都有体温。”莫尔斯咕哝道。
这时候,护士背朝着他,正在照看新到的伤员。
这是个年轻人,腿上都是泥块,身上大部分地方都裹着一件红黑条纹的橄榄球运动衫,刚被人用轮椅推了进来——额头上有一道让人不寒而栗的巨大裂口。可是莫尔斯觉得那位护工全面询问他的生活史、宗教和亲属的时候,他好像完全放松了。而那位护士用听诊器、手表和温度计测量那个年轻人体征的时候,他也显得非常轻松,莫尔斯只能羡慕这个年轻人和同样年轻的护士之间产生的亲密感。真是残酷——莫尔斯突然意识到那位同样年轻的护士已经看清了他——莫尔斯!——究竟是什么面目:历经坎坷,年届五十,即将面对疝气、痔疮和尿道感染——没错!——还有十二指肠溃疡这些有失体面的窘境。
肾形搪瓷碗放在莫尔斯伸手可及的地方。他还在剧烈干呕,可是什么也吐不出来。这时,一个年轻的实习医师(年龄只有莫尔斯的一半)走到他身旁,浏览了救护人员、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的报告。
“您有严重的肠胃问题——您意识到了吗?”
莫尔斯茫然地耸了耸肩:“还没有人告诉我任何情况。”
“但是您就算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也能察觉自己的内脏出了某些严重问题吧?”
莫尔斯正要回答,实习医师继续说道:“我想您是刚刚入院?如果您能给我们——呃,莫尔斯先生,是吗?——如果您能给我们机会,我们会尽快告诉您更多情况,好吗?”
“我没事,真的。”这位高级探长有些内疚地说,然后躺回床上,努力解开紧紧勒住肩部肌肉的衣扣。
“恐怕您不是没事!最好的情况是您得了胃溃疡,突然开始出血。”——莫尔斯突然觉得自己隔膜的某个地方猛地抽搐了一下——“最坏的情况是您得了我们说的‘穿孔性溃疡’,如果真是那样……”
“如果真是那样……?”莫尔斯小声重复。不过这位年轻医生没有立刻回答。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四处戳、压、揉莫尔斯下腹部满是脂肪的肉。
“发现什么了?”莫尔斯问道,然后淡然一笑,勉强表示歉意。
“您可以打掉一些结石。您的肝脏有些大。”
“不过我记得您刚才说的是胃!”
“哦是的,没错!您有胃出血。”
“那……那和我的肝有什么关系?”
“您喝酒喝得多吗,莫尔斯先生?”
“好吧,大多数人每天都要喝一两杯,不是吗?”
“您喝得多吗?”(同样的措辞——声音因为恼火降了半度。)
莫尔斯开始感到恐慌,他再次耸了耸肩,尽量含糊不清地说:“没错,我喜欢喝杯啤酒。”
“您每星期喝几品脱?”
“每星期?”莫尔斯尖声问道。他眉头紧锁,就像一个刚刚拿到一道需要心算乘法的复杂数学题的孩子。
“那么每天呢?”实习医师充满启发地问道。
莫尔斯在心里把实际数字除以三:“两三品脱,我估计。”
“您喝烈性酒吗?”
“偶尔。”
“您喝什么烈性酒?”
莫尔斯再次耸了耸紧绷的双肩:“威士忌——有时候我会喝一杯威士忌。”
“一整瓶威士忌您多长时间能喝完?”
“这取决于瓶子有多大。”
不过莫尔斯立刻发现自己的幽默并不受欢迎。他迅速在心里乘以三:“一星期——十天——大概有那么久。”
“您每天抽多少根烟?”
“八……十根?”莫尔斯答道。他现在掌握了窍门,轻轻松松除以三。
“您平时锻炼吗——散步、慢跑、骑自行车、壁球……”
回到乘法表之前,莫尔斯伸手取过放在手边的肾形搪瓷碗。这次他吐了出来,而在他呕吐的时候,实习医师十分警觉地观察着,咖啡渣里混杂的深红色血丝透露了实情——这些血液每天被大量尼古丁和酒精润滑着。
这些事情结束之后好一会儿,莫尔斯的头脑都有些昏沉。不过,他记得后来有个护士低头看他——还是刚才那个年轻护士。他记得她又用精心修剪过指甲的左手迅速拿出手表,然后放进手掌里。她紧锁双眉、眯眼算着半分钟脉搏数和手表上半分钟表盘之间令人不安的等式,这时候他几乎能跟上她的思路……
那一刻,莫尔斯知道死亡天使正在他的头上扇动双翼。他突然感到恐惧的战栗,这是他一生里第一次开始想到死亡。就在他的想象里,虽然只有一两秒钟,可是他觉得自己几乎看到了充满赞美的讣告——那些赞誉有加的段落。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