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跟中国南部无数个村庄的命运相似,凤凰村十室九空,人都进城了。去城市找生计,或干脆迁至城镇定居。溪流、田垌、森林、庄稼、祠堂、井台、戏台、池塘、屋巷、房舍、牛棚和猪栏,人、鸡和狗,野生的草木,野兽、蛇蛙、鸟雀和各式各样的昆虫……这一切在流失和消逝。不用多少年,人们远走他乡,村庄只剩下墓地及遗址。三十年前,尽管遭遇了难以计数的天灾人祸,村庄仍生机勃勃,一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达到了史上的繁荣。中国南部有无数个村庄跟凤凰村有相似的命运。这一切只活在我的记忆中,但也不断遭到磨损、削减并最终坠入遗忘。我在纸上建筑另一个村庄的妄想显得徒劳,但对抗遗忘的想法让人安慰。
每年三四月间,莺飞草长,春暖花开,我都返回村庄看一看。每一次,我都发现村庄少了一些东西。上次是戏台坍塌了,这次是井壁倾圮了。最让我忧惧的是,人气越来越淡了,只剩下几个老人和小孩,难得听到鸡鸣和狗吠。河流逐渐枯缺、萎缩,它干涸到几乎断流了。凭吊的意味越来越浓。
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村巷上行走,风从远处的荒山吹来,从黑屋子的角落吹来,夹着荒寂的滋味。我走到山间和田野,那种“生”的、荒凉的感觉愈来愈浓,在过去,山坡和田亩因为有人侍弄,有六畜的走动和人气养着,就显得很“熟”。每一陇柴禾都有人用镰刀去割取,每一株青草都有牛羊去啃食,每一株野果树都有人在攀摘。即使是一些杂树野木,也有孩子在攀折或挨擦,染上了人间的气息。那是一种家园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已丧失殆尽。村庄以及村边四周的山野,显得越来越生了。那种“生”的感觉,像石头郁积在我的心上,硌得我不舒服。很难说清楚,村庄是从哪一刻走向生的,当我发现村庄在不可避免地崩溃时,却悚然一惊。也正在那一刻,我才清楚它在心中的分量。我对它的了解,太过肤浅及模糊。我对村庄的历史毫无头绪,我对村名“凤凰村”之由来乃至“凤凰树”一无所知。当我想到要写它时,已是写作十八年后的事了,这也是我离开村庄的时间。在十八岁之前,“走出故乡就是最大的胜利”(叶赛宁语)成了我的信念,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好是坏,但我知道这个地方不值得留恋,不会有比这个村庄更糟糕的了。
随着年岁增长,我发现人是无法离开出生地的。你的躯体离开了,你的心仍留在那里。你会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无数次地返回那里。坐汽车是一种方式,倒提皮鞋跋涉在泥泞的小径是一种方式,做梦肯定是最常见也最直接的方式。在少年时代,我无数次通过梦境的魔法逃离村庄;有朝一日成了城里人,却一次次通过梦境回到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当你以为你离开了,其实你是将故乡带在身上,你到了哪里,故乡也跟着到了哪儿。你通过某种神奇的方法,将故乡折叠在身体的某处。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刻,尤其是半梦半醒之际,在烟雾缭绕之间,故乡就如卷轴在你的眼前展开——山水,草木,人畜,以及相关的一切。它既是一个梦幻般的画面,也是真实的图景。你走在村庄的小路上,跟来往的人说说话,也跟路过的鸡和狗打招呼。你有点兴奋,有点怅然。你就这样一次次沉湎于故乡的风与物而无力自拔。
每一个人都是出生地所孕育和养大的。这个意义对于乡村长大的人愈加凸显。尤其是在乡村长大的诗人、画家和音乐家。我朋友中就有这些人。他们跟乡村的关系恐怕更夹缠不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就像一棵在出生地长大的树木,无论成年后走到哪里,都无法带走树根。一个成年人,就像是一件家具的成品,涂上油漆,用砂纸打磨,看上去神气活现,并在嘈杂的市场被买主慧眼识珠,继而在岁月中遭受漫长的磨损而最终报废。所有的家具都曾经是木头,它即使被斧斫,被锯开,被刨削,被抛光,最终不可能忘掉树根的记忆,不可能忘掉身上开出的小花。枝头掉落的果子,不会忘掉吹动树叶的轻风和鸟鸣;更不可能忘掉源源不断地通过树根施送的汁液以及星空隐秘的召唤。那是生命的根基,也是自由的全部。生命在于运动。树木的生命在于一动不动。也许,人终究不是树,而更像蒲公英,成熟了就到处飞。但是,乡村的孩子要飞出去、飞到城里去,他必须脱胎换骨。这就是树木变成家具的秘密。大多数的树木都想成为雕像,但结果只能成为家具。只有少数的树木想成为煤炭。一如家具想返回树木,树木也想返回种子,而种子沉睡于黑暗而混沌的泥土中。它从未萌芽,也就不必担心砍伐,但它从没有放弃生长的想法。光是这种拱出地面、抽出嫩芽的想法,就让人情不自禁了。种子迟早长成小苗,除非它已窒息。我宁愿相信,即使一棵被肢解并制造成家具的树木,也梦想回到家乡。何况是一个乡下人。
但是,你真回得去吗?
我想起了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于一九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你不能再回家》。我不是没有动过回去定居的念头。我在城市住腻了。我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在南方最大的城市里定居,并获取了一份稳定工作,娶妻生子。我终于发现,我终究是自然主义者。我喜欢山野溪流,喜欢泥土及草木之气,喜欢树林里的鸟虫以及林间的清风,喜欢无遮无拦的天空,它空无一物或挤满奇异的云朵并不重要……我不喜欢城市。城里人也让我觉得市侩。他们喜欢用金钱权衡一切,乃至幸福与自由,纯净水可以用金钱换取,清新的空气却无法凭钞票购买。我终究是误入此地的乡下人啊。近十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过逃离。我心目中的净士,一定要有山与水,最好是某个山中小镇,不能有太多污染,又不能太寒冷,旅游区也太嘈杂。这说来简单,实已近于苛刻。我想过去海南文昌(二○一○年楼价疯长,将我此念扼杀了)、广西桂林的郊外(诗人安石榴一再向我推荐)、云南边陲乃至移民海外。我既异想天开,也一本正经。总之,我不喜欢任何一个大城市。我还没有赚够生活费,但对工作也没什么留恋。我从未渴望过建功立业,况且一个小职员能有什么功业?我对成功有迥异于种种流行成功学的理解。我想得最多的就是返回出生地,不回凤凰村,那么在化州郊外也行啊。考虑到在村庄度过的复杂岁月(快乐的童年、懂事之后饱受屈辱的少年时代,成年后在村民卑躬而惶恐的目光里,我也算是衣锦还乡了),我的念头略感动摇。我将怎样跟村民们相处呢?村庄荒废了,河水断流了,田地饱受污染。我无须再以耕种为生,在村子却无法找到乐趣了。我像那些在乡村长大而误入城市的人,没有回头路走了。我暂居在广州城郊的边缘之地,距市中心有数小时之遥,暂时打消了返乡定居的念头。
那个夏末的黄昏,彩霞像熔掉的黄金从天上缓慢而黏稠地滴落,奇异而灿烂的光芒笼罩着村庄低矮的屋顶及山野,仿佛在给村庄镀金。那是我第一次跟黄昏遭遇。我没有记忆。在粤西乡间,几乎每个夏日在晴天都有这种辉煌的晚霞。在某间泥砖屋舍里,粗通术数的主人因为一个男婴的诞生而将当天的霞光赋予了某种美好的色彩。彩霞将他的笑容染上了金色。在乡村,没有比添丁更让人高兴的了,何况是长子。
少年时,我无数次在山冈、河畔或庭院中目睹过村庄的黄昏,云霞太耀眼了,太美了,太辽阔了。那种金色为主并交织着橙色、红色、紫色种种光彩的云霞,像彩帛承托并缭绕着火球般的落日。落日掠过山冈,像烧红的石头急速地向暮色中的树林坠去。那种辽阔的美像浩荡的江水涌入我的心底,我感到了大自然的震撼。那时我不知道上天在将一个重要的启示一次次地显示于我。黄昏或落日不仅是自然的事物,也是重要的隐喻。我看到了这个喻体而懵然无知。一个乡村少年要屈服于大自然的壮美并不难,要从中领悟到某些奥秘或道理,且跟自身的命运相联系,却必须通过某些契机或桥梁。那二十年,我一直呆在村庄,从婴孩步入成年的这段时光,我无法看到旭日初升以及正午的凤凰村,那是属于父辈以及祖先的光阴,但我目睹了村庄的黄昏。在十几二十年间,村庄从生产队时期的奄奄一息到开放年代的起死回生并达到了史上的繁荣,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却犹如落日急遽衰落。当我意识到那种黄昏的巨大辉煌及绝望跟我多次观看晚霞的感觉毫无二致,已是离开村庄多年后的事了。
那个夏日黄昏,我从求学的广州回到村庄,我躺在彩霞照耀的山坡上,从裤袋掏出一本叫《偶像的黄昏》的小册子。我望着天空、云霞、落日和远山,暮色愈来愈浓,村庄的屋舍略显模糊,有的房子透出了灰暗的灯光。我第一次意识到,黄昏的具象与抽象,黄昏的符号与实质,黄昏的光芒对应着转瞬即至的黑暗,黄昏的厚重与华美也将转眼即成记忆。至少,它有着多重的含意,而不仅是我所目睹的事物。
多年之后,当我回忆那个黄昏、那本书以及我当时阅读的情景与思绪,我似乎领悟了那个启示——我有责任将凤凰村在暮色完全笼罩之前,将天上巨大的辉煌和大地的安详呈现出来,使之成为相对固定的记忆——之后,是不可避免的黑暗像铁锅倒扣下来——像果壳的内部,像灶膛的灰堆,那是乡村的夜晚,连星光都在揭示这是真正的漆黑。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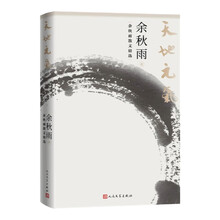
——安石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