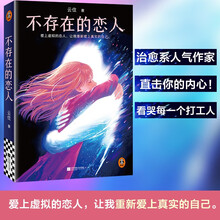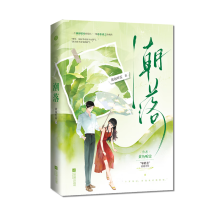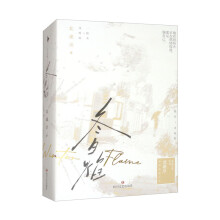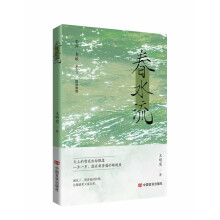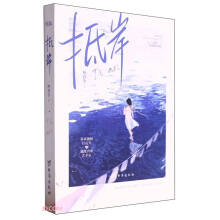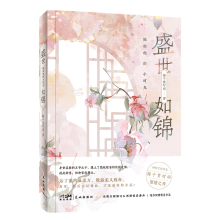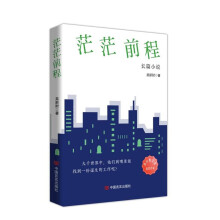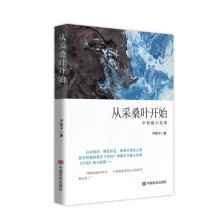《黑弄堂》:
我时常会回到狭弄里,对着那扇山墙上的后窗。
在我的左边,是我们那排房屋的后墙。那种水泥拉毛的墙面,不像楼体的正面,水泥的颗粒比较细腻光滑。也可能只是因为背阴受潮的缘故,墙面的涂料剥落了,使它看上去有一种裸露的效果。它有三层高,顶上有晒台,于是,屋脊、晒台围栏、壁炉烟囱——壁炉早已经废弃了,烟囱兀自立着,在天空上划下一道凸凹有致的边际线。我右边是一座院墙,墙那边是某个机关单位的大院。墙高大约抵二楼的位置,墙头上长着杂草,毛茸茸的一行。墙面剥落,颜色灰暗,这使它看起来比实际的高度更高。两面挟持下,顶上只有一线天。我的前面,略上方一些,就是那扇后窗。
我努力要看清周遭环境,以便了解这后窗显得如此荒凉的原因。说它后窗,其实是在侧面,开在一面山墙上。这一面山墙面积相当大,挡住了狭弄前方的视野,可以想见这一幢房子的楼体。石头的基座上面垒起红砖,铺展开一道大屏障,上方,二层的位置上,就是那扇窗。照理说,它是应当有些情致的,木头的窗框,嵌在红砖墙上,砖缝里生出几茎草,窗下还有一片空地。它似乎是一个后院,可是,倏然间,它敞开了,于是,原先的幽闭的静谧,在光天化日之下,消散殆尽。有一样东西可证明它先前的隐秘,就是那一段残壁。方才说的,机关的院墙,在狭弄口的位置,断开一条横切面,由此中止了狭弄的延伸。很显然,原先是有一道墙从这里开端,将狭弄和后窗所在的楼房隔开,一贯往之弄口。后来,为了某种原因,这道墙拆除了,却没有拆除干净,残留的砖块从水泥壳子里戳出来,形成嶙峋的断面。有些空间是不能开启的,一旦开启,便气韵尽失,瞬息抛荒。
现在,它成了这弄底的一个死角。那片空地,不知为什么没有像弄堂内其他的地面一样铺上水泥,而是裸着泥土,却又没有草木,因为高低不平,下过雨后积着水洼。山墙上的砖面有一点皲裂,窗框的木头已经半朽,再加上那条残壁衬托,那扇后窗竟有些狞厉起来。我经常回到这里,我指的是思绪,回来这里,站在后窗下面,大约二十米远的地方,看着它。或者不如说是,它看着我,将它瞳仁里的黑暗全投注于我,我不由心怀忧惧。
方才说了,从这面山墙看,就能看出楼体的壮观,它是由数十个门洞一列排开组成。石头的基座至少一米半高,砖砌雕花的门面,巍然立于台阶,每一层的层高都在三米以上。房间交互相错,既要考虑采光,又要考虑达往通衢,因此结构相当复杂,犹如迷宫。它们混沌一团,只有我去过的地方,兀自亮着。真的,我进去过!就像鼹鼠走在昏暗的地底。还像蜒蚰,所经过的地方都留下银色的黏液,在暗中发亮,那就是我去过的地方。没有多少,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根本抵不住四下里汹涌的沉暗。有时候它们完全沉没了,有时候却陡然地一亮。记忆这东西,真是又脆弱又顽固,而且颇具弹性,当遇到阻力,就会改变形状。它如此之柔韧,在时间的夹道里挤身而过。我还能嗅到灰尘的气味,藏在地板夹层里,肥得流油,人踩在地板上,便从缝里一蓬一蓬溢出来,就好像是房子的体液。你一伸手,都能握一把,蛛网似的,又呈粉末状,滑溜,又黏腻,而且,温乎乎的。
我对它心生畏惧。跨过地面上残留的墙基,这是我们弄堂与他们弄堂暖昧的分界,走过去,天色不由就暗了,那是这庞然大物投下的阴影。相对底下的弄堂,楼体显得过于壮大了。石头台阶的阶级很高,对于小孩子的腿脚,用得上“爬”这个字。爬上台阶,迎面扑来一片森凉,我简直望不见天花板,天花板被楼梯切割成一个巨大的立体几何形。门厅的一侧是房间,门扇如此之高,上方的天窗将日光曲折地投射过来,并没有因此而明亮一些,反而造成一种昏晦的气氛,灰尘在微明中翻卷。相隔一条走廊的另一侧,是楼梯。这道楼梯直上二层,可想有多么远和高,够人爬一气的。梯级的木板早已让鞋磨褪了漆,裸露出白木的颜色,灰尘像油灰泥住缝,又变成一种铜青。此时,还能借到门厅外面的光,照着我们,就像甲壳虫悬在斜壁上,一点一点往上攀。攀到顶,转上走廊,和底层一样,一侧是房间,一侧是楼梯。走廊顶头有一扇窗,所以,这里尚有光线可言。可是,再上楼梯,陡然黑暗下来。通向三层的楼梯上方,平铺了楼板,接近三楼时,伸手可触碰顶上的楼板,在最末五六级梯阶的位置,留了出口,供人上下。这就有些像工事,也体现了这幢楼的防御意识。三楼简直就是个黑匣子,伸手不见五指,四周是一些紧闭的门。这房子里,四处潜伏着黑暗,猝不及防便身陷其中,所以我说我们像鼹鼠。就在这黑匣子中间,竖一架木梯子,没有扶手,只能匍匐在上面,这样,我们就变成了蜥蜴。黑暗中,爬上陡立的木梯,是对手脚笨拙的我的考验。当我爬到中段,上不能,下亦不能的时候,我几乎要啜泣起来。没有人帮我,甚至,有些时候,还有人故意摇晃我身下的梯子。我为什么要越过这么多障碍去到那里?为了开小组。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学生的一种学习方式,课余时间里,相邻居住的同学集聚一处做作业。于是,我走进了这幢可怖的大房子。作为一个学生,学校的所有规矩都神圣不可违抗。
我终于爬上了梯子,出乎意料的是,梯子上方格外明亮。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