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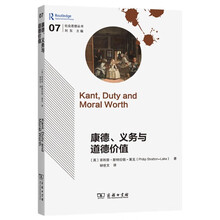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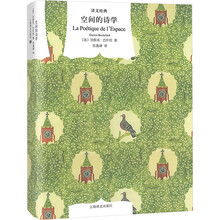








作为著名的印欧宗教学专家,布鲁斯•林肯以极扎实的多学科功底,探讨了印欧民族关于战争与献祭的行为及其所蕴涵的生死观这一重大主题。全书在主题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探讨死亡的本质,由此引出信仰的问题;二是战争与献祭,从宗教实践的层面展开叙述。这种复杂结构借助作者对道德、情感、逻辑等技巧的娴熟运用,使得全书在整体上自足,令人的阅读感受高潮迭起。本书曾于2002年出版首次中文版,出版以来收到很多宗教学、人类学和神话学等专业读者及普通读者的关注,对于本书在有关仪式的考据和语言的文献等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不约而同的好评。此次再版,译者重新修订了译文,并对当年出版时一些概念的认识做出了有学术进展的更新。
作者自序
没有温迪·多尼格的坚持和善意,本书不会问世:在本文开头向她表示感谢是恰如其分的。温迪在许多封充满情谊的信函以及辩论中强调,我在1978年至1980年间所作的一组讨论死亡的神话以及各印欧民族想象中的丧葬布局的论文,一直是有趣而重要的,而我却老眼昏花,不是忘得精光,就是视而不见。她力劝我把它们整理成册,也许还可以加入一些新的材料,以使那些能够从中获益的人们比较容易得到它们,在此期间,她不仅慨然襄助,而且游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力陈这一选题的优点。本书乃是在她的创意、鼓励、帮助和友情之下问世的,我对她感激至深。
我们在一起整理出了一份目录,开篇是对印欧宗教的概述,原系1983年为一部后来从未问世的作品撰写的,接着是讨论死亡的论文,其中补充了一些论文,以及较新的材料。温迪要我坐下重读旧作(本书第一部),它们都是多日不看的。匆匆看过一遍后,我诧异于这些文字与第二部、第三部之间的差别。我得承认,我本人更喜欢后面的文章——理由我会解释的——不过我还是得说,这些旧作自有其价值在。
将本书作为整体通读一遍之后,我看到一些主题的一再出现,我发现书中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恐惧。书中开篇所论,是要发现面对死亡的意义与慰藉,这一探讨本质上是令人绝望的,却蒙上了它所使用的学术用语和文字学上的精确性的假面具。我还诧异于这一事实:最初数篇格调明快、充满希望的论文——《论天堂的意象》《冥王》和《记忆之水和遗忘之水》,都是在一个令人快慰、几乎是狂喜的音符上结束的——居然是在我至爱的祖父(弗兰克·威廉·林肯,1890年1月—1977年3月8日)去世的冲击下写出来的。而今我明白了,我在那样的时刻作那样的研究,乃是要竭力发现,那些神话,那些讲述死者如何脱离痛苦和烦恼,安眠于幸福、光明之乡的神话,于我是一种安慰,尤其从一系列描述死者的经验和智慧如何不是永远归于遗忘,而是以记忆的形式返回生活的想象中,我得到了慰藉。
然而,希望、慰藉和安慰证明都是难以持久的。最初对于虚无和湮灭的畏惧和逃避,再次把我带到虚无面前,这一虚无反映在一系列神话主题中间,它们比我以前所研究的更加阴冷抑郁。《摆渡死者的艄公》证明并没有什么艄公,他只是最令人烦闷、最令人感到威胁的晚境的人格化而已,而死者的居所(“泥屋”)证明只是坟墓而已。最后,我的研究计划不止在一个方面变得难以维系,至于我曾经渴望做的进一步研究——关于阴间的金苹果,或曰在阴间入口处召唤和问候死者的女子——亦未保持一以贯之的兴趣[1]。1982—1983年,我接受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打算写一本关于“印欧神话中的死亡和阴间”的书后,我发现自己在探讨把不同灵魂引向不同命运的两条道路描述的那一章就写不下去了。该书仍为草稿,从未写完,而我已转向其他问题,即导致我写《神话、宇宙和社会》[2]的那些问题。此后,我再也没有读过我的旧作,直至温迪劝我这样做,于是,我便回头来完成《两条道路》的研究,只是与最初的研究方式大不相同而已。我不仅反思神话材料本身,而且反思我试图理解它们时所遇到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此文作为第九章在此发表。
在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有一个重大的断层。例如,我观察到,后者更加关注的是实践而非信仰,是杀戮而非死亡。因为第二部写于1984年至1988年间,探讨了战争和献祭,分别研究武士和祭司的职业化杀人实践的特点。在这些章节里,死亡并非被仅仅当做终将临到每一个人的自然事件,而是在一定情形下一些人处罚另一些人的事件。此外,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所持有的信仰,杀人者常常能以一定的自信和相对的问心无愧从事他们的工作——对我而言,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
研究重点的转变显然和我心境、态度的转变有关,因为,研究死亡标志着是人皆有死的事实所唤起的一种普遍的慈悲心,而研究杀人则表明一种比较政治化的意识,我感受到人所处的阶级不同,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就大不相同,因而我觉得,必须站在受害者一方进行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在《德鲁伊特和人祭》《论斯基泰人的王族葬礼》或《荷马史诗中的lyssa,“豺狼一般的狂暴”》的研究中——并非随便地、毫无结果地呼吁弃绝杀人,即使这样做有着崇高的道德意义。毋宁说,我试图对那些使相关的行动者相信他们有权(甚至有义务)去杀人的想象和论点进行严肃的思考,我承认,这些解释具有(并且继续具有)非常真实的和明显的说服力。我研究它们的目标,首先是要理解这些话语如何以及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其次是要使它们不再神秘化,揭示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并解释它们所为之服务的看得见的社会的、物质的利益。
这一计划也许在以前未曾发表的有关《献祭的意识形态与印欧社会》的论文(本书第十三章)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文中将献祭的概念从真正的杀人行为扩展出去,把其他一些情形也囊括了进来,其中宗教的话语被利用来系统地证明,一些阶级是依附于另一些阶级的——武士依附于祭司、百姓依附于国王、女子依附于男子、少年依附于长者或者奴隶依附于自由人——并使这种依附成为永恒。这些统治结构常常镌刻在神话叙述里面而得以合法化。不过,在我看来,神话未必一定压迫人,而“科学”则未必一定解放人: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乃是内容与结果的问题,而不是样式(genre)问题。科学的话语也会像神话一样神秘而害人匪浅,我在第二部的最后三篇文章中就是为着试图澄清这一点,文中探讨了古代生理学“知识”是怎样被利用来支持阶级、性别和人种之类的等级范型的。
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断层,在另一方面表现为从比较研究转向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更多依据的研究。第一部中的所有文章皆致力于发现“印欧人”或“原始印欧人”的内涵,而第二部则主要探讨历史上已知的民族和文献:例如,恺撒和其他人所叙述的凯尔特人的德鲁伊特[3]、苏鲁支看到的伊朗武士。比较仍然是有的,如《战争和武士:概述》一章,但总的来说,我现在感兴趣的比较是在不同的互不相关的语境中探索共同的主题:如以人体比拟社会等级,以及在战争经历中的动物比喻和非人行为,或者话语在社会边界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类的主题。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以前所做的但现在倾向于放弃的那种比较,乃是作为一种研究目标,去努力重构生活在假定的时间和地点、说一种假定的语言的一个假定的民族的假定的信仰和实践。此类研究,每一步都会遇到一个陷阱。在我看来有好些理由拒绝这类比较。其一乃是学术上的谨慎。因为,印度、伊朗、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欧洲大多数古代民族所讲的语言,显然是有相互联系的,但是绝不能断定这些联系的本质是什么。大多数专家肯定,这些语言起源于一个未经证实的、在发生学上互相关连的原型,就像罗曼语起源于拉丁语。不过,其他学者则论证说,起源上完全无关的语言,完全可以通过文化交流和贸易而相互影响,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原始印欧语”是人为构造起来的混和语,更像斯瓦希里语或托克皮辛语(Tokpisin)而非拉丁语[4]。在我看来,试图确定一个最初的共同体和最初的家园一开始就是成问题的,而考古学家之间最新一轮的争论,几乎未能增加我的信心[5]。
那些尝试重构“印欧”神话、仪式或宗教信仰——仿佛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原始民族——的人也面临类似的困难。更有甚者,情况显然比在已经够困难的语言那里还要困难。因为正如克里斯第安努·格罗塔内利(Cristiano Grottanelli)多次表明的那样,被某些作者奉为经典的“印欧”文献,其中许多叙事范型,同样也可在不操印欧语的民族的文学中找到[6]。我找到了首次与格罗塔内利的交谈记录,这是我在编辑本书时的一大乐事。此次交谈是在1979年9月进行的,当时我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论文《作为太阳与救主的密特拉(斯)》(本书第六章)。讨论伊始,他就温文尔雅地向我指出,我单独放在印欧传统里探讨的一个神话主题在别的传统中也可以找得到,而其他人便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进行争论。我承认印欧人“并不拥有对于其他任何宗教的版权”,但是继续坚持认为,即使那些传播最广泛的观念——作为灵魂的引路人(psychopomp)和死亡契约的太阳——它们在印欧文献里的表达方式,与同样的观念在别处的表达方式大不相同。从此,格罗塔内利和我继续以书信形式进行个人之间的讨论。渐渐地,他改变了我的想法。正如他在一篇我给予最高评价的文章中所言,不是共同的语言或者共同的血统,而是共同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境遇,产生了共同的神话,因为,正是后者提出了在神话故事中所欲解决却从未解决得了的那些问题[7]。而且正如他多年来所教导我的那样,探讨神话叙述和历史—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较诸描述和解释任何设定的民族——不论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的神话,更加有趣,也更加重要。
如果说神话讲述很久以前极为遥远的故事,其目的则在于讲述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同样可以看到,包括学术在内的其他叙事形式也是如此。因为在训练最有素、学识最渊博的学术话语里,过去进入现在,自有其现在的理由。这并不是说学术与神话无异,研究只会产生虚构。我只是主张,学者与其他人类绝无差别。他们生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生活环境里,他们的言谈、思想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反映着、受制于他们自己现有的经验,尽管这不是他们所做的全部。不过,学者著书立说、公开演讲,不只是对某些毫无疑义的“既存”的事物作描述性的说明。毋宁说,它们是由言者、所言和听者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解释。这一过程可以是特别精确的、启发性的、有教益的,但完全不会是中立的、毫无偏见的,不论言者还是听者是如何诚心诚意地相信这一点[8]。
这一点再没有比印欧研究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因为正是殖民者的接触首先使欧洲学者掌握了梵语,随着他们认识到印度和伊朗的古代语言与希腊、罗马和北欧语言之间的亲缘性,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立刻将诸印欧语(特别是梵语)同以前出于神学和“科学”的缘故而被视为世界最古老的希伯来语进行比较。他们进而把说这些语言的人——他们所称的雅利安人、闪米特人,在种族的、精神的以及语言学的基础上互相加以系统的对比,并且总是有利于前者,不利于后者。对语言和其他材料的解释,遭到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严重歪曲,其后果广为人知,虽不必赘言,却也极为严重,不可忽视[9]。
1945年以来提出的其他各种新理论,与那些和国家社会主义一道声名狼藉的理论相比,显示出了重大不同。讨论原始印欧人家乡的学者普遍将其放在东方,而不是北方;最近关于印欧人之扩张的叙述,则把它和传播农业实践而不是武力征服联系了起来[10]。这些新理论的产生,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学者的态度有所改变,以及,相应地,他们所予认真思考的各种证据也随之必然有所改变(已经引起学者赞誉的安纳托利亚和苏联考古学的证据,以及现已衰落的体质人类学的证据等)。进而言之,他们的态度和理论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反对前几代人的态度和理论而形成的,此外,还可以从中识别出其他一些旨趣来。其中有的并未使我感到特别不适,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解释,人们或许会争辩几句。比如,我想起了充斥在玛丽亚·吉布塔丝(Marija Gimbutas)大作中强烈的女权主义取向,而这种女权主义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其大作产生的动机[11]。不过,也有其他的旨趣和理论我不得不有重大的保留,这就产生了本书第三部。
《泰晤士文学副刊》的几位编辑最早要我给1985年初问世的乔治·杜米兹的《人的健忘与神的荣耀》[12]写篇书评,正是我刚好写完《神话、宇宙和社会》的时候。当时,我还认为杜米兹是我所积极进取的学科分支中最优秀的学者:其作品技法纯熟,概念极富开拓性,影响深远,入情入理。事实上,我觉得我的作品深受他的影响,尽管我们的观点在几个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与此同时,我先是读了阿那尔多·莫米格里阿努(Arnaldo Momigliano)的、接着是卡罗·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文章,它们指责杜米兹的早期作品表现出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尽管我没有被这些出色的学者提供的事实说服,但是着实为此感到苦恼[13]。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我回信《泰晤士文学副刊》,谢绝了他们的约稿,另外推荐了几位能够代我执笔作书评的学者。
然而,1985年末,我偶然翻检到杜米兹的一篇极其晦涩的文章。它刊登在1927年的《土耳其人类学杂志》,题名为《论几次子虚乌有的大屠杀》,其内容足以令我心潮激荡——其中的理由我在第二十一章中有所陈述——我觉得不仅需要重新思考我对杜米兹的想法,而且尤其需要重新思考学者的生活与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回头重读了阿那尔多·莫米格里阿努和卡罗·金兹伯格的批评文章以及杜米兹的回应,钻研杜米兹的其他许多作品,同时去了解20世纪法国政治右派历史。我还发现了刊登在法国右翼出版物上的对杜米兹的访谈,在这些访谈中,杜米兹反复提出,首先,社会组织在等级上区分为三种“功能”是一个朴素而自然的事实,其次,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中间,唯印欧人获得了对这一“自然”事实的意识,并且这一意识构成了恰到好处的概念模式[14]。在读完这一切之后,我深信:首先,杜米兹早年深受法兰西运动的创始人查尔斯·穆莱(Charles Murras)的深刻影响,晚年则与阿兰·德·贝努依斯(Alain de Benoist)的新右派调情;其次,在对莫米格里阿努的回应中,杜米兹关于皮埃尔·伽索特(Pierre Gaxotte)的生平和事业上故意并且策略地说了谎话,既是出于对故友的忠实,也是为了掩饰自己与极右翼的瓜葛;第三,杜米兹从穆莱(而不是法国以外的任何法西斯主义来源)那里所汲取的保皇党和全民集权的观点,歪曲了他在学术作品中的诸多要害之处的材料的选择和解释。
这根本不是我轻易忍受得了的。我写信给《泰晤士文学副刊》的编辑并且提出,如果他们仍然有兴趣要我写曾经要我写的书评,我乐于从命。是的,他们有兴趣。1986年6月,我将写毕的手稿递交给他们,满心期待杜米兹作出挑衅性的回应,以及接踵而至的充分争论。1986年10月,我的书评刊登了,删除所有的注解,以便符合《泰晤士文学副刊》的风格。一星期以后,杜米兹去世。
书评——即本书第十九章全文并附原注——很自然引发了许多讨论,有的还很重要,不过杜米兹死后出版了《与迪迪埃·埃里邦谈话录》,我的推论,即杜米兹早年确与穆莱有牵连,而且他继续信奉穆莱的许多信条,在该书中大多得到了证实[15]。这一新发现与其他名人的类似发现相比,所引发的评论相对要小一些,却促使我回过头来,进一步研究杜米兹的个人信仰与他的学术作品之间的关系。我把研究结果放在了第二十和二十一章,我知道有人会严厉指责我还在批评一个死者。
这一攻击我应当认真对待,我希望杜米兹在此继续争论。肉体上他是死了,不过在其他方面他还活着,因为实际上不可能也不应当把同死者的联系割裂开来。毋宁是,死者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免要谈及他们,和他们说话,从中探索他们在生者的土地上继续发挥影响的性质与后果。一门健康的学科,就像任何其他团体一样,在继续地聆听其前辈,但也在继续地盘问他们。我——怀着希望与恐惧的复杂心情——期待着有一天其他人也会同样对待我。
我还要感谢许多人,他们对于本书的不同章节提出了建议和批评意见,谨向他们所有人表示深深的谢意。我已经提到了温迪·多尼格和克里斯第安努·格罗塔内利。此外,我还要感谢弗朗索瓦·巴德尔(Francoise Bader)、保罗·珀沙兹(Paul Bauschatz)、乌戈·比昂奇(Ugo Bianchi)、玛丽·鲍伊丝(Mary Boyce)、多米尼各·布里格(Dominique Briquel)、沃尔特·布尔克特(Walter Burkert)、埃昂·古里亚努(Ioan Culianu)、理查德·迪特尔里(Richard Dieterle)、乌尔夫·德罗宾(Ulf Drobin)、丹尼尔·杜贝松(Daniel Dubuisson)、埃里克·阿·埃德赫姆(Eric af Edholm)、安妮·恩克(Anne Enke)、保罗·弗里德里希(Paul Friedrich)、玛丽亚·吉布塔丝(Marija Gimbutas)、埃里克·汉普(Eric Hamp)、安德斯·胡尔嘉德(Anders Hultgrd)、埃克·胡尔特克朗兹(ke Hultkranze)、斯坦芬妮·亚米松(Stephanie Jamison)、大卫·尼普(David Knip)、奎珀(F.B.J. Kuiper)、珀·克瓦恩(Per Kvaerne)、威廉·马兰德拉(William Malandra)、格里高利·纳吉(Gregory Nagy)、托德·奥尔松(Tord Olsson)、尤哈·潘提卡能(Juha Pentikainen)、迭戈·波利(Diego Poli)、埃德加·波勒美(Edgar Polomé)、扬·布魏尔(Jaan Puhvel)、詹姆斯·雷德费尔德(James Redfield)、彼得·沙尔克(Peter Schalk)、约翰·谢德(John Scheid)、汉斯彼得·施密特(HansPeter Schmidt)、布里昂·史密斯(Brian Smith)、彼尔·乔纪欧·索利那斯(Pier Giorgio Solinas)、约尔根·波德曼·索伦森(Jorgen Podemann Sorensen)、杰斯泼·斯文布罗(Jesper Svenbro)、托维·泰比杰(Tove Tybjerg)、维斯内尔(H.S. Versnel),以及玛格丽特·瓦布格(Margrit Warburg)。我还要多谢替本书编写索引的黑德尔·阿佐丹鲁(Heidar Azodanloo)。
我最深的谢忱是留给路易丝·林肯(Louise Lincoln)的,她的鼓励、支持和批评都是极为宝贵的。
作者中译本导言 1
温迪·多尼格序 1
作者自序 1
第一章 印欧宗教导论 1
第一部 印欧神话中死亡与丧葬的布局 35
第二章 论天堂的意象 37
第三章 冥王 53
第四章 记忆之水和遗忘之水 81
第五章 摆渡死者的艄公 102
第六章 作为太阳与救主的密特拉(斯)127
第七章 论地狱的看门狗 161
第八章 泥屋 181
第九章 两条道路 201
第二部 战争、献祭和人体科学 217
第十章 荷马史诗中的lyssa:“豺狼一般的
狂暴” 219
第十一章 战争和武士:概论 230
第十二章 武士与非牧人:对玛丽·鲍伊丝的回答 245
第十三章 献祭的意识形态与印欧社会 277
第十四章 德鲁伊特和人祭 290
第十五章 论斯基泰人的王族葬礼 309
第十六章 切乳、断臂、砍头:斯基泰人和亚马孙人的一些献祭活动 326
第十七章 一部钵罗婆文献中的生理学思考与社会范型的形成 343
第十八章 一篇钵罗婆语经文中的胚胎学思考与性别政治学 358
第三部 驳论一束 373
第十九章 构想过去,构想未来 375
第二十章 国王、叛逆和左手 397
第二十一章 神话研究中的神话和历史:乔治·杜米兹的一篇晦涩文本,它的背景及其亚文本 421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