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哪位王子?”白雪公主一边刷牙一边想,“哪位王子会来?会是安德烈王子?伊戈尔王子?阿尔夫王子?阿方索王子?马尔科姆王子?杜纳班王子?费尔南多王子?西格弗里德王子?菲利普王子?艾伯特王子?保罗王子?明仁王子?雷尼尔王子?波拉斯王子?米什金王子?鲁珀特王子?佩里克莱斯王子?卡尔王子?克拉伦斯王子?乔治王子?哈尔王子?约翰王子?玛米留斯王子?弗洛里泽尔王子?克鲁泡特金王子?汉弗莱王子?查理王子?马查贝利王子?埃斯卡勒斯王子?瓦利安特王子?福廷布拉斯王子? ”然后白雪公主振作起来,“啊,等待一位王子真是太棒了——你等待着,并且知道你等待的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王子——但它仍然是等待。正如布拉克评论的那样,等待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阴暗的方式。我情愿做一百件其他的事儿。但是,如果我会让这次等待把我期待中那些崇高的感情从头顶上的卧室天花板上拉下来,你就打我好了;那些感情像这么多充满氢气的法文字母在那儿跳舞。我不晓得他是否会有哈布斯堡唇?”
(二)
也许我们不应该坐在这里,和别人一样,照看大桶,刷洗楼房,一周去地窖花一次钱。也许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干点别的。天知道该干什么。我们干事情从不思考。照看大桶,刷洗楼房,去地窖花钱,从不停下来考虑整个过程也许是卑鄙的。有人站在某处鄙视我们。在达克斯的温泉中,一个患痛风症的思想家在思索,上帝原谅他们。以前情况更糟。这么说没有丝毫问题。在我们发现白雪公主在林子中迷了路之前情况更糟。我们发现白雪公主在林子中迷路之前,我们的生活异常宁静。大家都很宁静。我们刷洗楼房,照看大桶,一周去一趟县上的窑子(嗨嗬)。和别人一样。我们是简单的资产阶级。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当我们发现白雪公主在林子中迷了路,饿着肚子,神志不清,我们问:“你想吃点东西吗?”现在,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白雪公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惑和苦难。过去,我们是简单的资产阶级,知道做什么,现在,我们是复杂的资产阶级,茫茫然不知所措。我们不喜欢这种复杂性。我们疲惫不堪地绕着它转,时不时还用店主式的食指戳戳它:它是什么?它或许对买卖不利?宁静已经失去了。可是,有时候,我们主要考虑的不是宁静。那时候,我们看着白雪公主,第一次懂得我们喜欢她。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三)
然后我们产生了一种幻想,一种愤怒和恶毒的幻想。我们在做梦。我们梦见自己把白雪公主烧了。说烧了不对,应该说是做成菜。在梦中,我们把白雪公主架在大火上做成菜。你还记得德雷尔导演的《圣女贞德蒙难记》中的火烧场面吧。就像那样,只不过德雷尔的片子中是竖直的,而我们的是横向的。白雪公主是横放的。她被戳在叉子上(一根大铁棒),叉子横在大火上。在梦中,凯文向火中扔更多的木头。休伯特往火中扔更多的木头。比尔往火中扔更多的木头。克莱姆把酸甜的调味汁涂在姑娘赤裸的身上。丹做好了米饭。白雪公主发出尖叫。爱德华摇了一下转肉的曲柄。她烤熟了吗?她正在发出许多噪音。肉的颜色看起来快烤熟了:一种棕红的颜色。烤肉温度计显示肉快烤好了。“转一下曲柄,爱德华。”比尔说。休伯特往火中扔更多的木头。简往火中扔更多的木头。烟还是那样呛人。在烟中,安托南·阿尔托往一根长棍一端挂了一个十字架。白雪公主问我们是否会拿起叉子。“痛得很。”她说。“不,”比尔说,“你还没有熟。痛是应该的。”简笑了,“你为什么笑,简?”“我笑是因为烧的不是我。”“为你,”亨利说,“我们准备了赤热的铁鞋。一双赤热的可塑的铁鞋。”“它和公正无关,”比尔说,“但和恶意有关。”我们在梦中看见白雪公主在转动,在痛苦和美丽中转动。
(四)
白雪公主又把头发挂出窗外。现在它更长了。大约四英尺长。她还刚用金色的普瑞尔洗发水洗过。她对男性控制物质世界感到愤怒。“啊,但愿我能一把抓住那个把电气连接也称作男女相合的人!他以为自己精于世故。但愿我能一把抓住那个把管件叫作乳头的人!他以为自己温文尔雅,但你会注意到,那并不能妨碍他们把野牛问题弄糟。野牛去哪儿了?你可以走上一里又一里又一里又一里又一里又一里又几百里却见不到一头!而那并不能妨碍他们用铁路攫取最好的土地!也并不能妨碍他们让疏离感渗进每一个地方,像一条当你把开关推到‘开’的位置后仍不起作用的灰色大电褥子那样,覆盖万物。所以不要跑过来指控我不严肃。女人也许不严肃,但至少她们不是大傻瓜!”白雪公主把头伸出窗外,把她挂在那儿的长长黑发拉进来。“还没有人爬上来。那就说明了一切。这个时代不是我的时代。我生不逢时。那些人都有毛病,站在那儿伸着脖子目瞪口呆。那些人都有毛病,来都不来,也不试一试爬上来。来充当这个角色。世界本身也有毛病,连提供一个王子也做不到。连至少开化到给这个故事提供一个正确结局的能力也没有。”
(五)
白雪公主又喝了一杯健康橘子汁。“从今以后,这些方面我要节制。这些让人快乐的东西。我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我再也不会在夜里,或午饭后,或雾蒙蒙的大上午,像一个少女般轻快地走到他们床边。我从未干过那个。总是我的一时兴致所至支配着那些次群居,李维巧妙地把它们总结成‘败者该遭殃’。我至少要为那个比分感到庆幸。我再也不用给他们切洋葱,煮面条或腌牛排。我再也不用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寻找有灰尘的地方。我再也不用把他们的内衣叠得整整齐齐,塞到高脚柜里。现在,我甚至不用和他们说话,除非通过第三方,或者有特殊的事情要通知——我的情绪又一次产生了细微变化,又一次异想天开,又一次反复无常。我不知道这样一个策略会让我得到什么。我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希望实施它。这么做好像挺小心眼、挺卑鄙的。我内心冲突,但贯穿我思想的主题是存在的,那就是觉得不满足。这个恼人的观念是从哪儿来的?无疑,来自出租书籍处。也许那七个男人本该把我留在林子里。我会死在那儿,当所有的树根、浆果、兔子和知更鸟都耗尽了。假如我那时候死了,现在我就不会在这儿思考。没错,有朝一日,我终究会死。肯定会的。思考将终止。你再也不会总是在早晨四点差一刻时,在床上用胳膊肘支撑着,思考着日本人是否比他们猪一样的西方同龄人更幸福。再来一杯橘子汁,这一次稍微加点伏特加。”
(六)
我们坐在一家路边咖啡馆里,谈着过去的岁月。那些往日的岁月。然后老板来了。他带来一位警察。一位带黑皮警棍和拉斐尔·萨巴蒂尼的书的警察。“你们太靠人行道外侧了,”警察说,“你们必须待在花盆后面。你们离楼房基线不能超过十英尺。”我们又退回到楼房基线后面。我们想我们可以在花盆两边谈论过去的岁月。我们友好而且随和,和往常一样。但移动桌子时,我们把饮料弄洒了。“弄脏桌布也要付钱。”老板说。然后我们把剩余的饮料全倒在桌布上,让它全部变成红玫瑰色的。“把弄脏的部分指给我们看,”我们说,“哪儿脏了?只要你能把弄脏的部分指给我们看,我们就付钱。找找吧,我们还要再喝点。”我们深情地回头看着刚才待过的地方。那个警察也和我们一起往回看。“我感觉那儿更好,”警察说,“但法律就是法律。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它是法律。你们是否介意我尝一下你们弄洒的饮料污渍?”警察把我们的桌布拧干,然后一饮而尽。“这污渍不错。现在,请你们允许我离开,我感到普利特大街上有一件重案。”警察飞一般地跑着去办他的重案。老板带着更多的污渍回来了。“谁把我的桌布弄皱了?”我们看着桌布,的确有一片令人难受的区域。“有人得出钱烫平它。”然后我们站起来,赤手空拳就把整个路边咖啡馆弄得一塌糊涂。当我们干完时,要弄清是谁的过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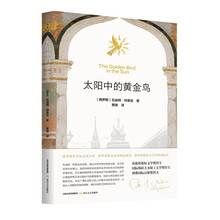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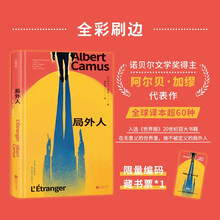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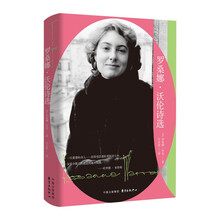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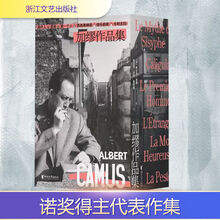

★读这本书如同一颗颗语言“照明弹”在眼前断断续续爆炸开来,风车转般变化的表述方式,乔伊斯式双关语与文字游戏的樱桃炸弹……一个荒谬的童话故事,被极具娱乐化地颠覆。
——美国《时代》周刊
★巴塞尔姆可以说是美国天才的作家。他创造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小说。《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里包罗万象:有像威廉·巴勒斯作品中的那些滑稽角色,有如图画般的语言构词,有粗俗的评论、疯狂的美学实验、大跌眼镜的喜剧效果。
——美国《生活》杂志
★耳边仿佛传来童话中七个小矮人哼着小曲儿。这位出色的作家知道如何将现实的精神困境转化为合理逻辑,将合理逻辑又化作一桩桩反映我们所处时代真实故事的荒谬喜剧。
——美国《新闻周刊》
★巴塞尔姆这种有控制的疯狂,可能显示了文学的一条新路径。
——美国文学杂志《星期六评论》
★他教过我们所有的人怎样写作。
——杰罗姆·查林,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
★巴塞尔姆小说中的现代人,是T.S.艾略特笔下“空心人”和“荒原人”的后代,被掏空了真正的感觉后,又塞满了既定口号。
——路易斯·戈顿(专门研究巴塞尔姆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