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塔戈拉没有直接回答苏格拉底关于“成为”与“做”的论证;他甚至完全放弃了西蒙尼德斯的诗,乃至放弃了所有的诗歌,转而诉诸所有人的意见:“诗人的无知就会太大喽,要是他竟然说,以如此方式获得德性是件太寻常的事,而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所有事情中最难的。”如果“所有人”都认为德性是一切事情中最难的,他们的判断正确吗?苏格拉底在反对这个主张时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不过他仍在借用普洛狄科的权威——这一次苏格拉底将普洛狄科作为老师,并认为普罗塔戈拉应该像自己一样向普洛狄科学习。苏格拉底说,因为普洛狄科属于古人的行列,他那“神样的智慧”已经“很有年纪了,不是起自西蒙尼德斯的年代,就是还要年迈些”(341a)-那么也许要经由匹塔科斯,上溯到赫西俄德和荷马。而另一方面,普罗塔戈拉却在这方面“没经验”,而苏格拉底因为是普洛狄科的弟子,所以更老练,而他本人也因此站在古人的行列。
苏格拉底的下一个论证属于谐剧,他把普洛狄科拉来做同伴,共同解释西蒙尼德斯第一行诗中的一个语词——困难(χαλεποζ),普罗塔戈拉曾重复这个词(最困难,340e)。“也许西蒙尼德斯对这“太难”的用法并不是像你的用法那样”——也许是克欧人的本地用法。也许他对“困难”的用法与苏格拉底对“可怕”(δεινοζ)的用法相同:“当我用‘可怕’这个词称赞像你一样的人,并说‘普罗塔戈拉是个可怕的有智慧的人’时,普洛狄科每每会告诫我……‘可怕’,就是坏。”苏格拉底得以当着普罗塔戈拉和他的同伴的面称他为一个坏的智者,在这么说时,他享有谐剧作者所特有的豁免权。如果克欧人普洛狄科认为,“可怕的”就是坏的,那么可能克欧人西蒙尼德斯用“困难”时指的也是坏的(341b)。“我们来问问普洛狄科吧,〔89〕关于西蒙尼德斯的方言,问他才对。普洛狄科,西蒙尼德斯的这个‘难’说的是什么呢?‘坏东西’。”难怪苏格拉底曾经跟随普洛狄科学习,普洛狄科这位智术师有种幽默感,所以一来愿意配合苏格拉底,一来也要看看,苏格拉底在回应时对普罗塔戈拉使坏,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所以西蒙尼德斯“谴责匹塔科斯,当匹塔科斯说‘做高贵者难’,在西蒙尼德斯听来,仿佛他在说‘做高贵者坏”’——仿佛是西蒙尼德斯听匹塔科斯说了苏格拉底听到普罗塔戈拉大胆对雅典年轻人所说的话:做好人是坏的,而做坏人是好的,所以要勇敢、智慧地打破你被教导的正义、节制和虔敬。普洛狄科是一个好的谐剧配合者:“可是,你认为西蒙尼德斯说的是别的什么,苏格拉底?他责骂匹塔科斯不懂得正确区分语词,因为他虽然是勒斯波斯岛(Lesbos)人,却是在蛮夷方言中长大的?”(341c)来自阿伯德拉的普罗塔戈拉又怎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他回答得对,也只是谨慎地再次强调了通常的看法:“这太离谱啦,普洛狄科。我很清楚地知道,西蒙尼德斯所说的‘难’与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不是‘坏’,而是不易的东西,要靠许多作为才能实现。”(341d)
苏格拉底承认,西蒙尼德斯当然是这个意思,而普洛狄科也明白,因为他是在开玩笑——而苏格拉底表现得好像是普洛狄科“要考验一下你是否有能力持守住自己的论点”。是苏格拉底在开玩笑,也是他在考验普罗塔戈拉,而且,他向所有人宣布普罗塔戈拉没通过考验:西蒙尼德斯并没有说“难事”是“坏事”,“最重要的证据”是紧接着的下一行诗:“唯有一个神恐怕才有这种好彩”(341e)-如果神有这种好彩,他的意思就不可能是“做高贵者坏”。这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当普罗塔戈拉自己援引的某行诗受到无礼的曲解时,如果他甚至不能通过背诵下一行诗来予以驳斥,那么,他又是怎样的一位研习诗歌的学生呢?而苏格拉底呢?他表演了大师般精湛的手腕,用小巧敏捷的解经学功夫应战这位智术师,后者宣称,在诗学方面的聪慧是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苏格拉底这位好开玩笑者能让他的玩笑叮人。①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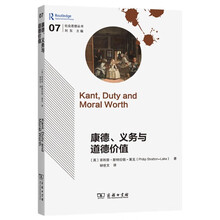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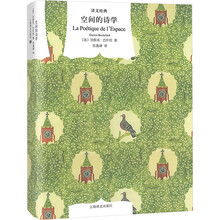








——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