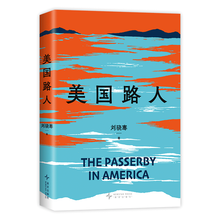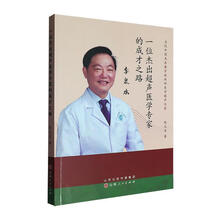春天以来,我一直循着那些绿色的线索,远离城市,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行走在乡间、田野,与那些庄稼以及与庄稼一样的农民为伍,询问并思索着粮食的事儿。从种子落地到漫山遍野的浓绿如染,我已经涉足了大半个中国的广大农村,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宁夏、甘肃、山西、河北、内蒙古……眼看着小苗从土里钻出,渐次地分出叶片,一片、两片、三片……然后看着它们一点点拔节长高,同它们一起渴望着自天空而来的雨水,担心着老天的坏脾气。当我终于看到它们手拉起手,遮掩住土地的时候,我再一次与它们有了情感和心灵上的呼应。
这是北方的八月。
我在吉林省一个叫作乾安的小县停了下来。这里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熬过了一个短暂的春旱之后,大片大片的玉米开始疯长,不知道哪一天,它们已经把自己的高度拔得超过了那些侍弄它们的农民。一望无际的松嫩大平原上,到处是它们挺拔的身姿。绿油油的叶片和紫红色的雄缨,随风舞动,在雨后的蓝天白云之下,酝酿出一派旺盛的情韵。
有时,它们极像农人们满身力气茁壮成长的儿女;有时,它们又像大地的手臂,意味深长地向天空举起。它们与那些葳蕤的蔓生植物以及早已长高的树木们联合起来,把零散分布的村庄、村庄里的农舍,团团环抱。那姿态很像一个满怀深情的妇人紧紧地用手臂护住自己的孩子。这久违的祥和、温馨的情景,让我在心里生出很多无以言表的眷恋与感念。是的,无以言表。面对这样的事物,我和所有人一样,都会显露出拙于表达的窘迫,尽管我已经在词藻库里进行了反复搜索,最后也只能挑选出一个毫无色彩的词语——大地的怀抱。
这情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现在的居住地,那些裸露着的楼群,那个在多雾的天空下显得形影孤单、突兀嶙峋的城市。它是我现在的生命象征,它的生硬、冷峻与眼前的景象形成对比。一个是我的现在,一个是我的过去;一个是我的表象,一个是我的内心。它们彼此对立,彼此忽视,彼此遗忘。在那些远离土地的日子里,有时我会与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样,在短暂的恍惚之中,自命不凡,认为人类本来就应该高于地上一切受造之物而傲然独立。只有现在这样的时刻,面对真实的土地和庄稼,我才能够清醒地从人类的狂傲中解脱出来,进入应有的自省与谦卑,再一次认识到人的脆弱与渺小。
此时,我和这些庄稼并肩站立在我们共同的生命的家园。最初,我就是在这里结识并熟悉它们的。黄米、高粱、谷子、小麦、小米、糜子、绿豆、大豆、荞麦……这些在古老的《诗经》里被称作黍、稷、麦、粟、菽、荍的事物,在我还一个字不识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我的生命和心灵。我人生的第一课并不是一加一等于几,不是那些阿拉伯数字的演绎与组合,不是赵钱孙李或周吴郑王,不是那些横竖撇捺的结构与排列,也不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不是那些凌空蹈虚、漫无边际的神游和幻想。我和我的父辈一样,只能把有限的思想和目光集中于生命的根部,俯首于我们生之所依、命之所寄的土地和那些最接近土地的事物。
在我生命的初始阶段,我和那些庄稼一同在土地上生长。
我了解每一棵庄稼的生长过程,就如我了解自己的成长历程一样。我能够像呼唤邻家伙伴儿一样,在各种植物之中叫出每一种庄稼的大名儿或小名儿。我不仅知道一棵庄稼从种子到禾苗到开花到结籽是怎样由几片叶子变成粮食的,更知道一些粮食与我们之间的那些显在的以及隐藏着的关系。那时,我不仅在饥饿时渴望得到粮食,而且在摆脱饥饿后仍然知道如何欣赏、品味和赞美粮食。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更深的东西,还不知道粮食就是庄稼的心思和灵魂,还不知道不会说话的庄稼把它们一生的心血、情感与思想都储藏在它的籽粒之中,更无法理解那些粮食会通过某种方式最终让它们的生命基因融进我们的血液和身体,使种植和食用它们的人们也具有了它们的某些禀赋和品质。
多年之后,当我再一次关注我们曾经不以为然的粮食时,走访了很多与粮食有着直接关系的人们,包括部、省(自治区)、市、县、乡、村的领导,包括那些每天与庄稼或粮食形影相随、休戚相关的农民和工商界人士。我查阅了古今中外各种身份的人对粮食的理解、认知和论述,又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终于发现,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们,原来对粮食的认识竟然是如此的肤浅。
我的脚,在行过了千万里路程之后,又重新站在了人生最初的起点。
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这让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事物,看到它们的形式、表象在与这个世界同时发生了巨变之后,它们的本质却出人意料地保持着恒定。比如我们一向所熟知的土地与粮食,虽然灾年与丰年交替显现,品种与产量年年发生着变迁,亲近与远离庄稼的人们交相更迭,直接与间接食用粮食的人数正发生着显著变化,但某些自然的伦理,人与土地、粮食的关系却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不管人们在口头上或在内心里承认与否,实际上我们一直依赖着粮食而生存。是土地,是粮食,是那些生产粮食的人们喂养了这个世界。
庄稼不仅在空间里生长,而且在时间里生长。
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回过头来才发现,尽管地上的庄稼没有一棵会移动自己的脚步,但庄稼能够走到的地方,我仍然永远无法抵达;尽管我的脚步急切而执着,但庄稼所走过的里程,仍然多于我所能够行走的千倍万倍。虽然它们已习惯于沉默无语,虽然它们已习惯于静虚守恒,但它们却能够以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和声势,迅速将广大的时空占领。它们的叶片一直延伸至地极,它们的根须一直触及人类最深远的历史。
每一次,当我走到田边仔细端详那些玉米和水稻时,都能够感觉出与它们的似曾相识。它们在北方时的表情与在南方时的表情仿佛一模一样;它们现在的姿态与过去的姿态也仿佛一模一样。大概,南方的庄稼与北方的庄稼,现在的庄稼与过去的庄稼都是彼此的化身吧。这种浅显而又幽深、单纯而又玄妙、无争无为而又无所不在的品性,正是一切伟大事物所共有的禀赋。而粮食,那是庄稼的灵魂,是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事物。如果说庄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人以某种企盼的话,那么粮食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足够的信念和力量。
在所有事物里,只有粮食如流动的水一样,绵延不断,在时间的河床里承载了人类悠长的历史以及我们苦苦寻索而始终难得的道。
老子在《道德经》里坐而论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我不知道老子的这段话是否专门说给那些需要刻意修行、规范自己言行的圣人们,但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段话的真正领受者并不应该是人,而是所有那些具有恒定本性的事物。道是应验在一切事物上的运行规律,是一种天然的本性,是不可更改的,它只能存在于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比如粮食之中,而不能存在于那些摇摆不定,总处于变化的事物——比如人类的身上。人可以从那些承载大道的事物中感悟并顺应其运行规律,而不是改变或改造什么。道在暗处,道以不变、以永远的被动对那些发出主动动作的事物进行制约。道,就是老子胯下的那头青牛,它只管使足了浑身的劲儿一直往前走,如果你想西出函谷,你才可以跳上它的脊背;如果你想东过潼关,你就得另寻一头听话的驴子或一匹忽惊忽乍的骏马。
然而,那些真正的粮食生产者并没有闲情逸致和你讲这些空而又空、玄之又玄的道理。他们沉默而又执着,如一批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年年涉过北极冰水的驯鹿,在岁月和生活的洪流里把握着自己那把握不定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