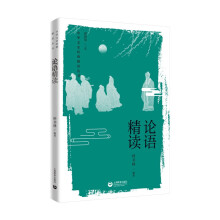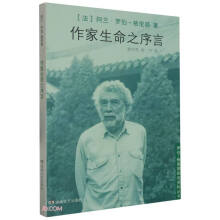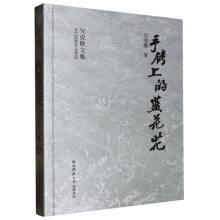序
赏不尽看不够说不完的大自然
大自然给人的赐予有两种。一是物质,空气水分,粮食蔬果,给人生存的条件;二是精神,花好月圆,明山秀水,给人享受的环境。自有人类以来,我们就向自然索取物质,创造了无穷的物质财富,从茹毛饮血到现在的电气化、原子能。和这个物质开发相同步的是向自然进行的精神索取和艺术开掘。一棵树、一片石、一竿竹、一株兰,千百年来硬是那样地看不够、品不尽、说不完、画不厌。人类在还没有文字之前就懂得欣赏自然的美。原始人就知道用彩石、贝壳制成项链、耳坠。从那时起,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一遍一遍、一代一代地观察自然,汲取自然,就有了山水文章、山水画卷,有了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有了姚鼐的《登泰山记》。人们向自然索取物质精神是两个相同步的过程,正是这两个永无休止的过程支撑着两个文明的创造,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我在云南看到过一块平光如镜的大理石,白色的底面上有黑色的图案,是一只猫,正伸出前爪去扑一只翻飞的蝴蝶,线条之清晰、神态之逼真,简直就是一幅人工的素描。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你想地层深处的岩浆在昼夜永无休止地滚动,里面有多少个点、多少条线、多少种色块,它们在运动中排列组合,一朝喷出地面凝为岩石就千姿百态,应有尽有。再加上那地面上的水、空中的风,对着山石一下一下地切割、一遍一遍地打磨,这石头又会再变出多少图案、现出多少花纹。只这一块小小的石头就有如此多的文章,其他还有水,有树,有云雾、虹霓,有高山、大漠,有林海、雪原,所有这一切的组合搭配又将会有多少无穷的变化呢?就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本来任取一件乐器来独奏便够迷人的,更何况再把它们组合起来,那将创作出多少伟大的乐章!一位科学家说:把一只猫放在打字机上,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也能打出一部莎士比亚式作品。无穷的组合总会出现最佳的选择。自然的伟大在于它所包藏的因子无穷多,它每日每时不停地变,而且又拥有无尽的时间。这是任何一个人的知识、能力和生命所无法企及的。且不要说单个的人,就是整个人类加起来也不过是它怀里的一个小宝宝。所以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又终于明白,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人类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自然是一面索取,一面研究——研究这个神秘体是怎样不断地释放物质、释放美感,然后借此指导人工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我们在物质文明方面已经从与自然的相似中得益不浅。飞机与鸟相似,埃菲尔铁塔的结构与人的小腿骨相似,核裂变聚变与太阳这个大火球相似……在艺术创造中,人类也是在苦苦地向自然求着相似。刘海粟十上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文与可胸有成竹,苏州园林浓缩山水,都是师法自然。我们经常把最好的东西称为“天然”、“天工”、“天衣无缝”。自然中永远有我们难以企及的作品,谁能向自然求得一点相似,谁能摸住一点自然之脉,得到一点自然之灵,谁就是那个突然撞开了藏有维纳斯的山洞的顽皮牧童,他的作品,包括诗、词、文、画、音乐、建筑、雕塑等便有新意、有创造,就会突然跃上一个新的高峰。如李白、苏东坡、辛弃疾,当局把他们推出政界,推入山水,终日行无定所,穿行奔波,终于有机会叫他们撞开了某一个机关,文章就有了雄健之气。而王维、陶渊明隐居山中,终日与青松、黄菊相悟禅,文章便得了恬淡之神。大自然总是将它的艺术之灵传给那些最亲近它、最想和它求相通的人。
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当艺术家,大多数人对自然只是想求得一点精神的抚慰、一点艺术的享受,这时大自然也表现得一样慷慨。大自然塑造了人,就像画家画好了一幅画。不管这幅画是冷调还是热调,是单色还是多色,画家的胸中却是储着所有的调子、所有的颜色。如果你不满意这一幅,还可以求他修改调整。人是一团不稳定的矛盾:我们的性格有内向、外向;情绪有欢乐、忧伤;工作有紧张、松弛;事业有时春风得意,有时沉沙折戟;理想忽如旭日东升,忽又日暮途穷。幸亏人不是一张凝固的油画,老黑格尔的一大贡献就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揭示了人的这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辩证关系。所以,当我们对自己感觉到有什么不满意时,就可以跳到大自然中去打一个滚。就像山坡上的一头牛犊,在微风中撒一阵欢,跑到泉边喝几口水,再斜着身子到石头上蹭几下痒。细想,我们这一生要在大自然中作多少次的调整、多少次的治疗,要作多少次环境的转换与心灵的补给呢?泰山之雄可使懦夫顿生豪勇,武夷之秀可使宦臣顿生归心。大江东去让人不由追慕英雄伟业,杨柳依依却叫你享受幸福人生。唐太宗说处世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其实他还少说了一面,以自然为镜可调身心。
近年来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不但已经上升到国策,而且已经成了全球的话题。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遗产保护,逐渐成了人类的共识。旅游已成了各国的一大产业,也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大内容。我自己在长期的记者生涯中得与山水为伍,磨鬟厮鬓,深深感受到这种天赐之福与天教之悟。多少次我登上高山,见层林尽染,波起涛涌,真想化作一块石头永立于斯;多少次在海边看大潮起落,万马奔腾,真想化作一朵浪花随波而去。这时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杜牧要“停车坐爱枫林晚”,陆游欲“一树梅花一放翁”,其与自然相通相融之心多么急切。我变不成石,也变不成浪,但我可以采一块石,撷一朵浪,借此来完成与自然的交流,同时也想把这份美感传达给如我一样热爱自然的人。我生怕自己不能理解它的真谛,所以这种文字总是想得多,写得少;笔记多,成品少。有时一个地方去多次而不敢著一字,一篇文章改一年、两年也不敢送出去,所以产品极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山水文字到现在才结成这么一个专集,还不知道是否摸准了自然的脉搏。谨献于读者,以期指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