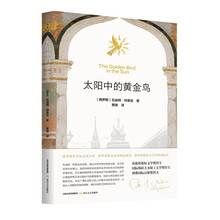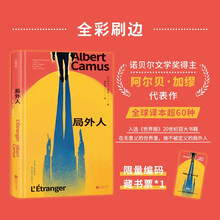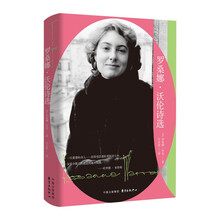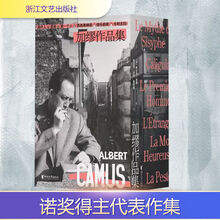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瓦尔登湖》:
第一章 节俭 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我写出本书的主要部分的时候,我是独自居住在树林里的,那是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的湖畔,方圆一英里之内没有邻居。我住在自己建造的一个房子里,仅仅靠着双手的劳动生活。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如今我又再次成了文明生活中的一位寄居者。
要不是镇上的人们对我的生活方式百般探究,我是不会强加于人,让读者注意到我的私事的。有些人会认为这些探究不相干,不过在我看来却一点也不是不相干,而是鉴于种种情况,是非常自然而又相干的。有些人问,我不得不吃些什么,我是否感到孤单,我是否害怕,诸如此类。还有的人感到好奇,想知道我的收入有多少被捐献出来用于慈善,而有的人,他们是多口之家,于是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穷孩子。
因而在本书中,如果我着手回答这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就要请那些对我并没有特殊兴趣的读者见谅。
在大多数书籍中,“我”,或者说第一人称,是被省略的,在这本书中,则被保留,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言必称“我”。我们通常并不记得,毕竟,总是在讲话的恰恰就是第一人称。倘若另有他人,我对他同样了解,那么我就不会这样大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由于经历狭窄,也就限于这个主题了。除此之外,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我也要求每一个作家,迟早都应该简单而又真诚地描述出他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描述出听来的别人的生活;应该写出就像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寄给他的亲属的信那样的描述;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活得真诚,就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也许本书更是为穷学生而写的。至于我的其他读者,他们将接受能够应用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部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在穿衣服的时候把缝口撑开,因为衣服合身穿起来才舒服。
我乐意说的事情,与其说是与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岛民有关,毋宁说是与本书的读者有关,也就是与你们这些据说是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有关;说的是你们的状况,尤其是你们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城镇里的外部状况或者情况,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状况事实上如此之差是否必要,是否它就无法得到改善。
我在康科德作了大量旅行:而在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在商店里,在办公室里,还是在田野里,在我看来,居民们都是在以一千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苦修。我听说,婆罗门坐在四面火的当中,直视太阳,或者在火焰上方,头朝下身体倒悬,或者扭头仰望天空,“直到他们不可能恢复他们的自然的姿势,而由于脖子扭曲,只有液体才能流进胃里”;或者终生用锁链锁住,居住在树的脚下;或者就像毛虫一般,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庞大帝国的疆域;或者用一条腿站在木桩的顶上——但甚至这些有意识的苦修的形式,也并不比我每天目睹的那些场景更令人难以置信和吃惊。与我的邻居们所从事的事情相比,赫丘利的十二件苦差也微不足道,因为他所做的苦差只有十二件,是有尽头的,但我却永远也不会看到我的邻居们杀死或者捕获任何一个妖怪,或者完成任何一件苦差。他们没有赫丘利的朋友伊奥拉斯帮忙,伊奥拉斯是用烧红的烙铁,烙多头蛇的头的根部,而我的邻居们则是刚把多头蛇的一颗头砍掉,又有两颗头冒了出来。
我看到,年轻人,镇子里的人,他们的不幸恰恰在于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牛,以及农具,因为这些东西获得比丢掉容易。要是他们是诞生在野外的牧场里,由狼来为他们哺乳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那样他们就可能用更明亮的眼睛看到,要求他们在其中劳作的是什么田地。是谁使得他们成为土地的农奴?当人注定要只吃一配克泥土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却应该吃他们的六十英亩的土地?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就居然开始挖掘他们的坟墓?他们得过人的生活,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推到他们的面前,尽可能地对付下去。我遇见多少可怜的不朽灵魂啊,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几乎被压扁,窒息,在生活的道路上爬行着,在面前推着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他们的奥吉亚斯的牛舍从来也没有清扫干净,还有一百英亩的土地、耕作、割草、牧场,以及林地!而无遗产继承份额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这种毫无必要的继承下来的累赘须与之斗争,却也发现征服并培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已是足够辛劳的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