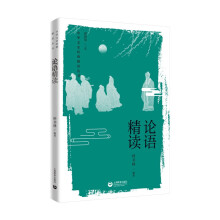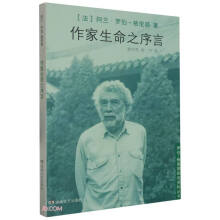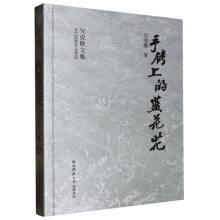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于敏文集(第七卷 报告文学·散文)》:
西湖即景
上次来杭州,有一天碰上阴雨。“冒雨游山也莫嫌,却缘山色雨中添”.想起这两句诗,就去攀玉皇山。拾级而上,路湿苔滑,一会儿浑身汗漉漉的了。美好的事物要辛勤地探索,果然!云气嗡嗡蒙蒙,一派淡灰色的调子。衬托着这个背景,挂了万千水珠的竹子格外青翠。站在山顶上,一侧可以俯瞰钱塘江。江水浩浩渺渺,从雾迷云封的天边曲折而下。对面的萧山只是一抹淡淡的青影。
山顶上风大雨大,只好在茶榭里避雨。窗外翠竹摇曳,从这里远望。一种奇特的、出乎意想的美景使我惊呆了。西湖宛如墨染了一般,完全变成浓黑的了。“波漂菰米沉云黑”,信然!“沉云黑’’三字出自胸臆,也还是得于自然。中国画里有一派米点山水,用饱墨浑洒大大小小的点子,或疏或密,或浓或淡,用来表现山雨空溟的景色。我一向以为这种技法写意太甚,用处是不大的。不想一个偶然的机会纠正了我的看法。湖水是浓黑的,而苏堤则是一条白色的带子,堤上的六桥竟宛如汉白玉雕刻的了。变幻的天工造成奇特的黑白对比,这美是我生平未见的。要在画面上传神地写实,似乎非米点的技法莫办。
这次来杭州,一下火车,碰巧又是个雨天。“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两句诗提起我的兴致,又冒雨去湖上泛舟。苍茫的湖上只有我一叶扁舟,可见像我这样的疯子原是不多的。虽然全身淋湿,我丝毫也不后悔。上次雨中登山,领略了非常的湖景,这次乘雨泛舟,又欣赏了出奇的山色。雨中的山色,其美妙完全在若有若无之中。若说它有,它随着浮动的轻纱一般的云影,明明已经化作蒸腾的雾气。若说它无,它在云雾开豁之间,又时时显露出淡青色的、变幻多姿的、隐隐约约的、重重叠叠的曲线。若无,颇感神奇;若有,备觉亲切。要传神地描绘这幅景致,也只有用米点的技法。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清代学者顾亭林的主张。这个“万”字很有意思。美是无穷的,正像宇宙是无穷的,人生是无穷的。要在无穷中有一得之见,真得在“万”字上下工夫。为了认识一个客观事物,不怕探索一万次,这种勇气本身就是美的。
我这个怪人引起船娘的好奇,而她的身世却也唤起我无限的同情。她叫柳阿巧,八岁就划船,朝朝暮暮,伴着一支桨儿,度过了二十二个年头。她是一部西湖的活历史。日本兵、国民党、达官、权吏、阔佬、贵妇,给船户带来灾难,给西湖带来荒废。阿巧和她的伙伴,天蒙蒙亮就站在高大的台阶下边,向门深似海的宅邸里窥探,心情紧张得气也出不来了。能揽到一个顾客么?能得到一天的口粮么?有时揽到顾客,也不一定得到报酬,因为还有船租和把头的剥削。苏堤荒芜了,任是莺歌三月,它也没有春晓。湖水淤塞了,一湾浊流,怎能映出清朗的月色!柳浪闻莺辟为杀人场,黑夜传出凄厉的枪声。在一带山坳里有一处碧瓦的高楼,据阿巧指点,原是杨虎的别墅。我记起来了,在国民党罪恶统治的年代,杨虎是淞沪警备司令,而上海国民党的头子叫陈群,所以统名为“虎群狗党”。这些野兽的爪牙,曾经沥下多少革命先驱者的血,就中也有左翼文学先驱者的血。为了这事,鲁迅曾经写过《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中一首七言律诗我至今还牢牢地记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好一个“怒”字!怒不可遏的中国人民赶走了虎群狗党,夺回了全中国,也夺回了西湖的美。
可是我何必缅怀往事。柳阿巧坐在船头,正从回忆里醒过来。她展眉而笑,宛如轻风拂起湖面的涟漪。既然现在生活在幸福中间,她怎能不笑。对于最近两年的灾荒,她没有悲叹,没有惊慌,没有失望。她当前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是有了确实的保障。她是西湖公社的一员,得的是月薪,不怕淡季,不怕风雨,也不怕生活中有什么变故。她不久以前生了个婴儿,在公社的托儿所里喂得胖胖的了。她的大儿子正在上海读中学,提到这一点,她心里的狂喜不禁满溢在脸上。几时见过船娘的儿子读中学呢?她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她满心欢畅地驾起轻舟,把游客送到这里那里。她在欺乃声中送走了屈辱,迎来了幸福,也在欸乃声中展望更好的明天。她是西湖的主人,而幸福的主人都是好客的。她热情地为我指点,为我解说,很怕我忽略了她从小就熟悉的西湖的美。
这时细雨霏霏,水天一色。阿巧送我到三潭印月,我就弃舟登岸。正是红瘦绿肥的暮春时节,但是西湖的花卉四时不断。我走过曲折的石桥,桥下的睡莲正沉睡未醒。杜鹃正盛开,自的如棉如雪,红的如火如血,一丛丛点缀在绿树修竹中间。杜若生在水边,很像兰花,但是不像兰花那么娇气;它繁茂得很,茁壮得很。醉人的香气扑面而来,很难分清这是哪一种花的香气。在这个天地里,那绿茸茸的细草,那碧萦萦的苔藓,似乎也都散发出清香。三潭在湖的中心,从这里引领四望,南北双峰早已裹在层云里,看不清了。柳浪和花港隐没在浓绿里,偶尔露出影子似的飞檐。南屏山下闪烁着点点的金色,这是净慈寺的琉璃瓦。所有这一切都披上细雨的网。雨丝时疏时密,景色因而瞬息变化。如今勉强地见诸文字,自然无法捕捉那种空灵的意境。
细细想来,若论水,西湖不及太湖,不及洱海;若论山,双峰不及雁荡,更不及黄山。为什么西湖的声名特高,吸引着特多的游人?是因为湖山掩映,相得益彰么?是因为阴晴明晦,湖山的变化四时无穷么?后来游灵隐,我才想通了这个问题。这里峰峦挺秀,树木参天,流水潺谖,正是“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山名飞来峰,下有许多石洞,最大的日“龙弘”,其中倒悬着许多冰柱一般的石钟乳。石壁上有千年以来历代的石刻佛像,其中不少艺术珍品。在洞的深处,有自然形成的裂隙,仰首窥视,可以看见一线苍天,所以名日“一线天”。这么清幽的地方,谁见了能不惊叹!但是人们流连不去,不只因为有这山、这树、这泉、这洞、这石刻,还因为有一座庄严的庙宇;又不只因为有这庙宇,还因为与这庙宇相关的有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人物,他对权贵嬉笑怒骂,对平民扶危济困,就是在传说中被神化了的济颠僧。自然的美,人工的美,伦理的美,这一切综合为美的极致。
后来游岳庙,我的想法更得到证实。从建筑艺术上着眼,岳庙并无特色;从造型艺术上看,岳飞的塑像更是不伦不类。但是,这里的游人四时不断。有谁到西湖而不来瞻仰岳庙的呢!我想是很少的。如果西湖只有山水之秀和林壑之美,而没有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这班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没有白居易、苏轼、林逋这些光昭古今的诗人,没有传为佳话的自娘子和苏小小,那么可以设想,人们的兴味是不会这么浓厚的。我们瞻仰岳庙而高歌岳飞的《满江红》,漫步南屏而暗诵张苍水的《绝命诗》;我们流连在苏堤上而追忆苏东坡的“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登孤山和放鹤亭而低吟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在这里,自然与人的功业与人的创造融为一体。相得益彰的不只山和水,还有自然和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