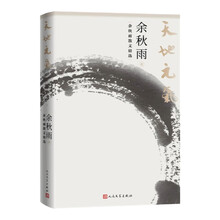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草木黎人 黔地黎族人最后的乡愁》:
民间乡村天地君亲师民间乡村,家家户户必设神龛,神龛正中必贴上五个字:“天地君亲师”。逢年过节,或是婚丧嫁娶,便焚香燃烛对其祷告,不单是祷告的人需要面目肃净,即使在一旁的妻子孩童,也不能作声,仿佛一个乡村的礼乐大典,很容易让人想起人世精神的慎重与端庄。
我小时每看着父亲行那仪式,便会立身噤声,仿佛深渊薄冰在前。虽然懵懂,总觉得在那五个字里,必定藏有人世的崇敬,甚至觉得人世的秘密,或许也藏在那里,而自己关于人世最初的想象和憧憬,经后来确定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那五个字,除了要居中外,一笔一画一定得用颜氏正楷,还必得要请一个从旧年的私塾里走出来的老先生执笔。老先生青衣善眉,挥毫运笔一如古风流转,也唯有这古意,才配得上那五个字里的肃穆——天地如神,君亲师如礼。在人世,似乎这便是准则,是皈依。
“天地君亲师”的旁边,是一副清秀的行楷: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比起那一笔一画的端正,这稍稍又有了几分人世的率性,从笔法到内容,似乎就像那清肃之地升起的一缕烟火,约略地透出世俗的气息,并紧贴乡村的日常。
敬神知礼的同时,便是来自俗世的期待。一份传家和继世的思想,直如荒寂野地的一朵菊,众木枯萎中,虽不敢说照亮了乡村的日子,却一定是温暖涌动的。尤其是多年后,当乡村日子照旧,耕读与诗书却如梦般始终缥缈难觅,这期待就越加显得质朴无比,宛若盛世繁华下的清守与坚持。
“天地君亲师”两旁,便是灶王菩萨和四海观音之类。众神分居两侧,宛如众星拱月,把那原本俗常的几个字,推上了至尊至崇的位置。而人世的尊卑友爱秩序,便在这最初的牌位里形成。只是让我觉得惊奇的是,“天地君亲师”原本只是庙堂上的思想,想不到在民间乡村,也会有如此热烈蓬勃的景象。
年节过去,婚丧嫁娶结束,“天地君亲师”依然高悬于神龛正中,而且在神龛上,除了一对永远的香炉外,必定是不能搁置其他杂物的,必得要保持那从始至终的清洁。甚至是,每隔两三日,父亲便要为之擦去尘埃,仿佛菩提树下的殷勤拂拭,其间的坚持与虔诚让人动容。四季之中,日子虽然忙碌,却不可以忘记一份崇敬和礼数。《论语》里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及“不知礼,无以立也”的句子,仔细想想,在我的民间乡村,是否也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一如流落民间的奇花异卉?——这算不算意外中的人世景致呢?因为在乡村,真实的情形必是:一方面高悬“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另一方面日出日落、锄禾担柴、渔樵闲话却才是正经事,至于诗书之类的精神话题,总是远在日子之外的。
菩萨引梵语上说,菩萨是觉悟的众生,又是使他人觉悟的有情。也就是说,凡已觉悟者,凡一切能使人觉悟者,一切有情,均是菩萨。
菩萨来到民间乡村后,似乎就有了点以讹传讹的嫌疑。先是《西游记》里那个手持净水瓶和杨柳枝的观世音被认作菩萨,再后来,一个洞穴,一块石头,一棵树,一朵花,只要稍有奇异处,都可以被视为菩萨之身,只不过没有观世音正宗而已。身形尚且幻化无常,自然更不敢奢望对那“菩萨”真意的理解了。
不过,这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民间乡村,菩萨只有一个最确切的定义:替人祛邪消灾的神。我小时每见到家家户户张贴的观世音画像,便会觉得有神秘自头顶而下,直逼全身,每一个毛孔均觉得似有“凉飕飕”的冷风吹过,。也总会觉得,这仙界与地上俗世毕竟是不同的。
再经过那些被视为菩萨的洞穴、石头以及一树一花时,心总是绷得紧紧的,眼睛从来不敢斜视菩萨的方向,只紧紧盯着前面的路,甚至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快速飞过去。这样的心理又是一种奇异。按理,菩萨既然是祛邪消灾的神,就必定是好神,对人应该可亲的,但我小时每每路遇菩萨,却要惊慌失措,总觉得会有一只手从那里伸出来,将我拽走似的。也终于确定,仙界与地上俗世,即使内心各自觉得亲,也各有各的排斥和拒绝。
生病或是有了三灾八难时,却必定要来拜菩萨。
拜菩萨时,张贴的观世音画像便不再起作用,必得要到观音洞或观音庙去,去时必定要扯上一丈二尺的红布,以及足够的香蜡纸烛。如果不灵验,那就改到洞穴石头或是一树一花之前。民间乡村普遍相信“药医有缘人”,说不准观世音不能解决的问题,山野小菩萨却能解决也未尝不可。这反映到人世道理上来,便是大有大的威仪,小有小的妙处,关键处还得看一个“缘”字。这样的大小此理,便是世间万物固有的秩序。
我小时对菩萨的又敬又畏,仔细究来,却是缘于我的外曾祖母。印象中外曾祖母始终独居于一隅,远远地避着外曾祖父。外曾祖父来寻她,她也不理,却也不另嫁。没有谁告诉我这其间的原因,但我想在外曾祖父那里,一定是有让外曾祖母伤透了心的地方,而且这一伤心,便是她全部的尘世。而外曾祖母一生留给我的印象,便是她一个人在屋子里供起的一个又一个的菩萨塑像。外曾祖母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些菩萨,一直到死,她才放下安放在菩萨里的尘世。
还有一点可以确信的便是,小时候我总会看见不断有人前去跪在那些菩萨塑像前,外曾祖母则安静地坐在一旁,一边敲打木鱼,一边替跪着的人念经祷告。至于菩萨是否真的显灵,人们的愿望是否最终达成,我却不知道。只记得去的人始终络绎不绝,连我也曾经随母亲去接受过外曾祖母给我们的祷告。外曾祖母清修的世界,也在这一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有了小小的热闹。后来外曾祖母去世,那些菩萨还在,便由她的儿媳继承了她的衣钵。只是我再没去看过那些菩萨,因为我觉得在外曾祖母衣钵传承的这一点上,始终有人世的一份奇诡甚至是滑稽在里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