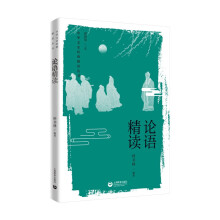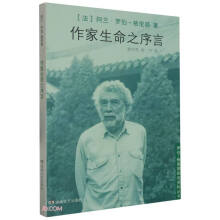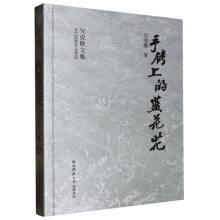一只蝴蝶?
卢贡内斯
我没能满足阿丽西亚的要求去给她讲那些花花草草,可我自有我的道理。这样我就把谈话引向了蝴蝶。她听得非常认真,这种昆虫生命里的点点滴滴都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那些灰白的幼虫、天才的织工、神秘的蛹沉睡在新生与暗影的梦里,双翅在阳光的爱抚里苏醒,好像一声光的叹息……当我的昆虫学知识山穷水尽,我建议换一个话题,她凭着自己十三岁女孩可爱的专横说道:——您得给我讲一个蝴蝶的故事。
我宁愿给她讲一桩真事,在这里面,不错,还有一段爱情。
丽拉要离开家去法国上学了,她和表兄阿尔伯特道别,她要说的话一定很多,因为他们足足说了三个小时不停止;说的话一定很重要,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一定很悲伤,因为分别的时候,他的眼睛肿了,她的鼻子红红的,手帕湿湿的——至少比平常要湿上一些,也不是因为香水草的缘故。
在丽拉离开的当天下午,外婆的家里一片哀伤,看着可怜的老人哭泣的样子,阿尔伯特就想到,她身穿黑衣是为了自己父亲的离世,而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不在了。就这样过去许多天,漫长、沉默的日夜煎熬。阿尔伯特不曾和外婆说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外婆看到这孩子如此悲伤,能做的只是哭泣,她明白这样的悲伤是无法安慰的。她十分清楚这表兄妹俩是一对小情侣,如果是真的情侣更要哭上许久了。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阿尔伯特变成了蝴蝶猎手。他学会了精巧地运用网兜,将美丽的俘虏分类,富有艺术感地摆放在明亮的玻璃上,每一只都用大头针固定好,完美地展示翅膀。这个爱好能宽释他的心情,尽管有些时候,特别是午后,当霞光在天空渐渐消逝,林霭披上静寂,他想起丽拉的话还是会哭上一阵:“如果你把我忘了,我会用某种方式来提醒你,你放心,我不会停止爱你。”但他不会真的哭很久,而且每次哭得更短些。
渐渐地,蝴蝶占据了他的整个心思,他一心只想着自己日渐丰富的收藏。外婆见他高兴,一直支持着这项无声而强烈的爱好,阿尔伯特从未缺乏过一根大头针或一块玻璃板。很快丽拉对他只剩下回忆而已,虽然他还很爱她,但再也没有为之哭泣的需要。现在他想的是:——要是她能看见我的收藏就好了!——仅此而已。他的确只有十七岁。我十七岁的时候也有过一位女友,但从一个黑夜到一个黎明她就在我心里死去。事情就是这样,让你觉得世上总有悲伤,只有悲伤。
我们刚才说到,阿尔伯特不再为丽拉哭泣。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完全攫住了他的心。
一天午后,他在花园的椴树林里张着网子游荡。宛如倾倒的酒杯,炙热的浆液化作血腥的波涛,流淌在渎圣的恢宏之上,太阳降到荣美的云朵中间。树林里一片寂静。突然间,在一丛灯芯草上面,阿尔伯特发现了一只陌生的蝴蝶。它呈白色,但在双翼上有着一对蓝色的斑点,好像两朵紫罗兰。不论是在收藏里,还是在图鉴上,他从未见过一只这样的蝴蝶。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奇迹,一个全新的品种,可以想见,他渴望拥有它。他满怀激情开始了追捕。然而那只蝴蝶灵动得可怕,总能置身于网罗所及的范围之外,但又从不远离他的视线。就这样过去了一个下午,夜幕降临,阿尔伯特愤愤地睡了,直到凌晨还梦见一只白蝴蝶,翅膀上带着两个蓝色的斑点。第二天他又在原来的地方找到它,徒劳地追捕了一天,夜里又一次梦见了它。终于,在第三天的时候,在像往常一样白白奔忙了一个钟头之后,他想:要是丽拉在就好了,她一定会帮我捉到它,我也不会这么辛苦。恰恰在这时候,那蝴蝶飞过来,落在离他极近的地方,一株忍冬上。他一网扑过去,发出一声欢呼。捉到了。
外婆见了这美丽的昆虫也赞叹不已。被捕后它立刻就被一根长长的大头针钉好,同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小心防护美丽的翅膀不被损伤。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到了第二天清晨,蝴蝶还活着,一直在痛苦地挣扎,怎样强力的毒药都无法让它安息。由于它不断地拍打翅膀,华丽的鳞粉渐渐脱落,在整整六天之后(可怜的家伙经历了这么久的受难),翅膀只剩下一对暗淡的空架子。
这时候外婆前来说情,而阿尔伯特也对保存这只难看的生物完全丧失了兴趣,它是这么顽固地抗拒死亡,于是同意拔下大头针,任它自寻生路。那蝴蝶,虽然有些艰难,还是很快消失在风里。
——那丽拉呢?——阿丽西亚饶有兴致地问。
——丽拉的故事很短暂也很悲惨:她在学校里表现得温顺而悲伤,不久便抑郁成疾。谁也不曾觉察,因为她从不抱怨。她只是变得越来越苍白,在课下暗中哭泣。在晚间她好像常常做梦,她的室友有一次曾听见她睡下的时候说道:
“这里的夜晚,在我的家乡是白天;我睡着的时候,梦见自己在那里,这安慰了我。”
她的苍白并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水土不服和远离亲人,身体有一些不适也很正常;她的沉默也被归咎于她近于零的法语基础。此外,在这些培养深闺淑女的学校里,寡言被视为一种美德,这为她赢得了很好的操行评价。就这样丽拉过了十个月,直到有一天清晨,人们在她的白色小床上发现她已经没有了气息,并不是死于她平素的苍白和沉默,因为有一团刺骨的寒气怀抱着她,仿佛浸在月光里。
医生判断不出她的病因,尽管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检查,但只在夭折女孩的胸口和背部,勉强找到了两处红色的刺痕。此外再没有什么可察之处,便在她的墓前放上百合花。
给阿丽西亚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所在的阳台也已经被黑夜包围。在我们头顶闪烁着猎户座七星,为黑暗中的静谧平添了庄严。夜风吹过,风中的呢喃显然不是为我们而发。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刚刚唤醒了一个灵魂。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难道我不知道童真是雪,是泪水中无瑕的白雪么?我正徒劳地寻找一个滥俗的尾声来抵消我的故事引发的激动,就在此处,近在咫尺,阿丽西亚已经消失在夜色里:
——阿尔伯特呢?——她问道。
一丝安慰的希望在我的灵魂中闪烁。
——阿尔伯特?
——对,阿尔伯特,他后来怎么了?
星星一样的眸子,无动于衷的神色,望着我。
——阿尔伯特继续和外婆一起生活,很快乐,虽然他常常惋惜收藏里少了一只蝴蝶。
——……一只蝴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