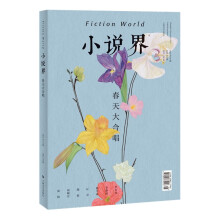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蒲宁文集(长篇小说卷 阿尔谢尼耶夫的青春年华)》:
匪夷所思的是印入我记忆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不足道的小事。那是一间浴满秋阳的大屋,由大屋南窗望见冷晖正映照着缓坡……如此而已,且仅仅一刹那工夫!为什么偏偏在这一天,这一刻,这一刹那,由于这么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我的意识会突然萌发,而且萌发得那么清晰,致使我的记忆得以运作?又为什么在这一刹那之后,我的意识又旋即熄灭,而且熄灭了那么长久?每当我回忆幼年时代,郁悒便爬上心头。其实每个人的幼年时代都是郁悒的,因为世界寂静乏味,而一颗对生活还浑然无知、胆怯、脆弱、什么都陌生的心灵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憧憬着生活。人说幼年时代是幸福的黄金时代,不!幼年时代一无幸福可言,而是弱不禁风、可怜巴巴的时代。
我幼年时代之所以郁悒愁闷,也许是我的生活环境太特殊吧?不说别的,单凭我是在穷乡僻壤中长大这一点也足以令我郁郁寡欢了。广漠的莽原,孤零零一座座庄园枯立其间……冬天是无涯无际的自雪的海洋,而夏天是庄稼、青草和野花的海洋……笼罩着原野的是永恒的沉寂,是莽原谜一般的缄默……可是换作一只旱獭或者云雀什么的,置身在死寂的荒山野岭中会寂寞吗?会发闷吗?不,它们才不在意哩,什么也不会问,什么都不会觉得诧异,更不会像人的心灵那样总是在他周围世界中幻觉有灵性存在,它们可不会感觉到这种神秘的灵性,它们既不知道空间的召唤,也不知道流光的奔驰。穹苍的深邃和莽野的广袤,告诉我除了这天地之外还另有天地,唤起了我对某种我还未拥有的东西的幻想和企求,触发了我对不知什么人和什么事的爱意和柔情……这个时候家里人在哪里?我家这片领地只是个庄子,叫卡缅卡庄,我家主要的领地在扎顿斯克,父亲经常去那儿,一去就要住很久,而卡缅卡庄的产业不大,家仆也寥寥无几。但毕竟还是有人,既然有人,不管怎么样,总归有生活……庄子里有狗、马、羊、牛,有雇工、车夫、管家、厨娘、喂牲口的、保姆、母亲、父亲、两个念中学的哥哥和一个还睡在摇篮里的妹妹奥丽娅①……可是留在我记忆中的为什么只是我独自一个人的那些时刻?这不,夏目的一个黄昏,夕阳已落到屋后,落到果园后面,空荡荡的宽广的院场内暮色四合,而我(世上完完全全只有我孑然一身)躺在院场的渐渐变冷的草地上,仰望深邃无底的碧空,像是在谛视某人一双美丽得无以复加的亲切的双眸,像是在凝望天父的怀抱。在这一碧如洗、深不可测的穹冥中,有片自云在极高极高的地方浮游,聚合成圆形,复又缓缓地变幻着形状,缓缓地消融……嚄,这催人泪下的美!要是我能驾着这朵浮云,在这吓人的高度上,遨游于广袤无垠的天际,离居住在这高峭的苍穹中的上帝和白翼天使们仅咫尺之遥,那有多好呀!这不,我又躺在庄外的田野里了。黄昏还跟那天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那低低的残阳还在熠熠闪光——而且跟那天黄昏一样,世上只有我独自一个人。在我四周,不论我往哪里看,到处都是麦穗累累的黑麦和燕麦,而在麦田里,在密密麻麻直不起腰来的麦秆间,是隐蔽的鹌鹑世界。此刻鹌鹑还保持着沉默,岂止它们,万籁都默不作声,只有一只陷身麦穗丛中的棕红色小甲虫,不时东碰西撞,怫郁地发出嗡嗡声。我怀着恻隐之心解救了它,惊奇地打量着它: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只棕红色的小甲虫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飞往何处,为什么要飞,它在想什么,有什么感想?小甲虫气鼓鼓的,不苟言笑,在我手指间爬动,坚硬的翅鞘沙沙作响,从翅鞘下伸出了非常之薄的黄膜——突然间翅鞘的坚甲分开,张大,那黄膜也张开来了,嚄,神态优雅极了——小甲虫腾空而起,心满意足地轻松地发出嗡嗡的声响,永远离我而去,消失在空中,把一股我还从未体味过的离愁留在我心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