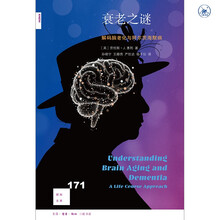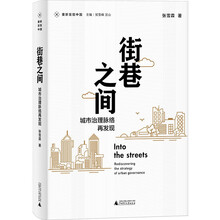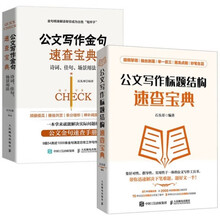论男孩的当代命运
柏拉图思考过一个问题:“哲学家可以对年轻人说些什么?”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哲学问题。
在前一章中,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讨论性别差异的主体(事实上,这很重要)。在本章中,我准备谈一下男孩子的命运。我还要谈谈女孩子的命运,这一点我放在第三章,也就是本篇最后一章来进行。
我打算在这里谈谈我的三个儿子:西蒙、安德烈、奥利维耶。他们都多次以十分粗野的方式,教训我说,儿子既是他们自己,也是父母的儿子。
我想从一个概念神话开始谈,即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Totem et tabou)和《摩西与一神教》(Mo.se et le monothéisme)中的一套东西。对于最基本的任务,对于黑格尔,弗洛伊德用三章的篇幅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第一章谈原始部落,在部落里,想寻欢作乐的父亲垄断了所有的女人,儿子们造反,为弑父铺就了道路。这就是契约的起源,通过契约,儿子们尽可能以平等主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第二章谈到了死去的父亲以单一神的形象升华为律法。父亲再一次成为严厉的守护者和苛刻的卫道士,但重要的是,要明白被弑的真实的父亲只能以象征性的父亲的形式回归。第三章谈到儿子们分享了父亲的荣耀,在基督教中,其代价是举行暴力残忍的成人礼:上帝之子的成人礼,通过折磨和死亡让自己获得人性。
关于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东西,关于讲述这个故事的结构,我有三个评论。
对于父亲。在第一阶段,我们遭遇了一个真实的父亲,一个寻求快感的父亲,一个拒绝分享他对快感的垄断权的父亲。我们会看到,对于这些儿子,一个起作用但不那么真实的因素就是斗狠(agressivité),只有凶徒才喜欢斗狠。在第二阶段,我们得到一个象征性的父亲,这个象征性的父亲建立在真实父亲的基础上,但正如拉康所说,他是以大他者(Autre)的外表回归的。从儿子的角度来说,真实所激发的反抗性的斗狠,被献给了大他者,所以,这是一个无穷尽的服从的形象。在第三阶段,即在基督教中,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想象性的父亲。真的,像以往一样,父亲重新回到了之前的舞台上,他就是儿子行动的背景。他成了三个秩序的想象性总体:他是一个父亲,三位一体的父亲。但无论在真实父亲还是在象征父亲那里,三个秩序都是无法形成一个总体的,所有父亲只能表现为一个外表。
在弗洛伊德的思考中,还有一些关于父亲的基本形象。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儿子。在这个神话中,儿子的生成是一个辩证的架构――事实上,儿子的架构是所有经典辩证架构的模板。因为,如果说儿子事实上能与父亲彻底和解,与父亲共享荣华,坐在父亲的右手边等等,那也只有在完成了三个阶段之后,儿子才能做到:直接暴力性攻击的阶段,从属于律法的象征阶段,共同之爱的最终阶段。在律法的中介作用下,爱就是弑父的升华:这就是儿子的命运。具体的反抗,抽象的服从,共同之爱。
重要的是要看到在这个辩证生成过程中成人礼的地位。儿子唯有在经历了代表着身体成熟的成人礼之后,才能进入最终的和谐秩序之中,身体的成熟需要经受折磨和死亡,我们非常熟悉其图像学上的命运。圣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无限上帝的激进形象化身为令人恐惧的凡胎。于是,当圣子通过“升天”的过程,返回圣父那里时,在复活的圣子身体上,留下了这一暴力行径的痕迹。
这就是严密一致的架构,乐观主义的哲人会满足于此,即便这个哲人是一位无神论者,因为它保留了三个阶段的观念,并最终走向了人类命运和谐的形象。
今天的问题在于,这个架构在两个方向上同时遭到了摧毁。在父亲一边,因为今天将父亲视为真实的和象征的父亲有点难度,至少他儿子很难这样来看待。事实上,我今天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儿子眼中的父亲。所以,我会说,作为快感的父亲和作为律法的父亲。 父亲成了一个成问题的形象。作为快感的父亲,今天父亲会反过来嫉妒儿子的快感。事实上,这就是现代青年崇拜现象――崇拜青年的身体,他们的身体不仅仅是崇拜的对象,而首先是一个主体。长期以来父亲被描绘为一个苍老的甚至有些淫逸的男性。很明显, 如果从当代社会中的快感角度来说,今天,这种形象几乎消弭于无形。这样,我可以说,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尽可能让老年人消弭于无形。真实的父亲逐渐地在社会中难以见到。与此同时,在儿子目光的凝视下,象征化的父亲的处境也很尴尬,因为最显著的律法如今都在儿子之外。这种律法就是市场的律法,其特征就是通过一个看不见的规则,让一切东西与其他东西等同起来,结果,父亲的形象与之决裂了,儿子的控制本身就是一个反象征。他们不可能自我建构出父亲的律法,对他们来说,这是公正的。无序,同时是非存在和溢出的,儿子们的社会控制与象征权力分离了。
现在,我们是否会认为,父亲是唯一的想象?或许存在着没有上帝的基督教的胜利。圣子上升到故事中的新英雄的地位,在商品化的现代性中,这个英雄是时尚的、消费性的和再现性的,这些都是年轻人的天生属性。但没有上帝,也意味着没有真正的象征秩序,因为即便儿子们掌管一切,他们如今也只能做类似的事情。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对儿子来说,由于已经被视为一个父亲,因而想建立一个稳定的身份是十分艰难的。事实上,儿子的身份是晃动的,因为他的辩证法被打破了。这个辩证法之所以被打破,并不是因为其基本形象消失了,而是因为儿子的身份发生了分化,彼此间有了距离。
让我们来描述性地分析一下。儿子的基本结构,就是“黑帮”,即著名的令人闻风丧胆的“青年黑帮”。顺便说一下,它再生产了弗洛伊德所谓的帮派(horde),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被视为社会灾难的根源。问题很清楚,这是无父的帮派,因此,不可能进行救赎性的谋杀,兄弟间也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让帮派成员在行动上(他们一起攻击父亲)彼此间达成默契的并不是契约,其连贯性来自模仿性的分工。帮派是有分工的,有自己的帮规。这些分工也是一致和类似的,因为其目的就是在无穷无尽的贸易、购买还有非法交易中促进商品流通。它是辖域化的(territorialisée),但这次的辖域化是对称的:领土就是其他有争议的领土的镜像形象。帮派只创造了一种不变的游牧主义。在这里,这一次,一旦帮派前进,他们的攻击就不可能被终止。他们不可能仅限于基础性行动。他们会不断地重复非基础性行动,最终这些行动是由死亡驱力支配的。
关于儿子辩证法的第一阶段就讲这么多,在这个阶段发生了攻击。
第二阶段怎么样?在这一阶段中,儿子服从于律法。当然,儿子与帮派的帮规也有关联,但要分开来看,一方面,在惯例、着装、语言、手势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表达上的规定,再一次在类似的模仿中消化了律法。另一方面,有一些惯性的律令,它仅仅规定单纯的自我感知,而不是变革的行为,在永恒的消极状态中,让惯性不断地持续下去。行为上的律令让儿子们的契约变成了商品中的交换,作为法律的律令则成为惯性的生产。
儿子辩证法的第三阶段,产生了成人礼。成人礼即从法律的外部成为其内在之物。它不再是让某种其他景象成为可能的东西。相反,它让儿子们变得呆滞。这就是刻板化的实践,最终走向集体对惯性的接受。成人礼,与把你当作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它滋养的是永恒成年的神话。
结果,儿子与成人、儿子与父亲的和解,只能通过让成人变得幼稚来实现。将它反过来,似乎是可能的。在最初的基督教神话中,就有圣子的升天。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父亲堕落的经验过程。
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神话的辩证图示崩溃了,结果,那里没有关于儿子身份的清晰表述。这就是今天世界上儿子身份的不确定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