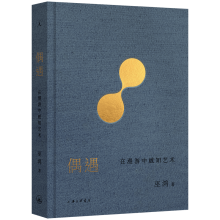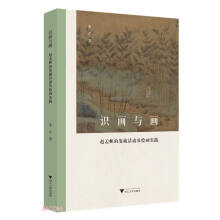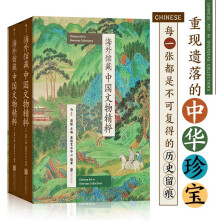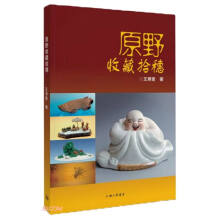《透物见人: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夏商周青铜器以其庄重典雅的造型、繁缛富丽的纹饰、神秘玄奥的内涵而闻名于世,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青铜器艺术,“直至今日,还被全世界的艺术家认为是古代东方艺术的精髓。它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当不在古代希腊之下”。不仅如此,青铜器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对夏商周历史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郭宝钧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青铜器, 而当时的风俗好尚、意识形态、工艺水平、文化进程也蕴育其中。”马承源先生进一步明确提出:“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商周青铜工艺还是指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尺度。”近年来,“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的相继开展为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研究创造了新的氛围。这些课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相关研究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化艺术等广泛的领域。
青铜器的纹饰更是20世纪初以来青铜器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外学者对青铜纹饰的内涵和意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西方一些学者,如罗越(M. Loehr)等人曾经认为这些纹饰纯属装饰,但大多数学者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装饰艺术,其蕴涵着丰富的时代内涵,正如《左传 成公二年》云“器以藏礼”,所以多数学者都对青铜器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内涵产生了较大兴趣,倾毕生心力而为之,为青铜器的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但是,三代青铜器的神秘内涵并不是一种或几种图案的解释所能阐释的,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对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必须对上述全部(即青铜器上所有的动物纹样)而不是几个特征做出说明。”然而,要想解释它的全部特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认为,要想理解这些纹饰的真正含义,对它的装饰艺术的系统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马承源先生就认为:“全面研究青铜器的艺术装饰,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朱凤瀚先生也曾经指出:“商周青铜器纹饰不仅有艺术价值,而且也是可借以了解古代社会意识形态不可忽视的实物资料。”的确如此,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是青铜器研究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是对三代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填补,诸多课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另外,就三代审美观念方面,目前涉及较少,其研究还相对薄弱,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的研究。朱剑心先生早就提出青铜器纹饰对认识三代审美观念极为重要,“ 如三代之鼎彝, 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审美观念对整个社会的大众生活、社会心理、艺术文化及精神价值诸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所以正确认识商周时期的审美观念对于理解青铜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就选择这一课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希望在对青铜器装饰艺术作全面系统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三代审美观念也做一些探讨。
目前,学者或从青铜器纹饰的概述上或从个别纹样的角度对青铜器装饰艺术作了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的确,夏商周青铜器上的纹样是青铜器装饰艺术的最为重要的部分,诚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这些纹样“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可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可见纹饰在青铜器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而作为青铜器装饰艺术,不能仅仅局限于纹样的研究。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包括哪些方面?所谓装饰,装者,藏也,饰者,物既成而加以文彩也。装饰艺术就是按照装饰表现规律并运用装饰性的符号和手法,融会于艺术、设计多种途径而形成的综合性的造型艺术形式。就青铜器来说,其装饰艺术主要是指在青铜器表面添加些富有艺术性的构件、纹样、符号和色彩,而使青铜器产生更为美观的效果,起到美化造型、突出造型、增强艺术感染力的作用。因此,其研究内容不仅涉及青铜器的造型、纹样的题材,而且装饰的工艺方法和装饰艺术的表现形式(包括平面纹样类装饰、立体雕塑性装饰、文字性装饰和其他漆绘、镶嵌等所形成的色彩性装饰等)都是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装饰艺术是可以有巨大的思想和精神力量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青铜器装饰内容的风格演变,探讨三代人们的审美观念的嬗替,正所谓“透物见人”。
三代的青铜器发现相当多,而且种类也很复杂,难以述及,但许多学者都认为,青铜礼器中的容器类是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最具典型性,因此,我们选择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容器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时代上从夏代到战国时期。通过对青铜容器的造型、装饰题材内容、装饰工艺及其表现形式等方面的系统疏理,揭示三代审美观念的流变。
本书所选青铜器主要来自考古发掘出土并经正式发表的资料,也采用了个别传世的青铜器资料,所引用资料具体来源均作了脚注。
第二节有关青铜器装饰艺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夏商周青铜器艺术作为夏商周文化的载体,历来备受学者重视,就目前资料显示,青铜器研究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对于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伴随着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不断有新的进展。
一、宋以前古代文献记载
早期涉及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主要是对个别图案纹饰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文献,主要有《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左传 宣公三年》中王孙满回答楚庄王的一段话:“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体。”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商周青铜器纹饰要“象物”,而且“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杜预注:“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可见,商周青铜器上装饰图案之复杂,而且这种装饰纹饰具有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体”的功能。
《韩非子 十过》曾记由余之言:“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 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 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 ”。
虽然注疏者多以为木器雕花,但从现代考古发现看,至迟在商代“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应是指青铜器的装饰而言,况且木器也不能流传上下几千年。另外,我们从这段话中还能了解到髹漆工艺可能也已经作为器物的一种装饰形式了。
《吕氏春秋》中多处都有关于青铜器纹饰的记载,所记述的纹样题材有饕餮、象、窃曲、鼠、马等,如“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先识》)、“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慎势》)、“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适威》)、“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不阳者,亡国之俗也”(《达郁》),在这些图案纹样中,虽然鼠至今未见,但对饕餮、窃曲之形象稍有述及,并沿用至今,而且也给予这些装饰图案哲理修养上的阐释。可以说,《吕氏春秋》在有意无意间成为先秦时期对青铜器装饰研究较为丰富的著作。
两汉到宋初,青铜器在文献中仍有不少记载,如《汉书》《说文解字》魏晋时《梁书》等均有记载。但涉及其装饰艺术的,较为少见,仅个别文献偶尔提及一些装饰纹样的题材内容。
《史记》卷四三有关于龙纹的记载:“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艺文类聚》卷第六十一记班固《西都赋 宝鼎诗》中也有关于龙纹的记载:“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敲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纭。焕其炳兮被龙文。”这两书中对青铜器装饰图案之龙纹有少量记载,说明汉代对青铜器装饰图案中的龙纹有所认识。
唐韦应物《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中有“江南铸器多铸银,罢官无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错盘,地中岁久青苔寒”等诗句,从中可以约略了解,诗人应该对“蟠螭”纹样有了一定认识。
据典籍记载,东汉郑玄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而著《三礼图》,其中有青铜器装饰图案的重要资料,惜已失佚。五代周世宗令聂崇义集诸家旧说校订而成《新定三礼图》,保留了一些较有价值的青铜器纹饰资料。
总的看来,在宋代以前,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仅限于个别文献对个别装饰纹样的记载,间或述及其功能,既零碎又少创见。
二、宋、清金石学者的启蒙性研究
北宋建国后,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但统治者采取了“守内虚外”的策略,重用文臣,转武功为文治,提倡经学,以复礼制;重视发展学术文艺,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宋代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繁荣,出现了大批富裕的地主士绅,他们对日常生活也追求一种精雅的玩味,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石学的兴起,青铜器的研究在此时才真正开始。金石学主要偏重于著录和文字考证,正如吕大临《考古图》所言“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所以,宋代青铜器的研究多用于“证经补史”,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王厚之(《钟鼎款识》)、赵明诚(《金石录》)、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等。但其中一些学者对青铜器装饰的图案的命名、分类及内涵等作了相关探索,可以作为青铜器装饰艺术的启蒙性研究。
吕大临著《考古图》十卷,卷首自序作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但据考证成书当在十年后,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青铜器学的学术著作。所收之器选自秘阁、太常、内藏以及私人收藏等,共37家,收录青铜器211件,其中商周青铜器148件。按器物用途分类,每器摹刻图像,有铭文者摹刻铭文,并附一篇说明,并记录器物尺寸,重量、容量、出土地点和收藏者。《考古图》对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最大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结合纹饰的形象对青铜器装饰纹样命名,如书中记述的青铜器纹饰名有饕餮、云气、牛首、兽首、螭、龟、象、虎首、龙等,并根据青铜器纹饰来命名青铜器,如云鼎、牛鼎、象尊、虎彝等。自此学者对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开始重视,有铭文即以铭文命名,无铭文则以主要纹饰命名,兼顾器形特征,也是后世通行的青铜器命名法。二是该书视纹饰为青铜器的有机组成部分,描摹器形时同时摹绘器上纹饰,亦成为后世青铜器著录的通例。
王黼《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宋徽宗敕撰。大观初年开始编撰,成书于宣和五年(1123)之后。收录当时皇室在宣和殿所藏,自商至唐青铜器共839件。按器形分为20类,每类有总说明,每器有图像,并摹写铭文,文字说明,记尺寸、容量、重量及铭文的考释,集当时流传和出土青铜器之大成。这部书对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更为重视,指出了一些象生性动物纹的装饰意味,如“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饰焉”。另外,对装饰纹样的含义研究尤为重视,如“象饕餮以戒其贪, 作云雷以象泽物之功,著夔龙以象不测之变”“以蟠蛇为之饰,亦以示其不可妄动之意”“蝉又取其趋高洁而不沉于卑秽”“山以取其仁之静,花以取其礼之文”。此外,《宣和博古图》继承并发展了吕大临《考古图》的纹饰研究成果,新命名夔龙纹、麟纹、蟠虬、蛇虺、蟠夔、旋纹、垂花等纹样,又将螭纹分为蟠螭、蛟螭、立螭,雷纹之中分出细雷纹等。
这两部著作在青铜器装饰纹样的命名、分类和内涵上用功颇多,且最有成效,为后世青铜器研究拓宽了思路。但由于其“证经补史”的主要目的的局限性,决定了青铜器装饰艺术还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元、明两代,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用力不多,仅有个别学者对青铜器的形制、铭文作了少量著录,对青铜器装饰艺术既无关注,更谈不上研究。
到了清代,清政府为禁锢人们的思想,大兴“文字狱”,推崇“朴学”,考据之学盛行,大部分学者“以考证古器铭文为学术之最”,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梁诗正《西清古鉴》、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荣光《筠清馆金文》、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端方《陶斋吉金录》等。其中,涉及青铜器装饰艺术的仍以对纹样的描绘为主,《西清古鉴》中记有盘云、云龙、垂云、云螭等纹饰名称,钱坫和吴云均对器物装饰的主要纹样作了摹绘。
由上可见,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在清代及其以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其研究也不够全面深入,但已引起部分学者注意,对其装饰纹样给予一定的分析、理解、命名和简单的分类,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