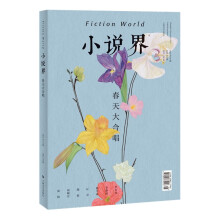狂欢节
帆船匠吉尔波洛克已经结婚一年了。他在湖边有着相当可观的产业:一座房子,一个农场,一座花园以及一些土地:奶牛在棚子里“哞哞”地叫,鸡和鹅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猪圈里关着三只今年就要杀掉的大肥猪。
吉尔波洛克虽然比他的妻子年纪大些,却更迷恋热闹欢愉的生活。结婚以来,他们几乎整日流连舞池。吉尔波洛克时常说,“只有傻瓜才把结婚看成受罪,对不对,亲爱的小玛丽?”一边说着,一边用粗壮的胳膊拥抱他丰润的妻子,“要我说,生活的乐趣才刚刚开始。”
的确如此。除了玛丽怀孕的最后六个星期之外,结婚的第一年对他俩来说仿佛是一个无休止的大派对——这六星期也只是稍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已。生完孩子之后,每当清风伴着华尔兹吹进这间偏僻的小屋,他们便兴冲冲地去参加舞会了,孩子则留给祖母照顾。
吉尔波洛克夫妇不仅自己村子的舞会场场不落,连周围村子举办的舞会都很少缺席。即便祖母卧病在床——这种事时有发生——他们也有办法把这个“小尾巴”带去参加舞会。他们在舞厅中找个角落,把孩子放在两把椅子上面,用披肩和围裙包裹起扶手来遮挡灯光。在震耳欲聋的乐器声中,在人群嬉笑喧嚣声中,在酒气与烟雾缭绕之中,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假如在场的人感到惊讶,帆船匠总是这样回答:“这才是吉尔波洛克的儿子,懂吗?”如果小古斯塔夫哭了起来,他的母亲就会赶在一首曲子结束之后立刻把他抱进冰凉的门厅里。她会坐在楼梯的台阶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把她那因为喝酒跳舞而热得滚烫、喘息不停的乳房送到孩子的嘴边,孩子则贪婪地把乳汁吸吮一空。喝饱之后,小古斯塔夫常常会露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这让他的父母感到一丝满足。孩子的兴奋十分短暂,他很快就沉睡下去,直到第二天早上。
夏天和秋天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帆船匠走出家门,发现白雪覆盖了整个大地。松树的枝桠全白了;大雪包围了湖泊和村庄,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
吉尔波洛克十分喜悦,因为冬天是他最喜欢的季节。白雪让他想到了白糖,白糖又使他联想到格罗格烈酒;格罗格烈酒常常被摆在节日里温暖明亮的房间中;最后他又想到冬天里那欢庆不渝的节日中去了。
望着那些缓慢移动、吃力前进的小船,他暗暗地笑了,因为湖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马上了,”他自言自语道,“冰马上就会结得厚厚的,我最美妙的日子要来临了……”
如果把吉尔波洛克先生看成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他比所有人干活都要努力。不过一旦湖面封冻,船舶相关的活计整月地停止,他也丝毫不会抱怨,默默地寻找一个庆祝的好机会。
吉尔波洛克嘴中叼着短烟斗,烟斗中喷着一团团烟雾;他慢慢地走下斜坡,来到了湖边。他用脚轻轻地踩了一下冰面,——出乎他的意料,冰面突然裂开了。尽管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试了试,但还是差点儿就掉到湖里去了。
他捡起掉在地上的烟斗,咒骂着往回走。
一个一直观察他的渔夫朝他喊着:“帆船匠,你想滑冰了?”
“有什么不行的,这就是一周之内的事儿!”
“那我可得去买一张新渔网。”
“为什么呢?”
“我得把你捞起来啊,你肯定会掉到湖里去的。”
吉尔波洛克爽朗地笑了起来。正当他要回敬渔夫几句时,他的妻子喊他回家吃早饭了。在回去的路上,他琢磨着洗洗冷水澡也不错,他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呢。
吉尔波洛克夫妇一起吃着早饭。
老祖母坐在窗前慢慢地喝着咖啡,时不时地微微张开双眼,担心地瞧着脚下搁着的绿色小箱子。此刻,她正颤抖着细长干枯的双手,打开身边的小抽屉并来回摸索,直到她用手指夹出一芬尼硬币,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脚下那个小箱子的铜质箱口中。
就如平常一样,老人找到夫妇俩忘记替她收起的硬币时,她那严肃、憔悴的面孔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吉尔波洛克和他的妻子看着这一幕,彼此会心一笑。
就在昨天,这个年轻的妇人又把一个马克兑换成了芬尼,开心地向她的丈夫展示这一堆硬币。
“母亲可是个称职的储蓄罐,”吉尔波洛克一边说着,一边热切地盯着那只绿色的小箱子。“谁能想到这个箱子里还有很多钱呢?要是她去世了,我们就会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一点你大可放心。当然上帝保佑她不死。”
吉尔波洛克的话令他的妻子感到十分愉悦,她站了起来,一边扭动着身体,一边哼起歌来:“我们一起去非洲,一起去喀麦隆,一起去安哥拉……”
一阵突如其来的狗吠打断了她的歌声。家里那条棕色的小狗洛基因为靠近绿色的箱子,被老人狠踢了一脚。小狗一瘸一拐地钻到壁炉后面,不停地发出呜咽的惨叫。这情景惹得夫妇俩笑个不停。
老妇人不住地咒骂这条狗,吉尔波洛克朝着他听力不好的母亲喊道:“母亲打得好,它胆敢嗅你的箱子,别说是猫狗了,任何人都不应该碰它!”
“她有她的智慧,”吉尔波洛克一边得意地说着,一边随着妻子走进院子,看着她给牲畜喂食,“我们一块钱都不会少的,对不对,小玛丽?”
玛丽开始麻利地搅拌饲料,尽管天气寒冷,她还是把袖子和裙子边高高地挽起,健康、丰腴的四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吉尔波洛克满意地瞧着他的妻子,同时为母亲的悭吝而带来的无形财富感到开心不已。
此时他无心干活,满心陶醉在这种愉快的情景中。他眯起眼睛,打量着肥猪厚厚的脊背,好像它们已经变成了火腿、香肠和熏肉了。紧接着他巡视了被白雪覆盖的院子,在他的眼里,这个院子就像一个盖着白色桌布的大餐桌,上面摆着烤鸡、烤鹅和烤鸭,尽管它们目前还活着。
他的妻子玛丽在给家禽悉心地喂食。孩子的哭声从房子里传出来,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让她不得不停下手边的活计。在她看来,家禽的健康兴旺是她生活的首要目标,而孩子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而已。
狂欢的日子来到了。全家人一起享用着下午茶,一岁的小古斯塔夫在地板上玩耍。所有人的兴致都很高,究其原因,一则是煎饼美味,二则今天是周六,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是村里化妆舞会的日子了。
玛丽打算扮成一个农妇,她的衣服早已经准备好,挂在熊熊燃烧的灰色大壁炉的旁边。从上个月罕见的寒潮开始,壁炉里的火一刻也没有熄灭过。这次的大寒使得湖面封冻了起来,哪怕满载货物的卡车也可以安全地行驶在上面。
祖母和往常一样,蜷缩在窗边她的宝贝旁边;小狗洛基趴在壁炉门前面,火光映红了它的身体;壁炉中不时传来噼啪的响声。
今天的舞会据说是这个冬天最后一次盛大的娱乐活动了,自然要玩个痛快了。
到目前为止,这个冬天过得十分惬意。他们只做了几次小活,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家或是别处的的节庆、舞会和宴会上。慢慢地,积蓄越来越少,牲畜也明显少了很多,但他俩的情绪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一想到来年夏天过后的丰收,他们就感到十分地舒心;只要瞥一眼祖母的绿箱子,种种焦虑也瞬间一扫而空。
老人脚下的绿箱子,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对他们夫妇俩产生极为安慰的力量:即便猪感染了瘟疫,想到它他们就平静下来;就算帆布涨价或者生意变得难做,他们也会想起这只绿箱子,焦虑马上烟消云散。
他们似乎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绿箱子上,一旦家里的收入受到影响,他们就开始梦想着打开它——那简直是一生中最美妙的一刻了!
他们早就规划好如何使用箱子里的钱了。首先,他们打算来一场为期一周的愉快旅行,就去柏林吧!小古斯塔夫就在家里呆着,他们打算把他送到湖对岸的施泰本村的亲戚家去。
每次提到这次旅行,他们都感到万分喜悦。吉尔波洛克认为这可以算作第二次蜜月旅行,而他的妻子则回忆起少女时代的记忆,滔滔不绝地讲起莱恩茨马戏团,哈森海德和别的什么好玩的地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