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陌生人说话/鲁迅文学获奖者小说丛书》:
不久,母亲亲手安排了两人的见面。为了准备这次见面,母亲带着春华到裁缝店做了一件带金丝线的两用衫,这是当时县城最时髦的布料了,衣服做好后,挑剔的母亲又逼着裁缝修改了两次,最终合体得像从春华身上长出来似的。正式相亲的前一个晚上,春华带着点羞怯地试衣服给大家看,大双小双小五一个个都喜欢得张大了嘴巴,秋实在一边闹着,说一定要借给她穿到学校,秋实那时刚上高中,爱穿衣打扮的心思一天比一天强烈。母亲一边趁机训斥着秋实,一边拿手指用力戳着父亲的肩膀,父亲从他的灯下抬起头,好像第一次见到春华似的围着春华看了一圈,母亲满脸得意地看着他,等着他称赞,父亲笑了几声,却突然有点悲哀起来,他很轻地说:这是春华的顶峰了。小五听不明白,想象中应当是句夸耀的话吧,母亲却沉下脸来:你不会学喜鹊唱,就非得叫声乌鸦调么!次日的相亲正如母亲所愿,两方你情我愿、一锤定音。后来的事就都按部就班了,陈善材会隔三岔五地带着小礼品来看望父母,春华也经常会穿戴得漂漂亮亮地单独跟陈善材出去看电影或到红梅公园玩上大半天。陈善材是个面面俱到、讲究细节的人,话虽不多,但每句话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一看就是在机关里待了很久的人。母亲对此非常得意,认定这是陈善材前途无量的最好证明。可能是出于习惯,他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就连小五端杯茶给他,他都会抬起屁股表示谢意。每次约春华出去,他都会让春华带回来一些好吃的零食,这让小五非常高兴,因为秋实最近嫌自己太胖,基本不吃零嘴了,大双小双两个虽然先天不足一直是瘦条子身材,但她们却喜欢围着春华听她讲电影故事,所有的零食基本上都由小五独享了。
但小五并没有因此对陈善材有更多的好感,因为小五现在开始明白父亲的那句话了,的确,订婚之后的春华好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尽管后来她又添了一些新衣服和漂亮的丝巾,频繁的约会也使得她的脸色更加红润娇嫩起来,但是奇怪,小五就是觉得春华变丑了,特别是她身上的味道,好像开始混浊厚重起来,夹杂着一丝陌生而可疑的气息。这让小五有点伤心。
春华结婚那天,小五第一次穿上带花边的新衣服,可是从后来的全家福照片上可以看见:她挂着小脸挤在大人们脚边,看不出一丝喜气。春华出嫁了,小五第一次体味到家人之问出现的这种以喜庆形式出现的分离,尽管只少了一个人,但小五觉得:家不完整了,像缺了一个角的月饼。小五去翻春华桌子下的纸篓子,她找到了大姐在这个家中最后一次扔下垃圾:一副旧的洗破了的假领子;内衣的空包装盒;一块皱皱巴巴的手绢;几张被剪坏的红喜字。小五看了看,又飞快地闻了闻,然后悄悄地收起来塞进她抽屉的最里边。
最先从别离中恢复过来的是秋实,因为春华出嫁之后,留给她不少衣服,她不顾母亲因为春华的出嫁而筋疲力尽、悲欣交集的状况,甜言蜜语地央求母亲帮她把春华的衣服一一改小,并在领子、袖口等细节处增加一些时新的变动。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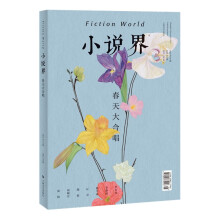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鲁敏或许是近年来对小说艺术的可能性具有探索志向的年轻小说家。她沉迷于对人性的无限想象,她相信人有能力在各种复杂境遇中以各种意料不及的途径探求和确证自身。她坚信,人的感受、思想和行动的无限可能,并使小说获得了角度、形式、语调的无限可能,由此,她为自己的写作确立了复杂艰巨、令人满怀期待的难度指标。
——“庄重文文学奖”授奖辞
鲁敏关切复杂的都市生活,独辟蹊径,敏锐地探索人的精神疑难。她不避尘埃,与她的人物一起经受困惑和考验,在短篇小说有限的尺度内开拓出丰厚深长的心灵空间。
——“鲁迅文学奖” 授奖辞
人性“暗疾”是鲁敏顽强探索的重要主题,并通过某种普遍性使之构成了生活的整体荒诞。这是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她的书写不是“原生态”的呈现或欣赏,而是被视为一种“精神疼痛的历史”。这同时也构成了鲁敏的一种历史表达,那幽暗的色调和宣泄般的冷眼,本身就蕴涵在历史之中。
——孟繁华(批评家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鲁敏的小说不仅仅呈现了混乱的人间世事本身,还挖掘出在细节、情节之下的隐秘秩序,体现斑驳中一种清晰的辨认,不露声色地探究这混乱的来由,之后,是虽然弱小但分明不绝如缕地坚韧存在着的自我抗争意识——正是这样,她怀着体恤写活了在变化甚至动荡情境中人的日常遭际,尤其是被命运和世事裹挟的中国式“成人礼”。
——施战军(批评家 《人民文学》主编)
鲁敏站在中国小说艺术的前沿。她将确切的戏剧性形式赋予涣散的、难以言喻的复杂经验,探测和呈现精神生活的结构、深度和边界。鲁敏的写作,是对小说艺术在这个时代面临的艰巨难度的有力回应,她思考和检验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由此表现出纯正鲜明的艺术信念和夺目的、训练有素的艺术才能。
——李敬泽(作家、文艺评论家)
鲁敏对人们精神“暗疾”的揭示,不同于以鲁迅为典型代表的“国民性批判”,后者有着更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性内涵。而鲁敏所揭示的“暗疾”,虽然并非与社会性因素完全无关,但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一种心理性的表现。它似乎植根于人性深处,或者说,也是“普遍人性”之一种。这样一种对人性的观察和把握,自有一种独特的价值。
——王彬彬(学者、文艺评论家)
鲁敏小说体现了一种折射的美景,只有角度技巧才通向那里,我们通过叙述者的“眼睛”来认识这庄重而又有点荒谬的世界,从双重玻璃的折射中窥视囚室的出口。鲁敏有妥协并经常地自得其乐,但不难看出的是,她似乎更珍爱其越轨、犯忌与亵渎的部分。
——程德培(作家、文艺评论家)
在如今强大的“写实潮流”与世俗趣味间,她顽强地葆有了形而上的追求,这使我感到一丝振奋。正如艾略特所说,谁能够在“传统”和“个人潜能”之间找到恰当的关系,谁就能够成为好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我对鲁敏寄予着期望。
——张清华(文艺评论家)
鲁敏是那么热衷于对暗疾“显微”的书写。《取景器》在鲁敏小说的独特意义就在于此:鲁敏开始变换理解视角去重新讲述一个“老故事”。
——张莉
我站在一个三十层的写字楼里,从办公室向外俯瞰,可以看到正下方各种各样的人,看到他们的头顶:官员、小贩、警察、司机、送水工、餐馆侍者、幼稚园老师等等,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方向坚定、匆匆忙忙,像奔流不息的水一样冲洗、腐蚀着整个城市。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的头顶、人们的头顶,像在大海中那样起起伏伏,某种激越的情绪突袭心头,如惊涛拍岸。
在目光所及之外,每个人都有一团影子那样黑乎乎的秘密,有着被镣铐所深锁的内心。可能就是那些深渊般的秘密内心,一下击中了我。像是积蓄多年的火山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迫切地想要贴近和占有他们的哀戚与慈悲。这就需要一个合法的工具。比如,一台高倍的、夸张的乃至有些癫狂的望远镜,给我以无限刺探的自由和权利。或者,一根细长的绳子,我可以顺着它,垂坠到人性深处。而当时我所能想到的工具,就是:小说。
——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