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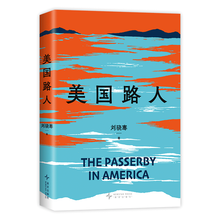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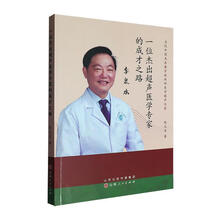


1.王鼎钧、徐晓、陈芳明等重磅推荐,台湾著名作家尉天聪重塑战后台湾人文精神史!
2.本书与《半生为人》《燃灯者》《暗夜传灯人》共同组成一幅两岸三地文化脉络图。
3.尉天聪刻写近代台湾文坛23位作家,让我们懂得那时代知识分子寂寞及悲壮之所在。在那窒息的年代,有人燃起一把火,火便开始传递开来,于是他们在光与火与苦难中,淬炼出台湾文学的篇章,那么悲痛,却又何其温暖,照亮了一个不屈的世代。
一个悲不敢泣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你们能想得到吗?尉天聪刻写近代台湾文坛23位作家,让我们懂得那时代知识分子寂寞及悲壮之所在。
在那窒息的年代,有人燃起一把火,火便开始传递开来,于是他们在光与火与苦难中,淬炼出台湾文学的篇章,那么悲痛,却又何其温暖,照亮了一个不屈的世代。
不管那些过往的日子是多么令人感到沮丧,而我们自己当年又是如何冲动、幼稚,甚至盲从,追根究底,却可从另外某些人有形或无形的所作所为中体认出,那并不只是一段空白的岁月。
苍茫独立唱挽歌
说高阳
高阳常说,他之所以成为一位历史小说家,其实是很偶然的。 他原名许晏骈,杭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族自清乾隆以降即功名不断,至嘉庆、道光、咸丰后更有官至刑部尚书、 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者。他曾对我叹说 :“出身于这样的家族,承 受这样的传统,到了民国时代,报考大学,攻读的应该是法律系或 政治系,但我多次翻阅了族中所保存的一些档案资料,听多了长辈 和族人谈论的官场旧事,吓得我把法、政视为畏途。”他问我 :“这 样一来,你说我应该走哪条路 ?”我也只能摇摇头。他接着说 :“处 于这样紊乱的世局之下,我只好做一个无聊的文人 !”
这样消极的话,乍听是一种自嘲和无奈,仔细体会,却是一 种悲愤,一种自悔和反省,使人想到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那一类的话 :一种对人生难以解说的感 喟。高阳平生最爱两个人的诗,一是李商隐,另一是吴梅村 :其 所以如此,大概是在这两位前人那里,感受到与自己相似的遭遇。 李商隐身处晚唐乱局,吴梅村夹在明清交替之际 :都对时代有着无可奈何之感。吴梅村尤其如此。于是,高阳之于吴梅村便更有 难以为言的同情。他说 :“看梅村诗集,怀古纪事,吊死伤别,无不充满了沧桑之悲、身世之痛,哪怕是咏物的诗,多半亦有寄托。”
这话似乎也可借以解说他自己的作品。从许晏骈而到“高阳酒徒” 的高阳,虽然在诗文、言谈之间经常挥洒自如,但其间那种自我 贬抑的语气却令人不能不感慨系之。正因为这样,他论到一些处于 两难之局压力下的知识分子时,便经常说他们只好用“别的方法” 来“抒写史书中所无法表达的深厚情感”。依高阳之意,这里所说 的“别的方法”就是诗与小说。
在前辈学人中,高阳最心仪陈寅恪先生。陈是史学大师,晚年 在目盲孤苦之中,却把治史的功力转移到《论再生缘》《柳如是传》 那一类作品的写作上。何以如此?这当然有其深意存焉。高阳既以 陈寅恪为师,他的历史小说应该也是在其中有所寄托的。有一次我 问他,在他的众多历史小说中,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部?他毫不 犹疑地说 :《荆轲》。进而解释说 :别的作品,即使毁掉了,仍然可 以重新写得出来,唯独《荆轲》,却是再也无法重写出来的。那种 青少年时代的梦,那种狂热,今天再也找不到了。即使以今天的眼 光来看,这部作品在文字的处理上还有粗浅的毛病。
我说 :“一谈到荆轲,一般人多着重在高渐离送行的‘风萧萧 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一类的诀别。你却在荆轲死后更 引出张良,而且借由张良的口说出‘我要嬴政知道,失败不足以令 人气馁,杀身不足以令人畏惧 :防范越周密,手段越恐怖,越有人 要反抗他’。又说 :‘荆轲以后有荆轲,张良以后有张良 :身可死, 志不减 !’真亏你写出这样的豪语。”
他却说 :“这不是我的豪语,这是中国历史的精神。钱穆先生 有一句话最让我信服 :读历史必须具有最起码的感情。我的一切都 是从那里孕育出来的。”
我认识高阳及高阳的作品也是偶然的。一九七二年,赵玉明兄出任《民族晚报》总编辑,约了我和一些朋友写专栏,每天赠阅《民 族晚报》,我得以阅读刊载在那里的高阳的历史小说《翠屏山》。那 原是《水浒》中杨雄、石秀和潘巧云的故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施 蛰存也曾经改写过。报上登出高阳这部小说连载的预告,我立即起 了一个疑问 :《水浒》已把这故事写得那么细致易懂,在京戏和地 方戏中也早已把它们确定下来,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他再去发挥?及 至看了他的新本,才了然于他吸引读者之处。他书写《翠屏山》中 的潘巧云是这样推展出来的 :一个绝代美人,先嫁给一个粗俗不堪、 夜夜鼾声大作的屠户,那是如何的遭遇!等那男人死了,改嫁的又 是一个钢刀一举人头落地的刽子手,那种感觉又是多么动人!高阳 的创造力与想象的灵活,不得不让人惊叹。而且他观察事物的角度 非常准确和细腻,使得他的语言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和生动,让读者 不由自主地想一读再读。
就这样,从《翠屏山》开始,我成了高阳的读者,也去找他之 前的作品来阅读。那时我在大学教授中国古典小说。由于受陈寅恪 的影响,我讲唐人传奇时便把唐代的社会制度拿来探寻小说中所未 说到的一面 ;也由此而发现高阳改写《李娃》的结尾别具用心,把 故事改放在唐人真实的门第人际关系上,而与唐人原作的安排有所 不同,把历史小说提升到史学的层次,使人想见故事背后的更真实 的一面,令人对小说的结局有着更多的思考空间。有一次我去拜访 台静农先生,谈到台湾当时的小说界,先说到白先勇,他说 :“先 勇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才华也够,但对于中国社会认识还不 到深刻的层次。”于是我向他推荐了高阳。过了一段日子再去看他, 他告诉我已经看了几本高阳的作品,并且说 :“他对中国社会很有 认知。他写《乌龙院》不着重在男女之事,而去写那些刑事书吏间的种种明争暗斗,而在《小白菜》中经由男女间的故事,书写杨乃武那样的讼棍文人与官场之纠葛,并扩及太平天国事件后湘人与当 地人在两江一带的矛盾,以及慈禧想借此一事件来借刀杀人,压低 湘人在江浙的势力。这些,没有功力是写不出来的。”我向台老说 出高阳的出身背景,他说 :“这就难怪了 !”
高阳当时不少作品都在《联合报》连载。一九七六年我在联 合报系所办的《中国论坛》担任第一任主编,开始与高阳有了往 来。那时正是高阳创作的高峰期,一系列有关明清之际的作品陆续 出世。有一次,也在联合报系任职的陈晓林邀了一些朋友餐会,座 中除了高阳,还有唐鲁孙、夏元瑜、阮文达、赵玉明等人。由于唐 鲁孙先生是前清光绪皇帝珍妃和瑾妃的侄孙,年少时曾多次进出宫 门,对旗人生活极为了解,听他言谈,获益不浅。于是晓林提议, 这样的聚会不妨每月举行一次,这就等于不着痕迹地每月上了一堂 历史课。由于这样地跟高阳交往多了,也就熟悉他的酒徒风范,言 谈之间渐渐领略到他读史、查证资料的用功程度。但他见到唐、夏 两位前辈,一直是诚诚恳恳地虚心求教。唐老为人谦和,谈笑时也 会在自我解嘲中流露出严肃感。有一次,他两杯酒下肚,就对高阳 说:“人家都说咱们是封建余孽,遗老遗少,但当封建余孽、遗 老遗少,也得先吃点苦,磨炼磨炼。就拿皇帝来说,也得规规矩矩 先把字练好 :奏折上来了,要看得懂,要会批。师父要上讲了,当 皇帝的就得先站在御书房门口等候,师父坐定了,皇帝才能落座。” 并指着我们年轻的几位说 :“读《红楼梦》你们很多地方不会真懂, 在其间,每一个事件都显示着一种文化,一点粗浅不得。”
唐老的每一言辞、每一行动都持平稳重却又那么自在,即使在举杯、持箸之时,也自有其风度,连服务人员递上一杯茶,他都用温婉的眼神回应。他的北京话不疾不徐,毫无一般人所想象的贵族 气象。在这样的言谈之间,高阳与唐老的对谈一直保持着虔诚的态 度,有时候谈到的虽是一些细微琐碎之事,也能感受到他们想在其 中探讨挖凿某些奥秘。
在高阳的作品中,历史的时空,往往只是一个架构,他最大的 着力点往往不是一般人视为“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反而是一 些人不太注意的小事件、小动作,让人流连、惆怅、会心一笑并有 所领会。譬如在《胡雪岩》中,王有龄出任官职,想要在端节之前 接任,胡雪岩向他建言延到节后去接。王有龄本想在接任后立即承 受大批“节敬”,胡则主张把这一机会让给前任 ;一来,结交人缘, 为前程铺路 ;二来,来日方长,何愁没有机会。像这样的一件小事, 即可让人体会到为官之道的奥妙。由此扩大联想,也就让人对人性 的好坏多了一层了解。
高阳历史小说的特色之一是他常常在真实的历史人物中穿插一 些他所创造的小人物,而且以女性居多,使得其间的相互关系及他 要呈现的场面更为生动而深沉。如《荆轲》中的荆轲与夷姑、《醉 蓬莱》中的洪升与玉英、《徐老虎与白寡妇》中的徐宝山与白巧珠、《胡雪岩》中的胡雪岩与芙蓉等等。他们之间的相遇、相处,都在 整部作品中呈现出沉重的力量。特别是《醉蓬莱》,它的主题原是 经由洪升的《长生殿》剧本,书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 读了以后让人感叹的却是洪升与玉英无法结合的缺憾。
这就涉及高阳的爱情观。在高阳的作品中,几乎每一部小说中 相爱的人最后都是徒然。《李娃》中的郑元和与李娃、《风尘三侠》 中的虬髯客与张出尘(红拂)、《再生香》中的顺治皇帝、冒辟疆与董小宛、《小凤仙》中的蔡锷与小凤仙、《曹雪芹别传》中的曹雪芹与《红楼梦》诸女子,所呈现出来的无不是那种无所求、无所得, 却一心流露着无限关爱的情操。高阳大多以淡笔写浓情,使得结局 虽是徒然,却让人获得珍贵的感悟 :人生只要能够实心实意地爱过 也就足矣。例如《风尘三侠》中,当红拂对虬髯客说出“从今以后, 你忘掉我,我忘掉你”时,那场面真把人带领到一种“隐忍”的美 学境界 :
“一妹 !”虬髯客站住脚,以极平静的声音问道 :“你还有话 说 ?”当着上百的仆从,她无法说一句心里要说的话,只俯下身去, 用纤纤双手,挖一掬土 ;使的劲太猛,折断了两个指甲,痛彻心扉, 然而她忍住了,终于挖起那一掬染有鲜血的泥土,眼泪扑簌簌地流 着,也都掉在那掬土中。
“三哥 !”她哽咽着说 :“你要想家,就看看这个吧 !”……
有一次与高阳闲谈,两杯酒下肚,我对他说 :“高阳,在你的 作品中,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有一位温柔、体贴、互相了解的 女子,化为很多分身经常出现在你不同的作品中,甚至有些名字都 雷同。那是你的梦还是你的回忆 ?”他只是苦苦地一笑,默不作答。
但我猜得出他的心情。那不仅指的是个人的际遇,推展开来, 更是整个民族处在历史变动的际遇。他平日最爱李商隐和吴梅村的 诗,而且用力甚勤。他常经由他们的作品体认他们平生所处的两难 之局 :个人的感情如此,世间的种种际遇也是如此。而在不知何去 何从时,有时只有在漂泊中度过。他注解吴梅村的《短歌》说 :“做 官潦倒,头白归乡,谁知在家乡却更不如在异乡漂泊!这是何等哀 痛的描写?”这无疑也涵盖着高阳个人的感慨。他用心于明清之际上人的处境,当然也有感于民国,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变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去从,陈寅恪写《柳如是传》,他写《江上之役诗纪》 都是经由南明的败亡而有着相近的吊古伤今的心情。吴梅村遗言 说 :“吾一生遭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 实为天下大苦人 !”其所以要忍受这种悲“苦”,实际是要在有限的 人生维系着某些不容扭曲的认知和真情。这认知和真情是绝对不能 用现实政治利益和阶级标准来判定的。而且,这才是最真实的历史。 所以在陈寅恪的历史书写中便处处见到很多人经由历史对当代所生 的感慨。在这方面,高阳似乎也与陈寅恪有着相似的感受。他想经 由历史去体会一些什么,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他才一再说,人生 的最大引力是“情”,其次才是“缘”。而且,他又补充说 :不要把“情”和“缘”讲得世俗化 ;历史的不停转变,很多事之所以在人 们心中打下难以泯灭的烙印,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有一次谈到当今人的人生态度,他说 :“现代人,常常把世间 的一切事都视为偶然,子女是父母做爱偶然生的,夫妻是偶然碰在 一起而结合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天设地配,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必然 的相守相爱的关系。这也就没有什么必然的道德伦理可言。这是彻 底的虚无主义,视一切为荒谬。”对此,他大不以为然。所以在高 阳的小说中,人生的际遇经常是偶然的,但在这偶然中,由于彼此 所付出的爱和关心,它所产生出来的关系和情操却一一成为无法割 舍的必然 ;让人愿意为之忍饥受冻,生死以之。即使男女之欢乐场 合的相遇,产生的也是难以忘怀的思念。说起来,这些都是微不足 道的小人物、小事件,汇合起来却是历史的主流。在这里,历史之 所以为历史,主要的便是在琐琐碎碎中所显现的、连续不断的生命 情调和相互关怀。不分古,也不分今,一直不断地绵延着。
有一次,《联合文学》邀请一些作家作中南部之旅,特别向铁路局包了一节车厢,同车还有无名氏(卜乃夫)、夏志清等人。在 车上我曾跟高阳聊到对历史的认知。我质疑司马迁把《伯夷列传》 置于列传之首的用意。司马迁谈到道家之言 :“天道无亲,常与善 人”,又感慨伯夷、叔齐这样的善人最后均遭饿死,这是对天道与 人世的怀疑,而这样的怀疑主义必然导引出历史的虚无主义,认为 世间并不存在公道与不公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由得让人怀疑 : 历史所给予人的意义是什么 ?
高阳回答说 :正因为如此,才能见出最真实的东西。正因为人 生无常,经由战乱、屠杀、斗争、欺骗、丑恶,才能见出比这些更 高的东西,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的“存在”;即使那是刹那的,也 会叫人难忘,成为永恒。
我说 :“这样一讲,我们也可以把李商隐的诗拉大到这样的层 次去了解 :‘相见时难别亦难’不正是人在尘世上的‘追寻—怀疑— 沉沦—觉悟’的历程吗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 就写尽这一历程的辛苦吗 ?”
高阳同意我的引申。他说他坚决相信,在历史中虽然处处充满 着暴乱和不公,好人不长寿,坏人享荣华,但在每个人的心里,何 者该做,何者不该做,总还是应该有所肯定的。想一想,这倒是真 的。在他的作品中,很多人物的结局都是不如意甚至悲苦的,从荆 轲到曹雪芹、洪升,乃至胡雪岩等人的人生结尾,几乎都是挫败的, 然而就另一面而言,却又存在着生死以之的庄严意义。例如《小凤 仙》中,当小凤仙听到蔡锷忍受着贫苦煎熬时,对于他一步步往“死路里走”的决心起了质疑,不禁问道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得到的回答却是 :“为了争人格——替全中国四万万人争人格。”就 此而言,历史不但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永续的精神 :在高阳的历史小说中,他是以人的品质来反省历史的。这些品质随着客观环境的不同,有时隐忍下来成为伏流 ;有时奔腾不息,成为主流 ;源源 不息就成了生命中的源头活水。然而,很多人却无视于这些。高阳 因而感叹地说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现代人经常以政治的、党派 的观点来审判历史,不但审判而且予以定罪,让人上天下地在精神 上找不到容身之处。”
就此而言,高阳对于历史的看法是非常不同意西方正流行的历 史主义 ;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在根本上是否定人世间有某种永恒 的、持久不变的东西,认为人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人们不停变化的 欲望,而在高阳看来,历史中虽然充满斗争、屠杀、侥幸、投机, 但就在其中却处处让人感受到有值得为之奋斗、牺牲的崇高和神圣 的价值存在,让人领会到生命的庄严意义。
高阳小说最让人叹服的是文字与对白的精妙。有一次在一场 文学奖评选会上与高阳和无名氏同席,高阳说了一段与文字有关 的话。他说 :小说之为小说,它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叫人看得进去。 看得进去就是亲切感。不但情节的安排要这样,连语言也是一样。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的写作都有粗糙的毛病,以为只要从嘴 里说出来的口语就是白话,不知白话不管指的是官话还是普通话, 从古以来因个人的身份不同、生活习惯的差异,都有各自不同的表 达方式,也各有独自的韵味 ;失掉这些,语言就干枯无趣。文字要 有诗的情趣才有美感,这是连介系词、尾词都马虎不得的。另外一 点,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常以意识形态挂帅,这是“莲雾打针变 成黑珍珠”的手法,不足为取。
因为看多了高阳的历史小说,就止不住有时也会对他的作品 提出意见。有一次我对他说 :“西方史学家都把世界近代史开始的时间放在十七世纪前后,独独中国学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放在一八四○年前后,认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才开始走向 近现代。这是外铄式的观点,失掉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萧一山 先生、胡秋原先生都不赞成这种说法。如果我们也赞成中国近现代 史开始于十七世纪前后,则明清之际正是一个关口。你的小说从《再 生香》的多尔衮率清兵入关,到《小凤仙》的袁世凯当皇帝,这一 系列作品,真是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写照 ;把中国明末清初以来的, 官僚社会的贪婪无能、吏治社会与帮派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广大群众 的愚昧,写得淋漓尽致,但也在优良的传统中,令人感到无限的温 馨。这些都有助于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如果把这一系列作品加以整 理,再给予一个总名,真可以和法国巴尔扎克(H.Balzac) 的《人间 喜剧》那一系列作品媲美,同时也可作为旧中国的挽歌。”他听了 非常高兴。又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 :“你这个人太好酒,有时 酒喝多了,为了赶写副刊连载续稿,一时赶不及就乱放野马,写些 典故趣闻凑篇幅,虽然也很有趣味,但整体来看总不够严谨,何况 不时还有重复的地方。应该整理一下。”
那次的谈话竟引起他的重视。他想在这一系列前再写一部小 说作为开篇,彰显一个时代的开始,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为他讲了 全谢山在文集里记载的关于钱敬忠的故事。钱敬忠的父亲钱若赓是 明朝的临江知府,因为抨击万历皇帝选妃的事被关在狱中将近四十 年,每年都是斩监候,受尽煎熬。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家破人亡, 连孩子也是在狱中长大的。钱敬忠一岁入监,在狱中接受父亲的教 育,后来考中进士。他要求代父受刑,钱若赓才被放了出来,年纪 已经八十了。此后,钱敬忠历经李自成之变和满清入关,亲身带兵 对抗,最后失败,绝食而死。全谢山在谈到写作之道时,曾经说过 : 文章中保留太多资料会破坏文的气势,但他却在书写钱敬忠时,故意把那些有关资料一一保留下来。其所以如此,就是想要后人经由资料中的琐琐碎碎见到历史中人性的光芒。他为钱敬忠写的碑铭, 非常动人 :
孝思已申,忠则未遂 ; 墓门流泉,潸潸者泪 ; 故国河山,同此破碎 ; 试读予文,寒芒不坠。
我问高阳 :“如果我们不以肤浅的什么封建意识来评定它,便 可以在其中见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明代是历史上最腐烂的一代, 也是在腐烂中最显现人格的一代。不知这一类的故事可不可以提供 给你来参考。”
那是一九九二年初的事。没隔多久他就因病连续出入医院。不 幸的是天不假年,本应人生七十才开始,一生背负着历史积郁的高 阳,却在那年六月六日以七十之龄告别了人世!
他过世之前接受《联合报》副刊访问时还特别说 :“我最感谢 尉天聪教授勉励我做中国的巴尔扎克……”
周弃子先生曾赞赏高阳以“苍茫独立四垂际”的诗句来描绘自 己的际遇。如今高阳已经逝世十五周年,每当想起他,脑海里浮现 的,就是一个微屈着背、苍茫独立于挽歌声中的寂寞身影。
百年冰雪身犹在•001
苍茫独立唱挽歌•013
找回失去的星光•024
素朴坦然一君子•034
土地的守护者•045
依旧是鹅湖风采•054
孤寂的旅程•068
他影响了那么多人•080
怀想那一段岁月•093
无名氏最后的日子•102
燃烧的灵魂•112
悲悯的笑纹•125
寂寞的打锣人•134
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148
府城的李白•179
独步的狼•189
诗人与同温层•202
掉进猪笼草的飞虫•208
那个时代,那样的生活,那些人•217
苦行的旅者•232
江湖寥落那汉子•243
去奚淞家看画•260
怆然的回望•273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落寞的学者,孤寂的作家,又从苍茫的历史迷雾中走出。不为人知的感情,不易察觉的思考,再次涌动。那种力道,在回首时,产生一种重量。来回行走在他的文字之间,简直是穿越一部战后台湾的人文精神史。
——陈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