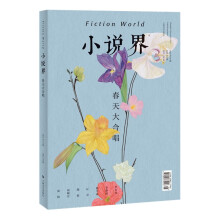不错,昨天晚上的行为并没有超越过所谓的实质性界限。也就是说在肉体上没有什么伤害。可这又能说明什么,那天早晨几乎把她推入绝地的也并不是肉体的毁坏。
和昨天晚上是多么的相像啊,不过是男女又方换了位置,把粗暴强迫改成了温柔的引诱。
也许把这样两件事联系到一起是荒唐的,没有道理的。
梅子也不愿这样想。所以想到了以后,便觉得事情严重了,便有些慌乱了。
可是再一想,恰可拜怎么会和一个脆弱的女孩子一般见识呢?
他是在能拔掉大树的暴风中连腰都不弯的,是曾掐住了狼脖子挤出它的眼珠子的,是翻越过连山鹰也不敢栖息的冰大坂的男人。
他肯定会以西部荒野汉子大戈壁一样宽广的胸怀把这件事放在一个极不起眼的位置上,他会像宽容一只一时迷乱了方向的小羊羔一样仍旧像过去一样对待她,一样在每个黄昏里都来她的酒馆里坐坐,永远也不多也不少地只喝那么一小怀酒。
可这也是她的猜测,她对这件事结果的希望并没有什么把握,也没有什么证据。
于是在这整个一天里,她都在紧张地等一个时刻的到来。
早早就准备好了一盘牛肉和一碟花生米还有一杯酒。她想好了,她还像过去一样,连表情都不能有一点改变,对着他淡淡地一笑,她要让他感到一切都和过去一样,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用不着多费一句言语,决不能解释,那会更糟,做到了这些,大家就会和过去一样照原来的样子把时光打发下去。
表上的指针终于对着那个钟点了。
注意听,没有听到往常这个时刻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心紧了一下,仄起耳朵再听,仍是没有动静。正发愣,腿被什么碰撞,低下头,先是一惊,后是一喜。
狗。他的猎狗来了。
猎狗抬起头用舌尖舔着她的手。
这么说他也来了,还是来了。
抬起头,注视着门帘,等着它被一只粗大的手掀起。
等了一会儿,不见门帘动。
等不及了,干脆出去迎接,猎狗紧随身后。
站在门口,往一条细细弯弯的小路上望,望到小路的尽头,仍是没有望到想望到的。
低下头,看看狗,狗也看看她。
想问问狗,想好没有吐出口,只是轻轻地摸了狗的头。
不会是病,他是强壮的男人,从来没有生过病,哪怕是一次轻微的感冒受凉。他的身体就像铁打的一样。
那他这会儿到底在哪儿,在想什么,在干什么?
梅子的心一下子没有了底,一个劲往下沉……
顾不上那么多了,梅子反身把酒馆的门关上并挂上了锁。
连围裙都忘了解,便沿着小路走去,开始只是碎碎的快步,走一会嫌太慢了,干脆小跑起来。猎狗也跟着跑起来,不然就会被她拉下的。
跑上了开满野玫瑰的草滩。
夕阳里翻滚彩色的草浪里看不到一个人的影子。
梅子把双手握成喇叭状放到嘴巴上,尔后用最大的嗓门喊着恰可拜的名字。
那名字像一只失群的孤雁在天空焦急地悲哀地飞着,在苍茫寂静的空旷里投下一重重影子般的回声。
在喊了十几遍恰可拜的名字以后,像是从那浑圆的落日里弹出来的一样,一匹马从西边的地平线上奔驰而来,枣红色的皮毛在火一样的夕照里,像一个划破黑夜的火把极耀眼地跃动着。
马儿站住,从马背上跳下一个牧羊少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