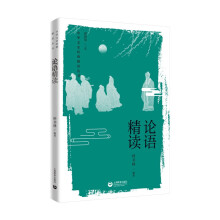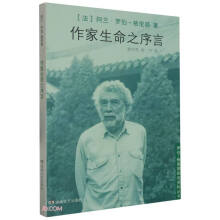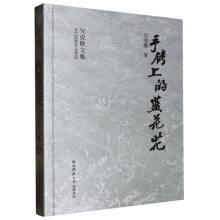东京的古寺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东京没有“古寺”。东京的寺庙本来不少,可经历江户时代的三大火事,再加上本世纪的关东大地震和美军大轰炸,难得一见百年以上的建筑。即便不计较多次的翻修与迁移,江户开府至今不到四百年,东京的寺庙能“古”到哪里去(《浅草寺史略年表》溯源到七世纪中叶,可屡建屡烧,目前的本堂是1958年落成的)?难怪许多到过京都、奈良的游客,对东京的寺庙不屑一顾。半个多世纪前和哲郎记录游览奈良附近古寺印象的《古寺巡礼》,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名著;淡交社正在印行的大型系列图录《古寺巡礼》,也以京都、奈良两地为主。手中有一册角川书店编的《图录日本美术》,收录并简介被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雕刻、绘画、工艺、建筑,是我游览古寺或博物馆时必带的“指南”;其中十六世纪以前部分基本与东京无缘。
谈论考古和艺术,“时间”具有绝对的价值。一千多年前的佛像,不管多么粗糙,只要能流传至今,便有惊心动魄的魅力。“文物”之所以显得“古雅”,小半赖人力,大靠半天工。不必“嗜古之士”,一般人都会对此类能引发思古之悠情的“文物”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东京是贫乏的──博物馆自然除外。对于曾经在长安城根拣过秦砖汉瓦、或者在西域路上遭遇“秦时明月汉时关”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感觉尤其突出。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不从“考古”而从“历史”、不从“艺术”而从“人情”来品读,东京其实不乏值得一游的“古寺”。叹息东京“古寺不古”者,大概忘了历史时间的相对性。倘若东京的古寺能帮助我进入历史,阅读我所希望了解的江户文化,那又何必过分计较其年龄?今日的东京,到处是高楼大厦,想追寻江户时代的面影,还真的只能借助这些不太古老的寺庙。“江户东京博物馆”固然让我动心,也给了我许多有关“江户”的知识;可我更愿意在香烟缭绕的寺庙边,抚摸长满青苔的石碑,似乎只有那样才能真正感觉到“历史”的存在。
当初不大满足于“博物馆文化”,主要是考虑到其中凝聚了太多的专家的理性思考,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限制了自家想象力的发挥。野外作业有惊险,有失败,也有意料不到的“发现”──在专家或许不算什么,在我却可以陶醉好几天。精鹜八极,神游四海,尚友古人……一觉醒来,眼前依然是东京的高楼大厦。既不感伤,也无惊喜,对自己笑一笑,上图书馆去也。
很快地我就明白这里的陷阱:东京的“野外”其实一点也不“野”,我的作业对象并非“原初状态”。寺是重建的,墓是重修的,碑也有不少是重刻的。除了地震和战争的破坏,还有重建时整理者有意无意的“歪曲”。常会诧异江户人为何不讲礼节乱搁石碑,事后想想,可笑的其实不是整理者,而是我之“信以为真”──呈现在我面前的并非“真正的历史”。明白了这一点,“古寺巡礼”时便有了双重的考据任务:既考古人,也考今人对古人的理解。带上一册“江户古地图”(此类图书甚多),还有安藤广重的“名所江户百景”,在东京街头散步,不时会有莫名其妙的叹息或微笑。
相对于观赏国宝级文物时的“焚香顶礼”,摩挲路边饱经沧桑的石灯笼或者街角略为残缺的地藏菩萨,心情轻松自由多了。没那么多谦恭,也没那么多虔诚,用一种通达而又略带感伤的眼光来看待古人和今人,思维自然活跃些。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古今对话中,“艺术美”逐渐为“人情美”所取代。所谓“线条”、“结构”、“韵律”等的思虑,实在抵挡不住佛家的“大慈悲”──起码在东京的寺庙里是如此。比如,位于目黑的大圆寺里,有一尊很不起眼的道祖神像,在墙角的大树底下“乘凉”。此乃中国的行路神,在日本则专管儿童和爱情,故刻成男女合体“勾肩搭背”的浮雕。我不知道这一对矮敦敦、胖乎乎、笑嘻嘻的小儿女组成的道祖神是否真有法力,一瞬间竟把我“镇住了”。无暇借问作者是谁,也不想考据创作年代,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充满稚气的神像里,蕴含着对世俗人生的热爱、以及周作人所再三赞叹的日本之“人情美”。
东京寺庙之所以让我流连忘返,很大程度正是这种充溢其间的“人情”。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浅草寺、增上寺,还是我居住的白金台附近的若干“无名”小寺,都是有信徒、有香火、有佛事、因而有生命的“活寺”。我很看重这一点,这正是收藏丰富的博物馆所不具备的。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佛事,也见识了真真假假的信徒,自认对日本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大概是我逛寺庙的最大收获吧?
(初刊《中华散文》1995年第1期)
木屐
小时候不喜欢木屐,主要是嫌重,穿上无法快跑或者蹦跳,玩游戏时总吃亏。
上学了,按规定不能打赤脚,可抄近路需要跳水沟踩田埂,穿鞋实在不方便。把鞋带一结,挂在书包上,光着脚丫子在泥地上跑,挺舒服的。偶尔也把鞋挂在脖子上,但那必须是新鞋才好看。到了学校门口,擦擦脚,穿上鞋,一下子“文明”起来了。
十五岁那年当了“知青”,来到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小山村,终于体会到木屐的好处。村里的水沟不大通畅,加上母猪率领小猪东游西荡(肉猪可圈而母猪必须放养),一到雨天街上猪屎和着稀泥,只有穿着木屐才能安然无恙。村民一般早睡早起,夜里十点以后,周围静悄悄的,巷口传来木屐声,大半是朋友找我聊天来了。石板路上深夜走木屐,清脆又悠扬。失眠时,数着远处夜行人的木屐声,也能渐渐沉入梦乡。
久居城市,重做“文明人”,只好告别木屐。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木屐实在不方便;住楼房深夜踱步,楼下肯定抗议。当然也有“从众”的压力,不敢过于“招摇”。已经隐去了的记忆,读黄遵宪和周作人关于日本“下驮”的描述,才重新恢复过来。此次东渡,很想听听东京街头的木屐声,顺便理解黄、周二人之争议。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述及“声声响画廊边,罗袜凌波望欲仙”的木屐:
屐有如丌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两歧。
据黄氏考证,此乃中国古制,与其时尚流行于南方的木屐样式不同。周作人赞赏黄氏的观察,不过认定日本木屐的“梁作人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吾乡与黄氏家乡相邻,风俗相通,自是不能同意周氏的意见。穿木屐到底是夹着还是套着方便,很大程度是习惯使然。周作人将其归结为中国男子裹脚故脚指互叠不能衔梁,未免牵强。不同于黄遵宪的风俗介绍,周作人之《日本的衣食住》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很能体现其个人趣味:
去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国大学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如今本乡东大附近旧书店仍在,可难得见到穿和服着木屐的读书人,更不要说“曳杖”了。
偶然在校园里见到一位着木屐的学生,看他上身西装,下身牛仔裤,肩上的书包前后晃荡,再配以踉跄的脚步,实在有点滑稽。那学生大概自觉很好玩,一路左右顾盼;我则从这颇具反讽意味的摹仿中,意识到木屐的“死亡”。
那天雪后初晴,我从东大回家,忽闻前方有念佛声。转过街角,见三位僧人各持一面小鼓,匆匆赶路。伴随着鼓声和念佛声的,便是那清脆的木屐声。大概出于苦行的考虑,天寒地冻仍不着袜。平日走路已属“匆匆”的我,赶上着木屐的僧人也都不易。踩着鼓点,跟在僧人后面念佛,直到实在跟不上才想起应该回家了。
于是,站在路边,目送渐渐远去的僧人,还有那木屐声……
(初刊1994年8月5日《南方周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