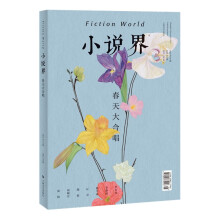俺爹传给俺的蛮干脾气,使俺从小就没少吃亏。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俺从学校的二楼上跳下来,挫伤了腰,足足躺了一个星期。也许有人会问:“为啥干那种傻事儿?”其实,也没啥了不起的理由。当时俺从新盖的二楼向外探头,一个同班同学便逗弄俺说:“不管你怎样吹牛,总不敢从那儿跳下来吧,你这个窝囊废!”当学校的工友将俺背回家来,俺爹瞪大了眼睛说:“天下哪有这样不争气的东西,大不了从二楼跳下来就挫伤了腰的?”俺回答说:“下次,俺再跳一回给你看,保证伤不了腰!”
一位亲戚,送给俺一把西洋造的小刀,俺在日光下晃动它那闪闪发光的刀锋,显示给同学们看。有个同学说:“亮是亮,可未必削得动东西呀。”俺马上保证说:“怎么能削不动东西?管它什么,削一下给你看!”同学提出:“那好,削一下你的手指头看!”“这有什么,手指头也不过如此!”说着,俺就朝右手大拇指的指甲斜着削了进去。幸亏小刀很小,加上大拇指的骨头又硬,所以,大拇指至今还留在俺的手上,可是伤疤却到死也去不掉啦。
从俺家的院子往东走满二十步,有一块南端稍稍隆起的小小菜园,菜园的正当中,栽着一棵栗子树,这是比俺的命还要紧的树啊。当栗子熟了的时节,俺总是大清早一爬起来就出后门,捡来落在地上的栗子,带到学校去吃。菜园的西边紧挨着一家名叫“山城屋”的当铺的院子,这家当铺有一个儿子,十三四岁,名叫勘太郎。勘太郎不用说是个窝囊废。别看他窝囊,却经常跳过方眼篱笆来偷栗子。有一天傍晚,俺躲在折叠门的背后,终于把勘太郎给抓住了。当时,勘太郎走投无路,便拼命地朝我扑来。对方比俺大两岁,虽是窝囊废,力气却很大,把他那大脑袋朝着俺的胸脯狠狠地顶来,顶着顶着,脑袋滑了一下,钻进俺的夹衫袖子里来了,绊住了俺的胳膊,用不上劲。俺拼命甩动胳膊,钻进俺袖子里的勘太郎的脑袋,也就跟着左右翻滚。最后,他受不了了,在袖子里朝俺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哟,这个疼呀!俺把勘太郎推到篱笆上,使了一个脚绊子,把他向前撂倒了。山城屋的地面比菜园低六尺左右,勘太郎把方眼篱笆压坏了一半,朝着他家的院子一个倒栽葱跌了下去,哼哧了一声。勘太郎在跌下去的时候,扯断了俺夹衫的一只袖子,俺的胳膊这才听使唤了。当天晚上,俺娘去山城屋赔礼,顺便把夹衫上的那只袖子也捎回来了。另外,俺还干了一大堆淘气的事儿。有一次,俺领着木匠家的徒弟“兼公”和鱼铺子的“角公”,将茂作大叔家的胡萝卜地给踩坏了。在胡萝卜秧出得不齐的地方,盖有一大片稻草,俺们三个人就在这上边摔了大半天的跤,胡萝卜地整个被踩得稀巴烂啦。还有一次,俺将古川家地里的水井管给堵上了,让人家吵到俺家里来。原来这是把大毛竹的竹节挖通,深深埋进地下,让水从竹管里涌出来的一种装置,它是用来灌溉那一片稻田的。当时,俺不晓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将石块和树棍狠命地塞了进去,一直塞到出不来水了,才回家来。刚吃上饭,古川就气得满脸通红,嚷嚷着进来了。记得好像是赔了钱,才算了事。
俺爹一点也不喜欢俺,俺娘只知偏向俺哥。俺哥长得白白的,喜欢模仿演戏,扮成花旦。俺爹一看见俺,总是说:“你这东西反正不会有出息。”俺娘也说:“你总是闯乱子,将来怎能叫人放心得下?”俺爹算是说着啦,俺是没出息,就像现在您看到的这个熊样嘛。俺娘说的“将来叫人放心不下”,也的确是如此。俺这个人,只差没有去坐牢,勉勉强强活下来就是啦。俺娘有病,在她死前的两三天,俺在厨房里翻筋斗,肋骨撞在炉灶上,疼得不得了。俺娘火冒三丈地说:“俺再也不想看见你这样的东西!”俺只好跑到亲戚家去住。就在这时,捎来了信儿,说俺娘终于一病不起啦。俺没想到娘这样快就会死去。假如知道俺娘的病是那样重,早知道俺稍微老实一点就好了。俺这样想着,回到了家。一到家,俺那个和俺合不来的哥哥就说俺不孝,为了俺的缘故,娘才早死的。俺气不过,给了哥哥一记耳光,挨了俺爹一顿臭骂。
俺娘死了以后,俺就和俺爹、俺哥三个人一起过活。俺爹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只要一看见俺,总是口头禅似的说:“你这个东西,不成器!不成器!”究竟哪点不成器,至今俺也弄不明白。天下真有这样古怪的老爷子!俺哥他说要当什么实业家,拼命学英语。他的性情本来就像个女人,很狡猾,俺和他处不来,每隔十天半月,总要吵上一架。有一次,俺和他下将棋,他总是卑鄙地预先埋伏好棋子,好把你“将”死,看见人家憋住了,他就得意地嘲弄俺。俺气极啦,将手中的“飞车”朝他眉心摔去,把他眉心划破了,流了点血。俺哥向俺爹告了状,俺爹说要把俺赶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