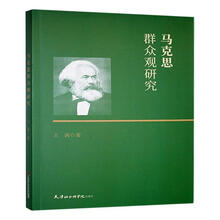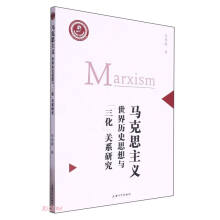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导言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社会矛盾的演变)反复地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这样一种困境:以往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突然失去了力量。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的理论也在那时成熟。20世纪50年代,“美国民主主义和自由企业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文明”这种理念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这种理念不遗余力地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描绘为美国民主主义的“邪恶的对立面”,但这种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陷入了困境。当非裔美国人的抗争揭示了他们受到美国“民主”的排斥时,其他群体所受到的排斥也就一目了然了。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1963)在《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中重新探讨了贫困。许多人,特别是许多年轻人,对美国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深深的不公平提出了质疑。越来越多的批评动摇了美国所承载着的无限可能性、上进心、机会均等、自由,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公平的憧憬。新一代的激进主义分子重拾过去的批评运动(为了和平、真正的民主和财富重新分配进行的批评运动),重新探讨被边缘化的社会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并形成了“新社会运动”(包括女性解放、少数民族及同性恋的公民权益,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越南战争草案曾经使数百万人面临巨大的个人损失及“体系”不公正。反战批评家和激进主义者重拾反帝国主义社会理论并构建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后来是老师),我们发现,大部分的老师(后来是我们的同事)和课程仍沉浸在对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理论的沾沾自喜中。为了批判他们,我们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这一非凡的百年之久的理论传统被冷战的歇斯底里(通常是通过妖魔化的形式)从大多数美国人的脑海中清除了,后者也扼杀了社会批判主义。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无数社会批判运动的经验积累出的大量结晶。人们很快明白,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至少是在重走冷战思想的老路,或者说得严重些,是在重蹈覆辙。我们随后意识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需要搞清在一些深刻问题上的困惑。他们首先要搞清的问题是:关于阶级这一核心概念与理论中以及关于理论的简单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导言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从多布(Dobb)、斯威齐(Sweezy)、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兰格(Lange)、阿尔都塞、列宁、卢卡奇和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作者入手,我们重读了马克思本人的文章,并最终重读了富有权威性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论》。在上述这些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作者中,我们更多地接触到的是将阶级视为配置/分配财产(贫穷还是富有)或权力(统治还是被统治)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是,通过阅读《资本论》,我们无比惊讶地发现了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全新定义,它引领我们开拓了一种新的社会理论。过去,我们曾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鼓掌喝彩,它准确地认识到了别人所忽视乃至诽谤的社会阶级差异。现在,按照剩余价值理念这一马克思置于其分析的中心位置的理念,我们了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如何压制了阶级概念的。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1)所有社会形式都会组织其中一部分成员生产剩余价值(产出多于生产者自身消费和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的那部分产量);(2)不同社会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如何生产、占有、分配其成员的剩余劳动。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指的是特定的经济进程(而不是政治进程或文化进程),它指的是生产、占有、分配剩余价值。阶级首先是一个形容词,它将这些剩余价值分配进程与其他社会进程相区分。因此,对我们而言,对任何一个社会的阶级分析就变成了揭示谁在社会中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谁从占有者手中获取剩余价值分配,以及社会大背景(其政治、文化、经济、历史)是如何与阶级进程彼此塑造的。这些都是关于阶级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重新又将这些问题引入了对社会(某一个时间点或某一个时间段)的分析中。这些都是被掩藏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的阶级问题,我们在阅读时要么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要么不认同它们。我们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提供了一条新线索,它能解释为什么美国社会中的不公正、不公平那么难以根治,那么具有毁灭性。首先让我们震惊的是,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阶级进程(一种唯一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分配主要是在企业中进行的)是如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保障了大规模的社会盗窃的。无偿劳动(窃取剩余劳动)是一种犯罪,它使得任何其他形式的盗窃相形见绌。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剩余价值剥夺者因此入狱或缴罚款。相反,这些窃贼还因其企业家才能、冒险精神或管理才干而备受尊敬。疯狂被当作了理性。下文中福柯的话将会深化这种理解,让我们明白,这种概念偷换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还会继续下去。在无偿劳动这种暴行之外,这类阶级进程还大大滋生了许多其他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从无情的商业周期到家庭危机,到社会冷漠的方方面面。然而,尽管犯了这些罪,促成了这些问题,资本主义阶级进程不论在通俗文化还是学术语境中都基本没有受到政治上的质疑,没有受到理论上的调查。比如,关于经济学的正规教育忽视或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上述问题的持续检讨是一种忌讳。我们有了一个计划,我们将从剩余价值角度对马克思独特的阶级理论做一个全面的陈述,展现出其与其他阶级概念(就资产和权力的社会分配而言的阶级概念)的不同之处。我们与阿尔都塞的意图相同,但又区别于他的哲学——我们将从剩余劳动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以这种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如果剩余劳动概念被设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我们在下文称为“切入点”的东西)的构成核心的话,作为对立面,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即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理论)的构成核心又是什么呢?我们早期的两本书(1982a,1986a,1987;Wolff and Resnick,1987)中的文章讲述了这些想法。一旦从剩余价值角度对阶级进行基本的概念化之后,我们将打算把它运用于现代社会:美国和苏联,以展现它们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如何构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我们的计划很快扩展到了构建马克思那远远欠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理论。我们先前已经认识到,大多数社会具有很多个不同的、相互共存且相互影响的阶级进程,既有非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也有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我们所追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分析不会忽视各个阶级结构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影响。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家庭会不会也是生产、占有、分配剩余价值的场所?按我们的方式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使我们意识到,不同的社会场所可以,也经常会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阶级结构。例如在美国,我们发现,企业除了主要扮演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之外,也会扮演非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如自我雇佣,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古典”阶级结构),而家庭则主要扮演封建阶级结构,但也扮演其他一些非资本主义阶级结构(Fraad,Resnick,and Wolff,1994b)。在苏联农业史中,我们发现,农场具有私人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国家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古典阶级结构以及共产主义阶级结构(Resnick and Wolff,2002)。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每个个体可以,也通常会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他可以是生产者,也可以是占有者和剩余价值的分配对象,这取决于他在家、在单位、和在其他社会场所被放在哪个阶级结构中。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发现阶级政策、阶级斗争、阶级转换的概念都变了(1994b;Resnick,2001)。我们的计划演化成了一个全方位的阶级分析。它旨在讲明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处于不同社会场所中的、复杂多样的、相互影响的阶级结构构成了所有社会的结构和动力。这一理论随即可被运用于特定的社会,得到特定的见解(这是阶级分析所赋予的)——它们是分析的见解,具有深远的、引人注意的政治寓意。马克思热情洋溢地拥护的社会变迁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在批评资本主义和其他阶级结构的同时,我们也提出,其他阶级结构也可能对社会公正、公平起积极作用。但马克思对他所钟爱的阶级结构——共产主义——的构想和描述在理论上很不完善,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所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也没能修正这一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些概念常常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总的来说与马克思所提出的以剩余价值论阶级的理论不一致。我们也注意到了由此产生的担忧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不同解读所产生的划时代的成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以及至少部分地由上述这样一些观点所构成的社会进行解读和互动,我们有了另一个计划:解释清楚为什么左派的平等主义目标及民主目标同样需要上述成就以及共产主义阶级结构(工人们共同占有、分配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从一开始,我们的研究就同时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方面,针对非共产主义阶级结构(特别是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我们构建了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构建社会。另一方面,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构建了共产主义阶级结构(1988,1994a,2002)。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