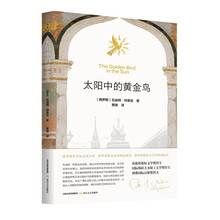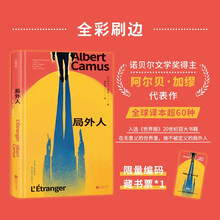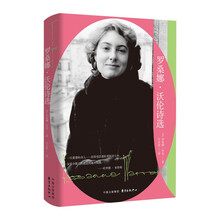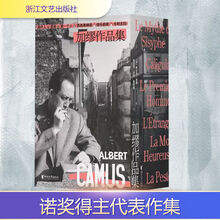个性与智性
我在爱尔兰的工作时不时地会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我如何才能让我的工作对朝气蓬勃的普通人产生影响?他们的注意力不在艺术之上,而在商店,在国立学校的教学,在分发药品上。”我不指望着能“鼓舞他们”或是“教育他们”,当然仅就这些词语的字面意思而言,而是想让他们理解我的想法。我不指望能拥有大批观众,当然更不是所谓的全国观众,而是期望有一批人愿意为了偶然的、短暂的事物驻足留步。在英国,人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接受诸多系统的教育,不过人们要摆脱学生那种鲁莽行事的方式,做事情不能仅有三分钟热度。真正的观众是能够认真倾听的。我总是十分确信:艺术中真正感动普通人的东西,就是生活中让人感动的东西,例如个人生活的强度,在书本或戏剧中呈现的语调,一个人可能会在市场或药房门口激动不已时表现出来力量。他们借助赖以生存的力量走出剧院,这种力量因某种激情会得到增强。无论选择哪种生活方式,这种力量都能击败敌人,让人存够积蓄,或是打动一位女子的芳心。他们同科学推测无紧密关系,即使有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同形而上学也无多
大紧密关系,即使有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如果心中的情感是模糊的,那么他们走在路上,身体就会感到疲惫不堪。尽管拥有对花的爱慕之情是非常迷人的事,那也不能把车从沟里拉出来。一位令人激动的人,无论是戏剧中的英雄还是诗歌的创作者,都会尽最大努力展现最多的个人能量。这种能量必定看起来像是来自身体,又像是来自心灵。当我们想象一个人物之时,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所赋予他的生活所必要的所有能力是否有其根源?”只有当人们确定这一点时,人们或许才能给他一种能力,让想象充满快乐的能力。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哪一部戏剧足够受大众欢迎,以致都不需要充分利用其主角的身体能量。如果“罪犯”维庸[1]以及爱尔兰人接受同样的语言和象征符号传统,那么他或许就可以用戏剧和颂歌来取悦这些爱尔兰人,但是雪莱就做不到。随着人们进入城市生活,阅读印刷书籍,开展许多专业化活动,那么要创造像雪莱这样的人物就变得越来越容易,而要创造像维庸这样的人物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维庸式的诗人是罗伯特·彭斯。拥有最高能力的人渐渐消失,带着美感进入某种缥缈的天堂,留下那些低能力的人缓慢吃力地前进。在文学中,
由于缺乏能把我们同正常人联系起来的话语,我们失去了个性,失去了作为完整个人的乐趣——血液、想象、智慧融为一体——但是,我们在本质、心境、纯洁想象以及很快就能让我们陶醉的优雅音乐中找到了新乐趣。摆在文学面前的是两条路——扶摇直上,变得越来越微妙,例如维尔哈伦、马拉美、梅特林克,直到最后在有教养且勤奋的人中达成一种新共识,这种新共识会造就一种新激情,看起来像文学的事物成了宗教;或者一路向下,带着我们的灵魂,直到一切事物再次变得简化和统一。那是最佳选择——像鸟儿一样,飞到普通人看不到我们的地方,或是飞到货车旁。但是我们必须确保灵魂陪伴着我们,因为鸟儿的歌声悦耳,现代想象的传统也变得越来越悦耳,越来越抒情,越来越忧郁,出现了雪莱、斯温伯恩、瓦格纳。这种现代想象的传统或许就是某些人的狂热,这些人会看到神父德·维拉尔斯出版的神秘赞美诗中提到的生活的王冠和耀眼的钻石。要是货车打破了我们
的幻想,我们必须将灵魂紧紧束缚在我们的身体中,因为灵魂变得越来越喜欢数代人不断累积起来的美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人会厌烦对纯粹力量、纯粹个性的渴望,厌烦对激动人心时刻的渴望。如果它开始慢慢离去,我们必须将它追回,因为雪莱的晨星小教堂比彭斯的啤酒屋更好——当然,它是啤酒,而不是大麦——除了在疲惫不堪的夜晚。它总是比那些不舒服的地方要好,在那些地方,没有啤酒,即现实主义者的机械商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