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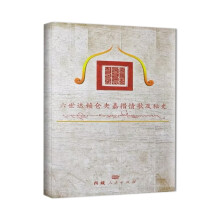




(1) 《豹变》——木心生前的“心愿之作”,木心身后的“木心小说选”
木心的短篇循环体小说《豹变》十六篇,属于汇集而成的长篇作品,不是短篇小说集,而是现代主义文学常见的一个类别。可参照海明威短篇汇成的《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同类书在国内出版的较少,但在20世纪世界文学里,已有安德森、海明威、福克纳的著作,这样结构成书。
相比海明威,木心也是擅长短篇的作家。2011年,好友童明翻译的英文版木心小说An Empty Room(《空房》)在美国出版,而这个短篇循环体小说计划,则早在1993年夏天,木心与童明(今《木心诗选》编选者)即已全部酌定中文版《豹变》这十六个短篇,在挑选并重新组合之后,就是一本完整的小说,木心的心愿也在此。这是飞越二十多年的“文学之约”。
(2) 《豹变》——木心的“一本薄薄的厚重礼物”,隐含“一个艺术家的精神成长史”
《豹变》首版的印刷纸张,自欧洲引进,触感自然,色泽柔和,便于纸质版的翻阅,也接近木心早年的民国书籍体验。书名“豹变”,源自《易经》“君子豹变”,隐含一个艺术家的精神成长史,是由弱到强的过程,全书则交织着《哥伦比亚的倒影》、《温莎墓园日记》、《即兴判断》、《巴珑》、《爱默生家的恶客》等木心著作,这是一本薄薄的厚重礼物。
木心有俳句,“我常与钻石宝石倾谈良久”,其眼光独到,看重的多是思想家,如老子、孔子、耶稣、蒙田、爱默生、尼采等。这碎片体也是欧美先锋派的创新之一,现代诗歌*突出的碎片体,当属艾略特的《荒原》,它以审美的陌生感挑战惯性思维,唤回现代生活时常忘却的美学经验,又在美学思维的探索中将碎片接了起来。短篇循环体小说,妙处也可相参。
木心的短篇循环体小说《豹变》,不是短篇小说集,而是一种特殊类别的长篇小说,根植于欧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
按木心生前的心愿,《豹变》 依次收入十六个短篇——《SOS》、《童年随之而去》、《夏明珠》、《空房》、《芳芳No.4》、《地下室手记》、《西邻子》、《一车十八人》、《同车人的啜泣》、《静静下午茶》、《魏玛早春》、《圆光》、《路工》、《林肯中心的鼓声》、《明天不散步了》、《温莎墓园日记》。各篇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相连,成为有着自己的结构原则的特殊作品,海明威著作即有此类 a short story cycle,照英语译为“短篇循环体小说”。
《豹变》的故事描写的是个体的人,大致看得出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几个人生阶段。私人经历又对应着战前、二战、二战后、建国后、打开国门等阶段,需要在这些历史背景中思考。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阶段:走出国门后的西方世界。
此外,《豹变》收入编选者童明的长篇代序,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如何看木心文学的世界性,从中也可见童明跟木心从1993年夏酝酿,先有美国英文版An Empty Room(《空房》)的十三篇出版,到木心诞辰九十周年,终有中文版全貌十六篇问世,这是飞越二十多年的“文学之约”。
书名源自《易经》:“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豹变是由弱到强的过程,隐含一个艺术家的精神成长史。
【代序选摘/童明】
木心自己的短篇,以哲思和情感互为经纬,叙述的不仅是故事,是散文、诗、小说之间的文体。木心的文字像是暴雨洗过一般,简练素静。深沉的情感,冷淬成句,呐喊也轻如耳语,笔调平淡而故实,却曲径通幽。他善反讽,善悖论,善碎片,善诗的模糊,善各种西方先锋派之所擅长,用看似闲笔的手法说严肃的事理(这一点和伍尔芙夫人相似),把本不相关的人和事相关起来,平凡中荡起涟漪,有中国散文的娴雅,有蒙田式的从容,更把世界文学中相关的流派和传统汇集一体。《诗经演》在海外初版,木心曾以《会吾中》为题,是这个意思。
《豹变》的碎片感,皆因各篇质地相异,形式灵活,结构近于海明威式的“断裂原则”。换一个文学例子比喻:有一种发源于古波斯的诗体,叫“加扎勒”(ghazal),两句为一诗段,七个诗段以上构成一首诗,而每个诗段可以在主题或情调上不同,一段宗教,一段回忆,一段爱情,一段历史,一段童话,一段超验。这样的构造,有灵动之美。
在现代小说的艺术层面上,短篇循环体小说如何由碎片合成整体,各家都有路数,《豹变》也有。说得仔细一些,以下几点可供参详。
一,短篇循环体小说的首篇,通常是引子或序。有些作家的引子,明晰点出全书主题。如安德森的《俄亥俄州的温斯堡镇》的首篇,阐释了“怪异”这个贯穿全书的文学概念的哲学意义。还有些引子,没有这般直白,以氛围托出情感基调,暗指主题,如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的首篇。《豹变》的首篇SOS是散文诗,像音乐叙事曲般拓展,在生死至关的一刻戛然而止,隐隐之间似有宣示:人类会遭遇不可预知的灾难,但在符合文明的人性中,博爱(爱他人、爱生命)和生命意志力不会泯灭。我认为,这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终主题。《豹变》结束篇的《温莎墓园日记》与此主题呼应,只不过主题经发展之后,落在“他人原则”(下面详述),以爱(爱他人)来抵制无情无义的现代商业文化。
二,《豹变》的时间排列线索,隐含一个艺术家的精神成长史。书名“豹变”,源自《易经》革卦: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大人即坐拥权位者,变化如虎。小人,脸上变化甚多。大人、小人的变,我们见得多了。惟君子之变,漫长而艰辛,可比豹变。幼豹并不好看,经过很长时间,成年之豹才身材颀长,获得一身色彩美丽的皮毛。木心向我解释书名时说:“豹子一身的皮毛很美,他知道得来不易,爱护得很,雨天,烈日,他就是躲着不肯出来。”“君子豹变”是由丑变美、由弱到强的过程。木心心中的君子是艺术家;其成熟和高贵,也要经过不易的蜕变。此外,“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文”同“纹”,恰是《豹变》斑斓的色泽。
《豹变》的故事描写的是个体的人,大致看得出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几个人生阶段。私人经历又对应着战前、二战、二战后、建国后、打开国门等阶段,需要在这些历史背景中思考。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阶段:走出国门后的西方世界。
三,“我”和他人(他者)。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有两类故事,尼克故事和非尼克的故事,这两类虽然不直接相关,却相互诠释,形成断而不裂的长篇。木心的《豹变》全都是第一人称的“我”为叙述者,但这个“我”有时在几个故事中可能是一个人,有时则不是,有时是被有意模糊了。这里牵涉两个文学原则需要说明:一,第一人称的“我”虽然带有作者经历的痕迹,故事却是虚构的,木心始终坚持:虚构的才是文学;二,有意“模糊”(ambiguity)在文学中是修辞手段之一。
有些故事可以理解为由同一个“我”链接,如第二至第五篇。有些故事(如《魏玛早春》)的“我”,不能认定和前面故事的叙述者是同一人。有些故事里则明显不是,如:《静静下午茶》中的“我”是英国女性;SOS的医生国籍不详;《温莎墓园日记》的“我”虽是男性,但种族、年龄等不详,有意被模糊。
人物身份的有意模糊,由木心的“他人”美学原则解读更为妥当。他人,也可以说是他者。英文里的the other可表示别的人,也可以表示另一个时空、另一个文化、另一种经验。他者原则开辟了木心文学的种种可能,是他的“魔术”法则。
木心本人有爱有恨,但他的“他人原则”以人性中爱的能力为主,意味着“我”融入更广泛的人性经历的可能。木心在《知与爱》中说:“我愿他人活在我身上/我愿自己活在他人身上/这是‘知’//我曾经活在他人身上/他人曾经活在我身上/这是‘爱’/雷奥纳多说/知得愈多,爱得愈多/爱得愈多,知得愈多//知与爱永成正比”。
《豹变》中的时空、经历、文明、艺术,相互交错,我中有他,他中有我。如果读者认定某个“我”一直跟踪,在某一刻就发现那个人虚幻了,“我”的界限模糊了。这一恍惚,阅读进入了“他人原则”的深化。多数情况下的“我”具有艺术家的属性。“豹变”的意思,也是将“我”散开,“我”和他人融为一体,他人也集中于“我”。结束篇《温莎墓园日记》凸显这样的情节:一个生丁(一分钱美币)在“我”和“他”之间正面、反面地翻转,比喻着我和他之间的互动,乃至相互轮回,印证生丁上的一行拉丁文:E pluribus unum(许多个汇为一个)。更形象的印证,则是墓碑上的瓷雕:“耶稣走向各各他,再重复重复也看不厌。”
木心的诗集《伪所罗门书》也是根据这样的“他人原则”将“碎片”连结为整体。副标题“一个不期然而然的精神成长史”,可以相参。
四,飞散艺术家的主题,是各短篇凝聚为整体的另一方式。这十六篇中,九篇发生在中国,七篇在中国之外的时空里。(新方向出版社排斥了三篇,只留了四篇国外的故事。这样一来,九篇和四篇的搭配,结构就失衡了)交叉的时空,是艺术家的成长舞台:民族历史的磨难是源,艺术家依靠生命意志成就艺术是流,源和流一起汇入世界。中国和世界、家园和旅行,是渐悟之后的顿悟。顿悟中,多了一些美学原则的宣示。
当然,把《豹变》的故事分成两个时空有些牵强,因为讲故事的人在心理上是不能分的。《豹变》一开始,那个“我”已是见过世面体验过生命的眼光。
我最早读到木心文学作品是1986年,感叹的是他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写法如此不同。我是世界文学的学生,自己在阅读世界名著体会到的那些美学原则,在木心的文字里一一验证,屡屡有感触。和木心一生为友,我们有这样的共识:汉语文学只有融入世界文学才能现代化,才能生生不息。
题记
代序/童明
说明/童明
SOS
童年随之而去
夏明珠
空房
芳芳NO.4
地下室手记(附:伊丽莎白·贝勒笔记摘录)
(手记之一)名优之死
(手记之二)路人
(手记之三)小流苏
(手记之四)谁能无所畏惧
(手记之五)幸福
西邻子
一车十八人
同车人的啜泣
静静下午茶
魏玛早春
圆光
路工
(之一)良俪
(之二)口哨
(之三)哗笑
(之四)雪礼
(之五)邻妪
(之六)险象
(之七)仙子
(之八)路工
林肯中心的鼓声
明天不散步了
温莎墓园日记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