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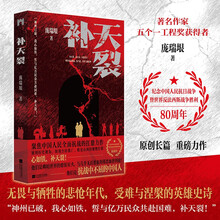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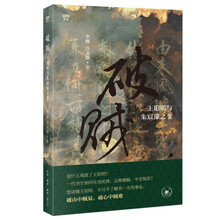

本书是西班牙国民作家、被誉为“西班牙的肯·福莱特”的伊德方索·法孔内斯继《海上大教堂》后又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巨作,讲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王国,一个年轻的摩尔人,卷入到一场宗教和权力的火热斗争中,在两种文化、两份爱情之间徘徊……善良与邪恶、信任与背叛、爱情与仇恨、信仰与抗争,在这里一一上演。
16世纪下半叶,此时距离天主教国王和王后占领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王国——格拉纳达王国已过去半个世纪,曾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八百多年的摩尔人被课以高额赋税,生活困顿不已,甚至不得不改变习俗和信仰。那些被迫改宗的摩尔人又称为摩里斯科人。
1586年底,阿尔普哈拉斯山区的摩里斯科人揭竿而起。年轻的埃尔南多被卷入这股洪流。他是私生子,是摩尔人母亲遭天主教神父玷污后所生,这一出身让他既受到摩尔人继父和族人的排挤,也不被天主教徒所接纳。一开始,埃尔南多负责押送物资,随起义队伍而走,在其他脚夫、起义士兵与领导层、海盗与土匪之间周旋,几次遇险,而在此期间与摩里斯科女孩法蒂玛的相遇、相爱,让他渴望过上安定、平和的生活。
起义失败后,埃尔南多、法蒂玛与其他摩里斯科人一起被驱逐至科尔多瓦。在这里,目睹摩里斯科人再次置于天主教治下的遭遇,埃尔南多开始投入另一场斗争:消融两种文化之间的分歧……
本书是西班牙历史小说家伊德方索·法孔内斯继《海上大教堂》后又一部跌宕起伏、令人窒息的史诗巨作,用翔实的历史细节、令人难忘的人物将摩尔人与天主教徒的冲突描绘得栩栩如生,再现了当年西班牙南部的民族纠纷与世俗风情。
格拉纳达王国,阿尔普哈拉斯,胡维莱斯镇
1568年12月12日,星期日
早晨十点,召集弥撒的钟声敲碎了冰封着小镇的阴冷。这个小镇坐落于内华达山系中一座山峰的峰顶。金属质感的钟声顺着山势而下,撞击着孔特拉维耶萨山脉的裙裾。孔特拉维耶萨山脉从南边包裹着肥沃的山谷,山顶的融雪顺流而下,丰沛的雪水滋养着穿越山谷的三条河流:瓜达尔菲欧河、阿德拉河和安达拉克斯河。阿尔普哈拉斯的土地跨越了孔特拉维耶萨山脉,一直绵延到地中海。冬日微薄的阳光下,近两百名男女老少拖着步子,静默地迈向教堂,会集在它的门前。
教堂用赭石色石块建造,不带任何外饰,呈简单的长方形。教堂的一侧倚着粗壮的钟塔。挨着教堂开辟了一方广场,广场建在溪流之上,溪流错综通向山谷之中。从广场向山脉望去,能看见许多狭窄的小路,小路两边镶着一座座低矮的平房。房子的墙是用石灰抹的,一两层高,门窗很小,平坦的屋顶上竖着圆柱形的烟囱,烟囱带着罩子,远远望去像朵朵蘑菇。屋顶上摊晒着辣椒、无花果和葡萄。小路顺着山坡向上迂回,下层房屋的屋顶和上层房屋的地基一般高,就仿佛是一幢叠一幢搭起来的一样。
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几个孩子和几个旧天主教徒——镇上约莫有二十来个旧天主教徒吧——正凝视着一位老妇。老妇被推上了教堂前高耸的楼梯;她战战兢兢地用手扶着栏杆,嘴里仅剩的几颗牙咯咯作响。受过洗礼的摩里斯科人纷纷进了教堂,甚至没有瞥一眼他们这位教友姊妹。一清早她就被推到这里,绑在最高的那根横梁上,没有外衣的她独自承受着严冬的寒风。钟声不停地响着,随着钟舌敲击而不停战栗着的老妇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个男孩伸出手来指向她,一阵笑声打破了现场的寂静。
“老巫婆!”欢笑中传出一声喊叫。
几个人拿起石块掷在了老妇身上;一时间,楼梯下唾满了痰迹。
钟声停了,还在外头的天主教徒们赶忙涌进了教堂。教堂里,距祭坛几步远的地方,一位皮肤被日头晒得黝黑的高大男子正对着信徒们跪在那里;他一头黑发,没戴披肩也没穿外套,颈上绑着一根麻绳,双臂交叉成十字,两手各握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几天前,这个男人曾把一件衬衣交给刚才楼梯上的那位老妪。衬衣是他妻子的,他妻子患了顽疾。他把衬衣交给那位老人,是为了让她把它带到传说中有治病神力的一汪清泉中洗一洗。那泉水隐藏在崎岖陡峭的石崖中,人们几乎从来不在那里洗衣服。赶巧不巧,老妇去洗衣的那一天,恰好被镇上的神父堂·马丁给撞上了;见她不远千里只为洗那一件衬衣,堂·马丁神父断定这事必与巫术有关,处罚便如期而至:周日的整个上午,那位老妇都得被绑在高悬的楼梯上,接受民众的嘲笑和奚落,而求她施展巫术的那位天真的摩里斯科人则不得不跪在祭坛前,让所有前来祷告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他一边忏悔一边接受训诫的样子。
进了教堂,男人们就得与他们的妻子分开,妻子们带着女儿站在最前面的几排。那个摩里斯科人就跪在女人们的脚前,眼神涣散。所有的女人都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耕着自己的地,养着自己的几头奶牛。他只是想要帮帮他那生病的妻子呵!慢慢地,男人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位子,有序地排在女人们的后面。待所有人都站定之后,神父堂·马丁、受俸教士堂·萨尔瓦多以及教堂司事安德列斯一齐走向了祭坛。堂·马丁身材丰硕、面色白皙、脸颊红润、身着一袭绣金神袍。他走到那些虔诚的教徒面前,在尊座上坐了下来,教士和司事分立在他的两侧。有人关上了教堂的大门;没有风,烛火也不再闪摆。教堂顶上五彩的伊斯兰装饰光辉闪耀,与祭坛及侧墙上天主教受难画的节制与凄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司事是一个高挑的年轻人;他身着黑服,身材瘦削,脸庞是和大多数信徒一样的棕黑色。他打开一本册子,清了清嗓子。
“弗朗西斯科·阿尔瓜西尔。”司事念道。
“到。”
证实了声音的来源之后,司事在册子上做了记录。
“何塞·阿尔梅尔。”
“到。”
司事继续记录。“米拉格洛斯·加西亚、玛丽亚·安布罗斯……”每叫到一个名字,都有相应的人以“到”回应,随着安德列斯的名单越念越往后,回答的声音也越来越像一声嘟哝。司事只管对照着每个人的面孔,做好自己的记录。
“马尔科斯·努涅斯。”
“到。”
“你上周日没来做弥撒吧。”司事诘问道。
“我那天是在……”那个男人试图辩解,但又想不出合适的西班牙语用词。他仓促地用阿拉伯语完成了后半句,同时挥起一份文件。“你过来。”安德列斯命他上前。于是马尔科斯·努涅斯挤过人群,来到祭坛下面。“我那天到乌希哈尔去了。”这会儿他算是完成了那句解释,同时把那份文件交给司事。
安德列斯瞄了一眼那张纸,便把它交给神父;只见神父拿起那文书细细端详,验证过签名以后,做了个同意的表情:乌希哈尔教堂神甫证明,胡维莱斯镇居民、新天主教徒马尔科斯·努涅斯于1568年12月5日在本市参加了教堂弥撒。
司事的脸上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他在册子上写了两笔,又接着念那份无尽冗长的新天主教徒名单——所谓新天主教徒,就是那些被西班牙国王强迫进行洗礼从而皈依天主教的穆斯林——作为新天主教徒,必须证明自己每个周日和训诫日都参加了相应的宗教仪式。念到名字没有答“到”的人员都被仔仔细细地记录了下来。有两个妇人无法说明自己为什么没有参加上周日的弥撒;她们不像马尔科斯·努涅斯那样带有乌希哈尔教堂颁发的证明,只是慌乱地辩解着。安德列斯任由她们解释,眼神却偷偷瞄向了神父。堂·马丁用专横的手势示意她们闭嘴,其中一个妇人立刻安静了下来,而另一个却还在奋力申辩,称上个周日自己是病了。
“你们可以去问我老公!”她一边嚷着,一边焦急而紧张地在最后几排人里寻找她的丈夫,“他会跟你们……”“安静,你这个魔鬼的追随者!”神父堂·马丁一声怒吼把那个摩里斯科人妇女吓得哑口无言,她低下了头,同时那位司事也记下了她的名字:这两个女人都要支付半个里亚尔作为惩罚。漫长的点名之后,神父开始了弥撒。在此之前,他又命司事让那个摩里斯科忏悔者把手里握着的蜡烛举高了些。“以圣父、圣子以及圣灵的名义……”仪式继续着,尽管真正能够理解这些神圣话语、或是真正能够跟上这种语速的人实在很少,甚至整个布道过程中夹杂着的神父的那些训斥都很少有人能够明白。
“难道你们认为一口破泉里的水就能帮你们祛病消灾吗?”神父用颤抖的食指怒指着那个跪着的人,脸皱成一团,“这就是你们的榜样。正因为你们如此堕落腐化、亵渎神明,基督才要惩罚你们,让你们的生活充满苦难;也只有基督才能拯救你们脱离苦海!”
下面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懂西班牙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用阿尔哈米亚语跟西班牙人沟通:那是一种混合了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的方言。但是不管怎样,所有的人都必须会用西班牙语背诵天主经、万福玛利亚、信经、圣母颂和戒律。那些受过洗礼的摩里斯科孩子有教堂司事给他们上课讲授,而一般的男男女女,每周五和周六都有相应的课程,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否则就得接受罚款或是被禁止结婚;只有当他们能一字不差地背下那些祷告的时候,才能被准许不再参加此类课程。
弥撒还在进行,有些人祈祷了起来。孩子们在很认真地听司事讲课;他们读得很大声,几乎像叫喊一样——这是他们父母教的,因为只有这样,大人们才能趁教士来回走动监督的当儿偷偷地呼求真主安拉。很多人都闭着眼,如此默默而语,不住悲呼着。
第一部 以安拉之名 1
第二部 以爱之名 201
第三部 以信仰之名 427
第四部 以我主之名 579
终章 717
作者后记 727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这本书有力地唤醒了那段历史、那个时空。
——《出版人周刊》
一本令人兴奋、可读性强的冒险小说,情节生动,描述栩栩如生。
——英国《独立报》
谨以这本书献给这世上所有曾经经历过以及依然还在遭受着苦难的孩子们——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问题,我们还无力解决。
——伊德方索·法孔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