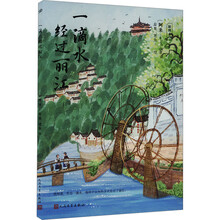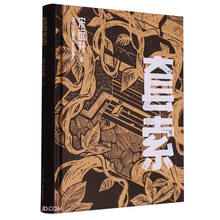如水的月光温柔地行走在西京的大街上。
忽然,太阳就像孩子可爱的笑脸,兴高采烈地挂在天边。这时,街道上便有身着各色服装的俊男靓女成群结队匆匆地从人群中风样般划过。节令已经完全进入了盛夏,那些亭亭玉立的妙龄美女们,手里撑着色彩鲜艳的太阳伞,鼻梁上架着款式时尚的太阳镜,高昂着自信的头颅,脸上绽放着甜美的微笑,迈开那修长的双腿,踏着轻盈而欢快的脚步,潇洒干练、气度非凡地行走在这个城市繁华热闹的大街,霎时街道上便形成了一道迷人而亮丽的风景。
一环套着一环,环环相套起来的一座城里,布满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蛛网般交错的一条条大街、一道道胡同,楼与楼之间的街道上那犹如潮水一般涌动的车流和人流。那些操着不同口音肤色各异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就在这样拥挤不堪的环境和骚动不安的心境中苟延残喘地生活着。同时,为了生活而不断地穿梭着、忙碌着、苦苦地挣扎着。
然而,居住在环环相扣、层层环绕的大城市里的人们多么想走出去,站在视野开阔的塬上,伸着疲惫的懒腰,舒展地长长出上几口气,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享受啊!而城外的人又钻头觅缝地想冲进来,以为大城市就像他们梦想中的人间天堂一样,这不正是钱钟书大师小说《围城》里所描述的情景吗?那么麻六在这样的城市里到底得到了什么而又失去了什么呢?
麻六曾无数次痛苦不堪地思索这一切。
这一切对于常常徘徊在城市边缘地带的麻六来说,是多么不堪回首又痛不堪言,他仿佛就像做着一场惊魂不定的噩梦一样……
这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样黑漆漆的夜里,听不到任何的声响,就连常常在夜深人静里爱吵叫的猫头鹰,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给这个平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静默和恐惧。此时,在西京闯荡了十几个年头的麻谷岔村民麻六,一脸愁容地回到生他养他的麻谷岔,呆呆地站在村头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两只眼睛死鱼般地望着远处起伏连绵的黄土山,时不时吮一吮快要流到嘴里的鼻涕,嘴里还不停地呢喃着这样一句话:我现在怎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麻六说不上来自己此时此刻心里到底有多么痛苦多么难受。回想那时候,他是多么风光地一路欢歌离开麻谷岔,走进了举世瞩目的大城市,在一个让村里多少人向往的大型建筑工程公司当上了工人。十几个年头的热热闹闹、风风火火就这样行云流水般地过去了,在他生命如日中天的时候,由于单位进行体制改革,他无可奈何地告别了机器轰鸣而又红火热闹的建筑工程公司,灰头土脸地回家了。
刚没工作那会儿,麻六的口袋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敲狗脑的碎钱,可是现在连那点碎钱也所剩无几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毫无选择地面对现实,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一条路。
麻六苦苦地寻找过,但都被拒之门外。无处可去的麻六,只好眼含泪水地返回他的老家麻谷岔。
快回到家的时候,麻六害怕村子里的人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便在村子外的一条荒野山沟里磨蹭了老半天时间,等天完全黑下来,路上再碰不到什么人了,他才沮丧地朝麻谷岔村子里走去。
麻六漫不经心地走到村头,站在他小时候常常玩耍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回想和感受着生活给他带来的无比艰辛和巨大灾难,深深体会到人是如此渺小又是这么不可思议,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还是回来了……”
麻六站在村头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不知怎地泪流满面。
此时此刻,麻六挎着他那破旧的黄色帆布挎包,像小偷一样从村头拐峁的地方绕过去,悄悄地从他家那道坡里爬上来,跌跤马趴地从他家门里溜进去,还没等他在脚地上站稳,猛然听见多年没叫的猫头鹰站在他家对面山峁的土圪尖上,发出几声惨唳的叫。
嘿呼!一声。
嘿呼!又是一声。
这时候,父亲正仰躺在他家窑洞里下炕的铺盖卷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一双皱巴巴的眼睛微微闭着。
母亲盘腿坐在他家那盘光板土炕上,她的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胸前,一副低眉瞌睡的模样。
老两口看见儿子突然从门里走进来,感到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这么晚怎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是不是这小子在外边出了什么事?喜的是儿子终究没忘记老两口,老远跑回来看他们来了。仔细算一算,儿子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甚至给他们写回来的信也越来越少。如果儿子不这样还好,他越是这样没心没肺,老两口心里越是不踏实地对他牵肠挂肚。
父亲看见儿子从老远的西京市回来了,忙探着身子在炕棱石上把手里那支劣质的带把把烟一灭,赶紧溜下炕棱,手忙脚乱地从儿子肩胛上接下了那个破烂的黄色帆布挎包,嘴张了几张,好像想问儿子几句什么话,但他又激动得什么话都没能说出来。
母亲这时候也从炕棱上溜到了脚地,颤微微地走到儿子跟前,不停地在儿子浑身上下拍打着,并喊叫着让麻六的父亲赶快到院子里去搂柴,她那心爱的儿子肯定现在还没有吃饭。
麻六痴呆呆地站在脚地上,眼含泪水,他从进得家门到现在,几乎什么话也没给父母说一声,就像从西京市里回来突然变成了一个哑巴。
麻六看着父亲从门里出去搂柴,母亲忙着走到灶台跟前,拿起马勺就往锅里舀水。他却灰着一副脸,倚在炕棱石上,眼睛看着窑顶上吊着的那个微微泛黄的电灯泡,不紧不慢地对母亲说:“妈,你别做饭了,我不饿。”
父亲费劲马趴地搂着一捆柴走到灶台跟前,听见麻六说这话,木愣愣地站着。
母亲看着倚在炕棱石上面无表情的儿子,再扭头看看搂着柴愣在灶台跟前的她男人,不明白儿子今天回来到底是怎么了?
夜是很静的,仿佛能听到两位老人此时此刻站在灶台旁心跳的咚咚声响。
老两口都僵硬地站在灶台跟前,愣愣地看着倚在炕棱石上的麻六,不知道在这时候究竟该给他儿子说句什么话。
“小六子呀,妈问你,你是不是跟你媳妇闹架了?”母亲趔趄着走到麻六跟前,身子不由地抖动了几下。
“没有……”麻六心不在焉地对他母亲说。
“那是人家单位上批评你了?”父亲放下搂抱着的柴禾,站在后脚地里问麻六。
“没有。”麻六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
“那你到底是怎么了?”老两口几乎同声问麻六。
唉!麻六呀你个麻六,你可从来不是这样,也从来没有像今晚上回来这么垂头丧气过。以前你每次从那个西京市里回来,人还没进得门,声音就先传进来了,不是亲热地问妈长妈短,就是关心地问爸的身体怎样,还给我们已经快要入土的人带回来不少好衣裳好吃喝,都是大城市里正时兴的那些稀罕东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