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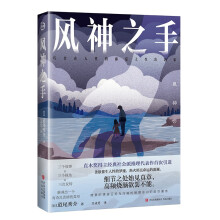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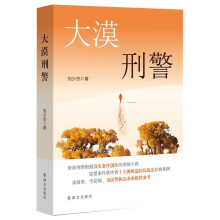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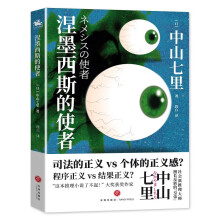
安东尼·拉克,备受头痛困扰的独行杀手,他在笔记本上列出了一串名字:特里·多特里、萨顿·贝尔、亨利·高摩伦。在他眼里,这些人的名字正从纸上发出红光,会浮动,会呼吸。他们毫无相似之处,除了一点:七年前,他们参与了一起犯罪活动——抢劫大湖银行。现在,拉克要追杀他们,他们三个不死,他决不罢休……
大卫·卢根,推理杂志《灰街》的编辑兼作家,他和警探伊丽莎白及她的女儿生活在一起,过着按时按点的平静生活——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匿名投稿信。在押罪犯、印第安男孩、小报记者露西、多位当地权势人物,与这些人有关的一个个奇异案件骤然闯入他的生活……
“来吧,”他说,“把鞋脱了,感受一下趾间的沙粒。走到水边去,好好看看四周,仔细地看。即便在月光下,你也能看见岸边水下的鹅卵石那清晰的轮廓。把脚伸进去,好好感受下水有多凉,肯定会冷得让你抽气。因为太冷了,一开始你甚至会有刺痛感。但这种感觉会提醒你,你还活着。”
我办公桌台灯的灯臂上挂着一串玻璃珠项链,但凡桌子有一点点震动,它都会晃个不停。深蓝色的玻璃珠,仿若傍晚时分的天空。灯光下,它散着荧荧的冷光,熠熠生辉的样子很是灵动,像被赋予了生命一样。
让我将这串项链的来历向你娓娓道来。我第一次和伊丽莎白接吻时,她就戴着这串项链。那是一个冬夜,在我的办公室里,就是安娜堡市缅因街这幢大楼的六楼。伊丽莎白是一名警探,那天晚上,她去一个车祸现场出警。现场满是断裂的金属、碎裂的玻璃,还有其他支离破碎的东西。现场有三人死亡,其中一个是孩子。那是一场你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看到的事故,一场你希望自己可以遗忘的事故。
但她看到了。她想逃离那里,尽自己所能,离那里越远越好。然后,她逃到了我这里。当时已是深夜,我在办公室里加班。我听到有人打开了走廊的门,然后听到了她的脚步声。她穿过外面那间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的门口停了下来。她个子高挑,身上的长大衣将她的身形衬得十分修长。几片雪花落在大衣的肩膀处,消融之后水印晕染开来。我看到敞着的大衣里是一件衬衫,第一颗扣子没有扣。她僵直地站在那里,右手五指焦躁地拨弄着脖子上的玻璃珠项链。
她的脸被乌亮的头发圈着,面色苍白。我非常了解她,知道她一定是遇上了不好的事。我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朝她走了过去。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无神的样子让我不由得凛了心神,不敢随意碰她。我慢慢抬手,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然后又收了回来。
办公室的窗外,雪花一片一片,从天空懒洋洋地向下飘落。我们一起站了一会儿,我一句话都没问,静静地等着她告诉我。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她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一句句话像连珠炮一样不停地从她嘴里蹦出来。每说到一个可怕的细节,她的手指就会拨弄一下项链上的玻璃珠。
说完之后,她别开脸。因为羞怯,或者可能是尴尬。我想应该是尴尬。我后退了一步,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便走到办公桌前,把抽屉里那瓶苏格兰威士忌拿了出来,给她斟上一杯。
但她需要的不是酒。
我的目光追随着她。她脱下大衣,轻轻搭在一张椅子的椅背上,慢慢向我走来。她离我越来越近,最后,我们四目相对。吻我的时候,她睁着双眼,眼眸幽蓝深邃,就像那串项链上的玻璃珠。第一个吻轻缓缠绵,不疾不徐。我们都知道它只是一种对抗之举。这是人类的本能。我们见证了死亡,但我们却想对抗死亡,我们想要证明自己是活着的。
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却没来得及深思。第二个吻比之前热烈而急切。我感觉到她的手从我的肩膀移到了后颈处,她的手指插进了我的发间。她贴着我,想要把自己嵌入我的身体里,我们紧紧地拥抱,我能感受到她的体温,她的活力,还有身体里澎湃的激情。
这段记忆我并不愿意全部说出来,我想能说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余下的,是我和她的专属回忆,禁止其他人窥探。那晚,它被伊丽莎白落在了这里。这就是我办公室里那条项链的来历。
我之所以告诉你它的来历,是因为它和动机有关。
如果你把这条项链放在一个珠宝商面前,他会说它一文不值。项链的串珠都是玻璃做的,用一根普通的线串在一起。我知道,这是事实,无须置疑。
但同样我也知道,如果一个小偷想把这串项链从我这里偷走,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制止他。如果杀死他是唯一的方法,我一定会这样做,毫不犹豫。
我说这么多,重点并不在于项链,而在于人们杀死他人的动机。关于动机,我有所了解。我叫大卫·卢根,是一名编辑,人们会向我诉说许许多多杀人的故事。我收到的大部分稿子都很糟糕,但也会有一些有潜力有前景的。我会从中挑出最好的稿子,做一番润色,然后放到一本叫《灰街》的推理杂志上出版。
也许,我说我的故事源于一份文稿,也丝毫不会让人意外。
事情非常简单明了。七月中旬一个周三的晚上,我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发现了它。这很稀松平常。当地的写手时常会把文稿放在那里,数量多得超乎你的想象。
然而,这一份稿子却是不同的。它被装在一个空白的牛皮纸信封里,只有不到十页。这份稿子描写了三起谋杀案,其中两起已经付诸行动,还有一起没有实施,这些都不是杜撰之事。稿子的开头和结尾都没有留下名字。写下这个故事的男人并不想暴露自己。他把故事录进电脑里,然后在外面的复印店里打印出来。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后来伊丽莎白发现的。
我把这份稿子交给伊丽莎白时,还抱着一线希望,想从中发现一些有用的证据。犯罪实验室可以通过检验毛发、纤维和DNA 来创造奇迹。我本以为纸页上除了我的指纹之外,还会留有其他人的指纹。但伊丽莎白把稿子交到实验室之后,线索就断了。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没有任何让她找到作者,或者是揭示作者动机的提示。
如果你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回到过去。回到七月中旬,我收到稿子的那一天之前。我们不得不摒弃常规,因为这是一个不循常规的故事,它根据自己的思路发展。尽管这故事和我有关,也和伊丽莎白有关,但却并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它从密歇根北部一个叫苏圣玛丽的城市开始。它从一个旅馆房间里开始。
故事开始于一本笔记本。
……
海明威是一个很好的分界点,海明威的句子呈现出一种很漂亮的深蓝色,而且大多数都是静止不动的,就像在一个无风的日子里静静垂着的麦穗。库尔特·冯内古特的散文是让人舒适的蓝绿色,他的文字温雅而流畅,就像一部缓速爬升的自动扶梯一样。
……
“来吧,”他说,“把鞋脱了,感受一下趾间的沙粒。走到水边去,好好看看四周,仔细地看。即便在月光下,你也能看见岸边水下的鹅卵石那清晰的轮廓。把脚伸进去,好好感受下水有多凉,肯定会冷得让你抽气。因为太冷了,一开始你甚至会有刺痛感。但这种感觉会提醒你,你还活着。”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