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诗学/李洱作品系列》:
费边对朋友们说,看啊,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台,在我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生活中最荒诞的戏剧。费边的朋友韩明说,自己以前就常来这里看戏,有时看得津津有味,恨不得在这里住下不走。
我们在那里谈亚里士多德,谈米沃什,谈布罗茨基,谈学生们送给阿多诺教授的两样礼品:粪便和玫瑰。布罗茨基的那两句话(我是二流时代的二流诗人,二流时代的叛臣逆子)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费边有一次提到了罗马的罗慕洛斯大帝的逸事,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这位有趣的皇帝,在代表着新文明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不事抵抗,只在那里逗弄小鸡。“他是一个对罪恶心中有数并能作出艰难选择的人,”费边说,“在缴械的时候,他盯着那些刚爬出蛋壳的小鸡,心中充满喜悦、寂寞和自由。”费边总能找到这种逸出历史编年史的“本质性”事件,使大家在严肃的讨论中,放松一下神经。有一次,韩明和一个写《论语新注》的人吵了起来。那个人事先强烈要求将自己的新注带来,供大家讨论,可临到出门的时候,却要求派车去接他,韩明是聚会召集人之一,他只好坐出租车去把他接了过来。韩明发现他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烧得厉害,头昏脑涨”,在讨论中就专和他抬杠。如果不是因为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这两个胖子就要像相扑选手那样扭到一起了。费边并不上去拉架,他有办法制止他们。他向别的人提起了一个梦,世上最有名的脱星麦当娜做的一个春梦。在梦中,麦当娜和罗慕洛斯大帝的现代传人戈尔巴乔夫做爱,在高潮上下不来。“赖莎在旁边吗?”有人问。费边说:“你们可以去问韩明,他知道得比我清楚。”韩明说,他是从录像带上看的。他说,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下次再看的时候,一定会格外留意。韩明顾不上和那个人吵了。他现在忙着给朋友们解释他看到的精彩镜头,并提议大家来讨论讨论那个有趣的梦。话题至此转换了。“世俗欲望”、“大众传媒”与“集体迷幻”、“性的深层本质”,这些词语立即从舌面上跳了出来,蹦上了桌面。就像一群猫见到了被夹住的一只老鼠,每个人的声音,都那么有力、那么欢快。刚才的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最后那两次聚会,这些精英们讨论的是怎样将思想转化为行动。他们决定先办一份杂志。既然已经到了秋天,到了收获的季节。那就有必要把每个人的思想都收割一下,存到谷仓(杂志)里面。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炒作”的词,像瘟疫一样在社会上流行开了,大家都说,这事要好好操作一下,首先得起一个能叫得响的刊名,然后制定一个有弹性的编辑方针。为了更好更快地把杂志搞出来,有人建议可以请一些有实际操作经验的编辑来一起讨论。这个请人的任务就落到了交际多、门路广的韩明头上。“你可别又领来一堆女人,”一个研究西马的人对韩明说,“这是正事,不能瞎闹。”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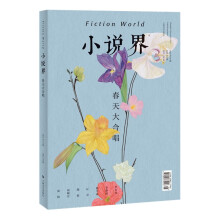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李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