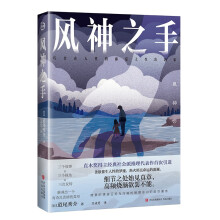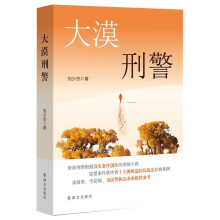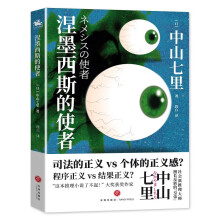一切都在我吻阿宽的那个瞬间注定,不可搀回!
事情是这样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暂时收敛了对我们的地下清剿行动。但是王木天不甘心,或者说他找到了更下作无耻的伎俩。其实,那时周佛海确实在对重庆暗送秋波,王木天就勾结他,利用他的力量对我们施行公开清剿。好在我利用革老父女对我的信任和重用,给他们下烂药,制造了一些假情报,使他们对我们地下组织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多不深,否则我们真的会受到重创。毕竟这是在南京,周佛海手上有军队,有警察,随时随地可以抓人杀人。但阿宽的目标太大了,王木天早知道他在南京,朝思暮想想把他挖出来,讨好戴笠。周佛海知情后也是如获至宝,替重庆抓到赫赫有名的老A,等于是他在重庆政权里存了一笔“善款”,何乐不为?就这样,一时间里,南京城里满大街都是阿宽的头像,大肆通缉搜捕。
风声太紧张,形势太严峻,阿宽只好先出去避一避风头。他去了江北,在新四军的地盘上去做了一回客人。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我日夜思念他回来,却又怕他回来。其间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他后来提前回来的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后,先发来电报要我把孩子处理掉。我当然不是太情愿,谁会情愿呢?他可能是怕我处理了孩子太伤心,也可能是担心我“有令不从”,所以提前回来了。
回来得真不是日子啊!有些事回想起来就觉得是命,命运要袭击我们!
我清楚记得,那天是星期日,头天晚上秦时光约我出来吃饭,我拒绝了。这家伙总缠着我,为了稳住他,我答应这天去幽幽山庄跟他吃午饭。这是郭阿姨离开香春馆后二哥出钱开办的一个饭店,是我们一个新据点。阿宽不在期间,我出门都是自己开车,每次出门前,赵叔叔总是帮我把车擦得亮堂堂的。这天,我出来开车,觉得奇怪,赵叔叔一个劲地冲我发笑。我问他笑什么,他说他刚得到一个好消息,不知该不该告诉我。
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说:“组织上不允许。”
我说:“你这不废话嘛,不允许你就别提起,提起又不说,挠我痒呢。”
他说:“你快上车吧,组织就在车里。”
我打开车门,天哪,竟然阿宽坐在驾驶位上!他几分钟前才回来,看到赵叔叔在擦车子,自然先跟他招呼。他从赵叔叔口中得知我马上要出去见秦时光,便跟我做了这个游戏。我好开心啊,激动得恨不得一口吞下他,可当着赵叔叔的面怎么好意思。赵叔叔建议我们回去喝杯茶再走,阿宽问我跟秦时光约的时间,我说是什么时间。他说:“那不行了,走吧,已经很紧张了。”就走了。
事后我想,我们真不该这么仓促走的,为什么后来到了秦时光楼下我会那么不能自禁地去亲他,就因为……怎么说呢,我已经那么长时间没见他,见了他我心里一下迸出太多的情感要渲泻,要抒发。不是情欲,真的,是情感,一种久别重逢、不亦乐乎、兴奋难抑、炽热如火的情感。如果我们当时进屋去坐一下,喝一杯水,让
我在他胸脯上靠一靠,哪怕只是拉拉手,我后来可能就不会那么不能自禁。还有,该死的秦时光,如果他当时准时在楼下等着,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他那天迟到了,这是他无意中给我挖的一个陷阱,我在诱惑中跳了下去。
其实,我们也没有怎么着,可以肯定绝对没有亲嘴。阿宽还是很理智的,我开始上车就想坐在前面,被他阻止了。“干吗?”他说,“别破规矩。”我说:“让我先坐一会儿,跟你说会儿话,呆会儿我再坐到后面去。”他笑道:“我已经习惯你坐在后面跟我说话了。”我说:“今天不一样,破个例。”他刚回来,情况不明,很谨慎,说:“何必呢,万一门口就有人盯着呢。”说着特意脱了外套,放在副驾驶位上,分明是没有商量余地。
我只好坐在老位置上,车子一驶出赵叔叔的视线,我一边说着话,一边还是冲动地去抚摸他的头。他跟我开玩笑:“现在胡同里没人,摸摸可以,呆会儿上了街可别摸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绝情,这么长时间没见我也不想我。”
他说:“你这人真没良心,我回家连门都没进,就陪你出来还不是因为想你。”
我说:“我每天都在想你。”
他说:“我每夜都在想你。”
我说:“我每一分钟都在想你。”
他说:“我每一秒钟都在想你。”
我们就这样以惯常的方式互相斗嘴、逗开心,一路逗下来,我的情绪真是炽热得要着火,恨不得坐到他身上去。车停在秦时光楼下时,我左右四顾一番,没看见秦时光人影,也没看见其他人,顿时情不自禁地去抓他手。看四周没人,他也让我抓,但身体依然正常坐着,既没有回头也没有侧身,只是把手伸给我,让我握着。如果仅仅握着,我不把他的手抬起来,外面是没人看得见的。可我自己也没想到,握住他的手后,我的情绪变得更炽热,是一种通电的感觉,浑身都麻了。
真的,我太爱眼前这个男人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上司、我的爱人、我的大哥、我的信仰、我肚子里那团血肉的父亲……哦,该死的我,居然在这时候想到我们的孩子!一想到这孩子,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化为泡影,我的情绪就乱了,我捧起他的手,又是亲,又是咬,是一种爱恨交加、不能自拔、几近癫狂的感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