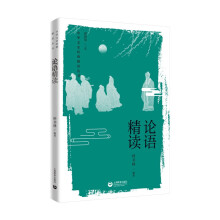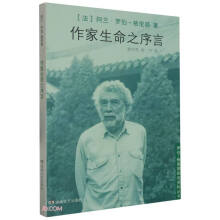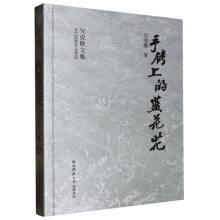卡拉
那是我二十八岁生日的时候,有一对与我同龄的年轻夫妇邀我吃晚餐,并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庆祝。
我从他们家出来,大约凌晨两点多的样子。我略微有些醉意,摇摇晃晃地朝电车站走去。尽管罗马九月的秋夜十分宜人,但街上依旧空旷。车站处,有一个姑娘坐在地上,背倚着支撑时刻牌的栏杆,双臂交叉环抱在膝盖上,头向下埋着。因她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她那金黄色的长发还耷在两旁。我感觉她是睡着了。当电车开来,铿锵声不绝于耳的时候,她也一动不动。
于是,我俯下身,碰了碰她的肩膀。
“醒醒!车来了。”
她缓慢抬起头,大大的蓝眼睛里默默地滚出大滴大滴的眼泪。她不说话,也没有丝毫要站起来的意思。于是,我弯下一只膝盖。
“不舒服吗?”
“不。”
“那你为什么哭?”
“我哭了?”她有些傻傻地问。
女孩用手在脸上擦了擦。她看了看双手,然后在牛仔裤上蹭了几下。
“是的,”她说,“我刚才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这时,电车开来,停下,又开走了。我没能上去。
由于我没赶上车,只好朝最近的出租车停靠点走去。我想我恐怕得再等一个小时。可没一会儿,就有人喊我:
“别走。”
她问我能否给她一支烟。她的问话没有语调的变化。我坐在她对面的人行道边沿。她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开始说话,她蜷缩着,像一只刺猬。
“我叫卡拉,你呢?”
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猛地抬起头,这一次,她盯着我看。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的名字和你的一样。我很爱他。他死了。”
她又把头埋了下去。突然,我意识到了事情的荒谬。
“卡拉,”我说,“我有点儿累,我想回家睡觉。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送你一程。”
“我不记得我住哪儿,”她说,“所以我才坐在这里。我在等我自己回忆起来。”
“那你没有钱包、证件,或者别的东西吗?”
“我什么也没有。我的东西都丢了。可能是有人把它们都偷走了,我不知道。”
她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从她说话的语调来看,我觉得她说的是实话。
“如果你不记得你住在哪里,那你怎么办?你去宾馆吗?”
“我一分钱都没有。”
“那你打算在哪儿过夜?”
“不知道。”
我很快做了个决定。我提议她去我家,我告诉她,和我同住的朋友正好不在,第二天早晨晚些才会回来,所以她可以睡在他的房间里。
“好的。可是我不希望你有什么想法……总之,我不……”
“我懂,”我说,“你不用担心。”
她站起身,我们朝停车场走去。
她比我高,模特身材。应该和我一样的年纪。有时,她会放慢脚步,停下来,皱起眉头,向四周看看,慌慌张张、手足无措的样子,然后又开始走起来。
我们窜到一条车辆还算多的街上,街对面就是停车点。我们的右边,正有一辆车飞快地开过来。我们停在人行道上,让它先过去。突然,卡拉让我震惊,她开始大声地数数:
“一,二,三!”
数到三的时候,她冲向街道中央,朝汽车扑过去。我闭上眼睛,吓蒙了!我听到的,不是意料中可怕的撞击声和刹车声,而是轮胎刺耳的爆破声。我赶紧睁开眼,看见司机成功地避开她,从她身旁擦身而过,往前开去了。卡拉还停在路中央,一动不动。有几辆车又要开过来了。我追上她,为了让她往道路的分界线处躲躲,我抓着她的肩膀,几乎是拖着她在走。
“你疯了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就是突然想那么做。”
我不禁被她的话吓得身子一抖,她却一脸平静。出租车上,她望着我,像之前从未见过我。
“你刚告诉我你叫什么来着?”
“安德烈亚。”
“你是第一个我认识的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叫斯特法尼亚。”
可是,她刚才还告诉我……唉,算了吧。
我们刚到家,她跟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要水。”
“你想喝吗?”
“不,浇在我身上。”
“你想洗澡?”
“对,就是这个。我想不起来怎么说了。”
我先给她指了指她的房间,然后告诉她浴室在哪里。一刻钟以后,她出现在我面前,浑身赤裸,满是水滴。她让人无法呼吸。
“我不会关水。”
我去关上了水龙头。她没擦干身体,也没跟我打招呼,就径直去睡了。她把衣服留在浴室。我仔细翻了翻她衣物,牛仔裤是最好的牌子,所有兜儿都是空的,仅有的东西是一条手绢。那晚我睡得很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十点。我想起了卡拉,或者应该是叫斯特法尼亚?我起床,去了她的房间。只看见一张乱七八糟的床。我去浴室,她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我发现,我昨晚挂在浴室门背后的牛仔裤正躺在地上。我捡起裤子,看见底下还落着我的钱包。我清楚地记得,钱包里有仅剩的四千里拉。现在,只剩下三千里拉。
.安杰丽卡
我曾经爱上两个叫安杰丽卡的女人。一个出自鲁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Ariosto)的诗歌,她让我开始有了爱情的感觉,令人振奋,又备感折磨。
六岁的时候,我就能流畅地进行阅读。从那时起,再也停不下来。我最早读的一本小说,是康拉德(Conrad)的《奥迈耶的痴梦》。那时我得到了父亲的许可,可以从他的书橱里随意挑书来读。我的父亲算不上知识分子,不过他对好的文学作品却爱不释手。那时候,我胡乱地读了不少作家的作品,有康拉德(Conrad)、梅尔维尔(Melville)、西默农(Simenon)、切斯特顿(Chesterton)、莫泊桑(Maupassant),意大利的作家有阿尔弗雷托?番契尼(AlfredoPanzini)、安东尼奥?贝尔特拉梅利(AntonioBeltramelli),以及马斯莫?伯坦佩里(MassimoBontempelli),等等。
我的外祖父母住在我们隔壁的公寓,不过,外祖父维琴佐的书橱丝毫提不起我的兴趣。他那儿满是Hoepli出版社出版的手稿,关于谷物的种植、牲畜的饲养,也有几本儿童教育的书,唯独没有小说。我的外祖父还收集了一系列历史、地理、经济的出版物,涉及意大利的各个区域。大部分书都被束之高阁,只有三十来本零散地躺在书架的底层。
一天,说来也巧,我发现在这些书底下,藏着一本大部头。我把它抽出来。这本书还真是厚,长宽都是普通书籍的两倍。厚重的装帧封面呈红褐色,上面的金字赫然写着“鲁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疯狂的罗兰”。那纸张光滑发亮,每一页都很厚。第一眼看去,古斯塔夫?多雷(GustavoDoré)精美的插画就深深吸引了我。
我把那本书据为己有,反正没人注意到它的消失,我把它带到了我的房间里。
从那时起,有好几年,我都和安杰丽卡在一起。我爱上了她,我为多雷描绘出的她的美貌而痴迷。多雷绘制的图案,让头一回看见女人裸露身躯的我,产生了难以名状的兴奋。或许是因为这些图案,这本书才被半掩着藏了起来吧?
多雷从没画过不披薄纱的安杰丽卡,不过我借给了她一个赤裸的少女身躯。她的手腕高举,搭在一根树枝上,这具体出自书的哪个章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用食指一点点地沿着那身体的轮廓画着,抚摸着,半闭着眼睛,心跳有些加速。我在心中一直重复着安杰丽卡的名字,像念经一样不停地默念着。
我十来岁的小脑瓜,已经接受了四年的优质文学熏陶,我读的可不是什么儿童读物。我还记得,这首诗有两个片段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个是菲亚梅塔(Fiammetta)的故事,她背叛了她的两个爱人,却仍旧和他们在床笫间寻欢作乐;另一个则是安杰丽卡,虽然有不少勇士和贵族富豪追求她,她却钟情于贫穷的牧羊人梅多洛(Medoro),并和他生活在一起。
读到这个故事,我和作者阿里奥斯托一样失去了理智,或者说,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本能地觉着,我理解安杰丽卡的选择,我站在她那一边。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被分在了一个男女混合的班级。我所有的男同学都很快爱上了一个叫莉莉亚娜(Liliana)的姑娘。可我没有。她很漂亮,无可否认,但她比安杰丽卡差太远了。
进教室以前,我们会把大衣挂在走廊的衣帽架上。放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们会抢着去拿莉莉亚娜的大衣,然后把它打开,帮她穿上。这可是场不小的竞争,免不了推搡、拳脚和辱骂。
不出意外的话,总是那两个强壮的家伙赢,乔治和切撒。他们是富商的儿子。他们总是穿得很体面,兜里装好多钱。而我是个穷雇员的儿子,他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不过,有一天,莉莉亚娜看到切撒拿好了衣服,正要准备给她穿上,却冷冰冰地说:“把它放回去!”
切撒一惊,乖乖地听话。这时,莉莉亚娜出乎意料地喊了我的名字。而在看了那一幕之后,我正朝门口走,一回头,很诧异。她真是难得和我说句话!
“安德烈亚,你帮我拿下大衣好吗?”
从那天起,帮莉莉亚娜拿大衣就成了我每天例行的事情。我还因此拥有了各种令大伙儿羡慕的特权,这第一就是陪着她从学校回家。还有大伙儿都不知道的,她竟然主动牵起我的手,在我的脸颊上轻轻一吻,悄悄说“我喜欢你”……
也是在那时候,我发现,原来在每一个女人身体里,都或多或少地住着一点儿安杰丽卡的影子。
1949年底或是1950年初,具体的日子我记不清楚了,我在罗马遇见了另一个安杰丽卡。
那时候,我是国家戏剧艺术学院的注册学生,西维奥?德?阿米科(SilvioD’Amico)担任校长,也是他创办了这所学校。我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这让我在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都能生活得宽裕,只有剩下的五六天不得已陷入窘迫。午饭的时候,为了犒劳自己,我会要一杯卡布奇诺和一个牛角面包。我常去一家咖啡厅,在威尼斯广场,科尔斯路的尽头。
有一天我发现,在我旁边的桌上,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妇人,着装很特别。她也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和一个牛角面包。突然,她抬起脸,看着我。我的心猛地一颤。
她的眼睛很大,炯炯有神,和我祖母艾薇拉(Elvira)一样。我很喜欢我的祖母,那会儿比起父母,我更思念我的祖母。或许是我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太久,老人家才会回头看我。她冲我笑着,那笑容和目光有着难以言说的魔力,瞬间抹掉了岁月加在她双肩上的沉重负荷,让她仿佛回到了妙龄少女的年纪。我无法控制我自己,双腿不自觉地动起来,尽管她并没有叫我。我拿起杯子和牛角面包,站起身,朝旁边的桌子走过去。
“我可以坐这里吗?”
她示意我可以坐下。接着,她有点儿惊讶地问我:
“您认识我吗?”
为什么我应该认识她呢?
“不,但是您,请原谅我,您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
她笑了。那笑容真是迷人。
“您的祖母叫什么名字?”
“艾薇拉。”
“我叫安杰丽卡。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
我一惊,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我早就听说过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的大名,伟大的俄罗斯女革命者,列宁的朋友,是她成就了墨索里尼……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个疑问就脱口而出:
“列宁怎么样?”
一定有不少人问过她这个问题,她回答不下千遍了吧。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他是个钢铁般正直的男人,是个有力量的天使。”
不过,她并没打算和我聊些政治上的话题,因为她很快换了话题,问我是做什么的。一听说我在剧院工作,她的眼睛就发光了。她开始对我不再称“您”,而是用“你”。
“你了解契诃夫吗?”
“知道一些。”
“年轻的时候,”她叹道,“我曾是《海鸥》中的完美的妮娜。”
她开始给我讲契诃夫,她是那样热心,讲得翔实透彻,我简直惊呆了。不过,她给我讲这些,不是为了教给我什么东西,而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像我的同学一样。有时候,无意识地,她会用手抚一抚我的背部。
于是,我发现,巴拉巴诺夫在政治以外,另一大兴趣是戏剧。我要走的时候,向她告辞,她对我说:“明天见!别再叫我女士,叫我安杰丽卡。”
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我再次赴约的时候,心怦怦地跳,像要赶赴一场温情脉脉的约会。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认识了她,我的同学们也不会明白我是在谈论谁。
她从没告诉过我她住在哪里,她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那天是月末,我们已经见了五次面,第二天我就能领到奖学金了。咖啡时光眼看就要结束,我问:
“安杰丽卡,明天我能邀请你吃午饭吗?”
她惊讶地看着我,然后同意了。
“好吧。”
她向我要了餐厅的地址,告诉我,她会在中午一点来,因为还有一个约会,不能和我待久了。她把手伸给我,我弯下腰,用唇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我拥抱了她,她踮起脚,吻了我的脸颊。
后来,她没有来餐厅,也没再出现在咖啡厅。她消失在我的生命里。我久久不能释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