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你第一次接触到英格兰文学。你读到的故事很可能就是由“从前”这两个字开始的。如果你是个生活在20世纪的孩子,你读到的开场白可能是这样的:“从前,距今很久以前,大概是上周五,小熊维尼‘以桑德斯的名义’,独自住在大森林里。”或者是这样:“从前,有四只小兔子,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软塌塌、乱蓬蓬、棉尾巴和彼得。”
也有可能你读到的故事是用诗歌形式来创作的。如果你是个生活在21世纪初的孩子,那么你读到的开场白可能是这样的:“一只小老鼠在昏暗幽深的大森林里散步。/一只狐狸注意到小老鼠,小老鼠看起来很酷”(朱莉娅· 唐纳森,《咕噜牛》,1999)。我们跟着这只小老鼠走进森林,同时也一起走进这个故事。我们有点兴奋,又有点担心。我们会在那里发现什么?这是一段非常传统的文学开场白:“在这人生的半道上,/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幽暗的森林”(但丁,《地狱篇》,亨利· 卡里译,1805)。我们开始了自我发现的旅程;我们会遇见怪物(咕噜牛!),我们会受到蛊惑而偏离预定路线,我们将和一位勇敢的英雄(一只小老鼠!)并肩作战,靠着自己的智慧取得胜利!强烈的韵律感驱使我们一路前行。我们想要继续读下去,并且很有可能在第二天晚上要求再听一遍同一个故事。
当莎士比亚的剧作第一次结集出版时,编辑(他们是莎士比亚的密友和演员同行)建议读者要“读他的作品,而且要反复读”。通常我们不愿意反复阅读昨天的报纸,也不愿意重读在机场书店最后一刻随手拿起的惊险小说、传奇故事或漫画。我们反复阅读的书籍才是真正的文学。有时候,其中不乏惊险小说、传奇故事或漫画,还会有儿童故事。当一本书成为某种文学体裁的代表作品时,它可能会被称为“经典惊险小说”或“经典传奇故事”。如果它已经超越了某种体裁的局限性,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它也可以被纯纯粹粹、简简单单地称为“经典”—比如,夏洛蒂· 勃朗特的《简· 爱》(1847)就不只是传奇故事。塞缪尔· 约翰逊博士在他为《莎士比亚戏剧集》所作的序言(1765)中写道,检验一部作品是否优秀,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经久不衰,始终受到推崇”。
为什么毕翠克丝· 波特的《彼得兔的故事》(1902)和A. A. 米尔恩的《小熊维尼》(1926)能够经受考验,始终受到推崇?一代又一代读者之所以怀着愉快的心情反复阅读这些作品,原因有三点:故事叙述、人物塑造和写作质量。外在的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比如作品里的插图(波特自己画的水彩画以及E. H. 谢泼德画的小熊维尼的世界),这就好比优秀演员的表演让莎士比亚的故事叙述、人物塑造和语言使用一直保持着活力。不过,研究文学的学生首先关注的却是语言技巧、人物可信度和虚构世界的范围。
《咕噜牛》一经出版就获得各种奖项,十年内销售了400万册。2009年,通过电话、短信和网络点击等公众投票方式,《咕噜牛》被评选为“最佳睡前故事”,这类评选在当下被认为是作品受到“推崇”的主要标志。受到中国民间故事《狐假虎威》的启发,《咕噜牛》巧妙地将传统元素与创新性相结合—这是许多潜在的经典作品的共同特征。但是,在高速发展的21世纪,文学审美也随之产生了急剧变化。目前我们无法确知《咕噜牛》最终能否取得经典地位。约翰逊博士认为“经久不衰”的时间至少是100年。哪怕将所需时间减半,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鉴于本书出版于2010年,书中所提及的任何出版于1960年之后的作品都只能算作暂时性的经典作品。
彼得兔让我们得以了解E. M.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1927)中提出的“圆形人物”。圆形人物通常以一些扁平人物来衬托。以彼得为例,他的那些故作乖巧的姐妹们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波特在作品的第一句话中通过简明扼要的方式暗示了这一点,她将三只小兔子分别命名为软塌塌、乱蓬蓬和棉尾巴,却将一个人名(彼得)赋予她们的兄弟。彼得谈不上好或坏。他很淘气,爱冒险,同时又很天真。这样的性格导致他不断惹出麻烦,但是读者知道他最终会时来运转。听过彼得兔故事的孩子们将来会发现,彼得其实就是亨利· 菲尔丁的《汤姆· 琼斯》(1749)和托比亚斯· 斯摩莱特的《罗德里克· 蓝登传》(1748)中所描绘的那一类冒险英雄。
那些杰出的文学人物既是独特的个体,同时又代表着某一类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人群。小熊维尼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鲜明的性格特征;与此同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个教室和每个会议室里,都会遇到热情的跳跳虎、悲观的小毛驴、夸夸其谈的猫头鹰,还有总想着管理别人的兔子。故事场景也具有双重性:小熊维尼的故事发生在百亩森林,作者以英国萨塞克斯郡的阿什当森林为基础,精确刻画了相应的地理环境,让这些动物所经历的超现实场景与作为背景的现实世界保持相似性。与此同时,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一种文学原型,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场景,一处伊甸园,一个带有乡间淳朴气息的地方。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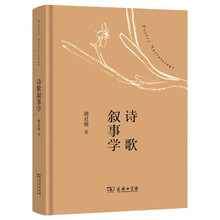



贝特一边带我们探索巨著的精妙,一边提醒我们文学能带给我们无边的乐趣。
——克里斯托弗?赫斯特,《独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