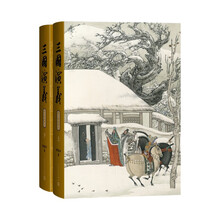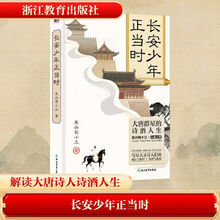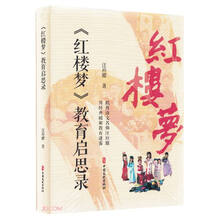《崇文馆:二刻拍案惊奇(注释本 无障碍阅读权威版)》:
话说上古苍颉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凛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多少少人?那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点头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头的,遮莫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说;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流传,同于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每见世间人不以字纸为意,见有那残书废叶,便将来包长包短,以致因而揩台抹桌,弃掷在地,扫置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践,真是罪业深重。假如偶然见了,便轻轻拾将起来,付之水火,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过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来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吩咐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原,官封沂国公。宋朝一代中三原的,止得三人,是宋庠、冯京与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谁知内中这一个,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岂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那个不称羡道是难得?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却错过了不做,不知为何,且听小子说几句:苍颉制字,爰有妙理。
三教圣人,无不用此。
眼观秽弃,颡当有泚。
三原科名,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何不拾取?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偶然记起一件事来。
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有诗为证:翰墨因缘法宝流,山门珍秘永传留。从来神物多呵护,堪笑愚人欲强谋。
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专一精心内典,勤修上乘。虽然顶冠束带,是个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经,做成居士相。当时因母病,发愿手写《金刚般若经》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处寺宇中。后来五代、宋、原兵戈扰乱,数百年间,古今名迹海内亡失已尽,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不知多怎地消灭了。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流传得一卷,直至国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吴中贤士大夫、骚人墨客曾经赏鉴过者,皆有题跋在上,不消说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赞叹顶礼、请求拜观、留题姓名日月的,不计其数。算是千年来希奇古迹,极为难得的物事。山僧相传至宝收藏,不在话下。
且说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原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抑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闲话且不说。只因是年米贵,那寺中僧侣颇多,坐食烦难。平日檀越也为年荒米少,不来布施。又兼民穷财尽,饿殍盈途,盗贼充斥,募化无路。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非舟楫不能往来。寺僧平时吃着十方,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载米上门的了。真个是:香积厨中无宿食,净时钵里少余粮。寺僧无计奈何。内中有一僧,法名辨悟,开言对大众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无此大施主,难道抄了手坐看饿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刚经》真迹,是累朝相传至宝,何不将此件到城中寻个识古董人家,当他些米粮且度一岁?到来年有收,再图取赎,未为迟也。”住持道:“相传此经值价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饥饿,真是戤米囤饿杀了。
把他去当米,诚是算计。但如此年时,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当这样冷货?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
”辨悟道:“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委是不能够。想起来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与我独厚。这卷白侍郎的经,他虽未必识得,却也多曾听得。凭着我一半面皮,挨当他几十挑米,敢是有的。”众僧齐声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索就过湖去走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