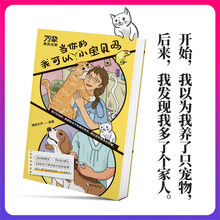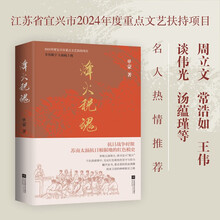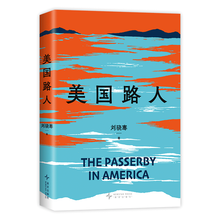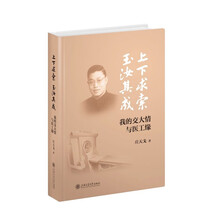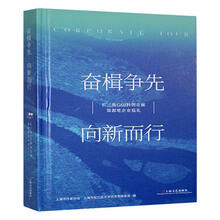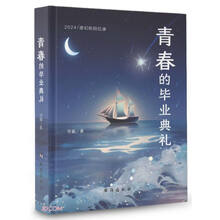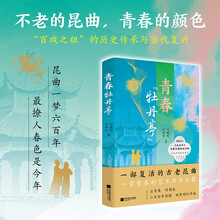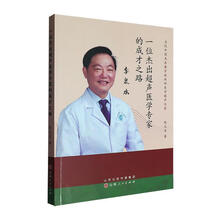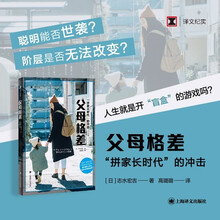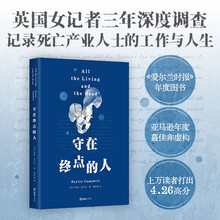《无尽的怀念》:
信仰是人的精神寄托,有坚定信仰的人能表现出伟大的智慧和胆识。罗先生一生从事史学研究,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他说,从事学术研究不能不以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1953年,他对在浙江绍兴发现的二十多处太平天国壁画进行考察鉴定时,由于受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对五花八门的表面现象感到困惑难解,一时难以做出科学的客观判断。后来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对立和发展变化的观点去分析看待问题,才恍然大悟,很多棘手的难题迎刃而解。经过七年边学习、边检查、边改写旧作和对新问题的实践,他做出了科学的鉴定:他认为原来的龙凤壁画是太平天国的真迹,但太平军退出绍兴后,有人在壁画遗迹上增绘了与太平天国信仰相符的图画,所以绍兴的壁画为真假并存的太平天国壁画。真理是认识事物的工具,是人生前进的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照亮了罗先生史学研究的道路。
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罗先生从事史学研究,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他对治学的任何环节都非常认真、细致、诚实,从不马虎从事,坚持科学、务实的态度。他常说,只有老实人,才配当史学家。关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日期,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罗先生在半个世纪内始终考证不辍,所得出的客观结论为大多数专家学者所信服。为了再清楚天历与阳历、阴历的对照关系,他前后花费了四十二年时间,终于得出总结性的定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是一部不朽之力作,他用了四十九年时间才完成。对太平天国政体问题的独特性质,罗先生平时总挂在心中,经常思索,反复推敲,经过三十年的深思苦虑,才有所顿悟,提出了突破性的新见解。
对史料他从来都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对待,首先从辨别史料的真实性入手,从中可以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史料的真实性也就得到确认。吴晗这样评价罗先生:“尔纲在朋友中是最忠厚笃实的一个,可是在著作中所表现的却是一个不安分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他不肯轻信,也不肯武断地否认一切记载的可靠性。”1956年,有人把李秀成的多种笔迹送司法部门法医研究所做鉴定,认为不是同一个人所写的笔迹,从而断定《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李秀成所写。一位精通书法的金石学家也认为不是同一人的手笔,劝罗先生放弃笔迹皆出自李秀成的论点。罗先生难以认同,为此,他下苦功钻研我国古代书法著作,学懂了书法八法,写出《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一文,确证《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赝品。后来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做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
乐于接受批评的人,心底可以始终保持清澈。罗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堪称权威,但他是一个乐于接受批评、勇于承认错误、欣然改正错误的学者。1955年,中华书局编辑曾次亮先生指出罗先生《太平天国史稿·天历志》中“错前一日的假定”不合理。罗先生恍然大悟,非常高兴地说:“这真是一件大快事!”1983年,著名历史学家祁龙威指出罗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小有疵病”,“对个别新资料尚未引用”。罗先生当面向祁龙威道谢:“你帮助我知道了原来不知道的事情。”1984年,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徐川一撰文指出罗先生《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中断言“太平天国举行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的说法与史实不符。罗先生读后深感自愧,虚心地说:我所著述若有纰漏都会贻误读者,表示深深歉意。他毫不踌躇地撰文订误,并恳切地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写信说:“徐川一同志在他的大著上指出我的错误,好似和风煦日一般的温暖,使我读后心旷神怡。请加编者按语,以我为‘的’,论著者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一位名家巨匠,能有如此博大胸怀,成为当时史坛上的美谈佳话。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