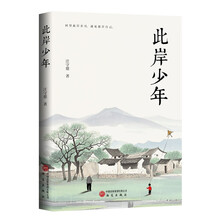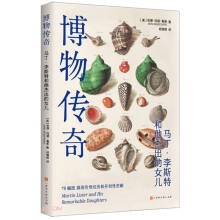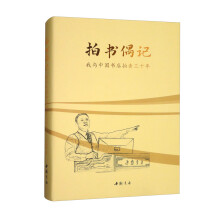情感波折
我和王蒙的情感联系曾有一年的中断,那是因为我的情绪多变。弥合之后,我们都体会到: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在到东四团区委帮助工作前,我已和王蒙相识。那时他是团区委的干部。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借河北北京师范学校的房子办公。7月的一天中午,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我一进去他便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感觉他不陌生。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式样旧,又不合体,个儿不高,脸瘦长,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于是不停地往上托。
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他说,是那一年春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
夏天这次会面,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
这一年,王蒙只有18岁。
不久,他向我表示了好感。
有一次,他鬼鬼地笑着问我:“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我一愣,说:“我哪里会知道。”心想你不过才18岁,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他说:“是周曼华,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觉得她真美。我想将来我长大后,就娶像她这样的人。”说完我们都笑了。
“那年你多大?”
“12岁。”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不大,智商很高;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洋溢、诚挚幽默。
秋季里的一天,我们去阜成门外(现在的钓鱼台附近)郊游。当时那里一片荒野,有农家小院,护城河的流水十分清澈。我们在一片绿地上席地而坐。王蒙为我背诵了许多古诗,我更加感到他的少年老成。
还有一次约会,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我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就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站在那里等我。我心想,怎么能带梨啊?“梨”的谐音是“离”,认识不久就“离”,多不吉利呀!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递给我一个,“吃梨!”了解他后才知道,所有水果中他最喜欢吃梨。可见他从来不在意没有“道理”的“道理”。
还有更有趣的事——
一天我们走在天安门西大街上,我有点儿累,就说:“咱们坐电车吧!”
他不肯。谁知电车一进站,他却把我推上去,自己关在电车外。我在上面着急,他在下面笑。电车当当地往前开,他就在马路上跟着电车跑。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我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
1956年,我在太原工学院读书。3月末的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来到学校的前门庭院,无意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蒙”两个字。我很好奇,原来是《火花》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春节》的作者,误认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
第四节课后,我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当年3月号的《文艺学习》,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说《春节》。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直接坐到了阅览架的地上,小说中的“我”,呼唤的不正是我吗?
我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谨,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
我想不管他曾受过多大的委屈,看了这封信之后,也会迫不及待回信的。
盼啊,盼!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
出乎我的预料,信如黄鹤,一去杳无音信。
那年暑期,在我即将离京返校时,王蒙突然来到我家,我非常惊讶。他怯生生地说:“我们出去散步吧!”我们一时无话,默默地走着。一阵沉默后,王蒙直率地说,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的生活难以想象。
我问自己,没有王蒙的日子,我是不是也同样?
感谢命运之神赐予我的厚爱,我和王蒙最终走到了一起。
分别后不久,9月9日,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我。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复习功课。一阵脚步声后,有人在敲门。没有想到王蒙站在门口。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说。
“我来了不好吗?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同学,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认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选,劝我跟王蒙好,一定要我遵命。
我领他参观了我们的新校园,又看了看侯家巷的旧舍。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我没上过大学,大学生活多好。”
在校园里,我们照了许多相。可惜胶卷冲出来后,却是一片空白。原来是胶卷没有上好。那部相机是王蒙用第一笔稿费买的,苏联制造,镜头还好,只是装胶卷太麻烦,需要在胶卷边缘剪裁下来一个槽,才能上好,这也是用了好久才总结出来的。尽管没有留下照片,但至今抹不去那时的记忆。
那次我们还去看了丁果仙的晋剧《棒打芦花》。一到声调高亢的拖腔时,王蒙就兴奋地鼓掌,我倒觉得过于刺耳。散戏后没车了,从柳巷到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我们便步行回校。一路下来走到移村的桥头,这座桥是新建的,桥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学校。过桥时,王蒙说:“哦,风好像小一些了。”我说:“哪里风小了,是桥栏杆把风挡住了。”话音未落,他笑得前仰后合,问我:“桥栏杆还能把风挡住?”至今我也弄不清当时怎么说出那样的蠢话。以至这些年来只要我说话做事不太贴谱时,他总会说“桥栏杆把风挡住了”。
太原海子边公园的小巷里,有家小餐馆,生意红火。那个年代,生意做得如此热气腾腾已属不易。我们找个座位点了山西名菜过油肉,只见一名方脸男服务员,头戴小白帽,一手高举着菜盘子,脚下生风满堂飞,口中吆喝着:“来了!三鲜汤一碗!”……同时又忙不迭地招呼着另一桌的顾客。那种热情,那种微笑,那种从容,以后多少年也没见过。王蒙在他的一篇散文《鳞与爪》里描写过我们对这个服务员共同的美好印象。
那一次的经历,我至今难忘。
我体会到王蒙常说的一句话:“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特殊婚礼
结婚一年后,王蒙成了“右派”。而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却浑然不觉,一派欢天喜地。多年以来,王蒙不断地感慨:“爱情和文学的成功,使我成为幸运者。”
深深的海洋,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荡的心。
在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王蒙向我求婚了。
我踌躇不定。那年我才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没独立,还没有条件考虑婚事。
然而王蒙接二连三地来信。我想,那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和语言能力真是帮了他的忙。频繁的信件来往,有时甚至一天两封,而每封信都像诗,都像散文,亲近、体贴,又充满才华和理性,让我无法也无力拒绝。
在他频频的求婚攻势下,1957年1月28日,我们结婚了。
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但我们已经是兴高采烈,精心地在房子里安置了几件还算体面的家具。软椅、转椅、手摇留声机、玻璃门书柜……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伴娘、伴郎和牵纱童。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礼服,王蒙穿的是一身藏蓝色海军呢的中山服。
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用餐时没有来宾。王蒙那个时候对于热闹的婚礼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所以,我们的婚礼,王蒙根本就没有告诉几个人。另外,当时王蒙刚调动工作,与新同事来往还比较少,与熟悉的老同事之间,还因为特殊时期,处在一种不正常之中……
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波,涌动着一股暗流。舆论对王蒙非常不利。我们选这个时候结婚,很多人不来很自然。
当天下午,亲朋好友来祝贺,送来花瓶、相册、衣料、书签,这些礼品在当时已很珍贵。但是我仍然觉得,婚礼不应该这样冷清,我隐隐有种不祥之感。
客人们说说笑笑。虽然桌上摆的喜糖、花生、脆枣现在看来都很低劣,却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
我的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除了问安、祝福以外,显得有些拘谨。
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唱片吧!
我们放了苏联的《列宁山》、周璇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还有《意大利随想曲》。接着,王蒙自告奋勇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大家恭维他可以当歌唱家。
或许受了王蒙的感染,大家唱起《深深的海洋》。这是当时学生们最爱唱的歌。
在同学的祝福声中,我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婚庆。
婚后不久,1958年年初,王蒙在“等待处理”期间,去景山少年宫基建工地当小工。
后来我们的房子作了调整,跟王蒙的母亲一起住后院。房子是一明两暗,我们住一间,还算有自己的一个小窝。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1958年5月,王蒙被戴上“右派”帽子,秋天被下放到门头沟区桑峪一担石沟劳动,我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期间我经常回到我母亲那边住。而我们在小绒线的房子也因此没有了往日的温馨。
那段时期,王蒙从山沟回来,我们俩很难相遇。据说上面担心这些改造者如果预先知道休息日,会有问题,所以一般是当天宣布,当天开始休息。而他休假只有两三天,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徒步翻山越岭,花去半天时间。到了北京城,首要的事是尽快找到我,上哪儿去找呢?到孩子姥姥这边,我却在奶奶那边等他,当他赶到那边,我又回来了。
为此,他落下了病,常常在夜里做同一个梦,给我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错了就是打不通,好容易接通了,“喂、喂”了一阵子,说话的人却不是我,于是又开始不停地重拨。
1989年他卸任部长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我又梦见了你》,里面记述了这个情节。我知道,这中间包含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和王蒙相识、相恋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18岁——后来,他写了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十分贴切的名字,或许我最能心领神会。
王蒙曾问过我:“你怎样证明你的真实的人生?”
我说:“有你了。”
王蒙又问:“怎样证明我的存在?”
我说:“有我了。”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人生旅程,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婚外的风流故事,他更不会去“拈花惹草”,我们珍惜的是我们自己。
王蒙常常感慨地说:“家庭就像健康,你得到的时候认为一切你所获得的都是理所当然,甚至木然淡然处之;而当你失去之后,你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不应该失去。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憾事,人间没有比爱情和文学的成功更令人骄傲的了,我是一个幸运者。”
身世不幸
和王蒙的相识,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王蒙身世不幸,这或许更成就了他的才华。
幼年的王蒙,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由于种种差异,使得父母的关系水火不容。外祖母、母亲和姨妈组成联盟,一致对抗单枪匹马的父亲。有一回,王蒙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刚走到院中,一盆才出锅的热绿豆汤兜头泼过来。直到今天,都无法抹去滚烫的绿豆汤烙在王蒙心中的印迹。
王蒙印象最深的是他5岁那年,父母不知什么原因又闹了起来。妈妈哭着把王蒙藏起来。王蒙心里很恐慌,但他还是懂事地劝妈妈:“你不要哭,等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一会儿,他又想起爸爸,便问妈妈:“爸爸呢?爸爸哪儿去了?”妈妈却伸手捂住他的嘴,吓唬着说:“别出声,不许你见他。”
王蒙的堂姐从小跟三叔(王蒙的父亲)好,见三叔可怜,偷偷跑过去,悄悄对他说:“他们都在家,藏起来了。”父亲手里拿着巧克力,却找不到孩子。他坐在一把褪了色的旧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知什么时候,屋门被反扣上,推也推不开。父亲大声喊着:“快把门开开!”王蒙站在门外,扒开门缝往里看,只见爸爸像愤怒的狮子,来回不停地走着;一会儿又坐回那张藤椅,点着烟,吸进去,吐出来,屋里弥漫着一团团的烟雾。
这种残酷的事实,使王蒙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相识以来,他并不轻易提起这些。我能感觉到,他不愿触动这块伤痛,但是,他却常在说,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这是他的切肤感受。
王蒙上学后,不喜欢放学就回家,宁愿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因为他害怕看到父母吵架。7岁时,有一次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忽然闻到一股肉香味儿,原来是一家烤肉店。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各式美味佳肴,真想美餐一顿。但是他没钱,也不可能向爸爸、妈妈要。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离开烤肉店,照直往前走。无聊的他,看到路边的一家棺材铺,顺手推门走进去,看看这口棺材,又看看那口。突然问道:“掌柜的,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店铺掌柜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孩。“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王蒙自觉没趣儿,赶紧退了出来。
小时的王蒙打发这种无聊、寂寞生活的方式有两种,幻想和读书。冬季的中午,遇到好天气,太阳暖暖的,大人在午休,他就会陪着猫,坐在房檐窗下的台阶上,看树枝上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想象如果自己有一双能飞的翅膀该多好!思绪一下子把他带到童话世界里,他可怜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叹七个神秘的小矮人……他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梦。
王蒙自幼爱看书。9岁时,他独自去离家最近的民众教育馆内的小图书馆看书,入了迷。直到天黑,整个馆里就剩下他一个人,管理员不断催促,他才回家。他在那里看了《少林十二式》、《太极拳式图解》、《十二金钱镖》、《小五义》,看了《悲惨世界》和沈从文、丁玲的书。他对文学的兴趣,或许从那时候已经开始孕育。
直到有一天,王蒙不经意地流露出深藏心底的痛苦。我们的儿子山儿3岁那一年,我在花市书店为他选了一本活动的小画册。这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会在掀动中不断变换图形。一会儿头部是火车汽笛,身子是拖拉机,脚部是汽车轮子;而翻过一页,脚会变成雪橇,身子成为机翼,头部成了旗杆。
王蒙看到后不住地问:“这是哪儿来的?”
“买的。”
“哪儿买的?”
“书店呗!”
我很奇怪,为孩子买的一本小画册,怎么招来这么多的盘问?
王蒙说:“我小时候,也曾有过这么一本,是父亲给我买的,羊角、鹿身、马腿,变来变去。那时,没有别的玩具,觉得很好玩儿。”接下去他说:“这种扭曲,使我想起许多……”
这句话,让我感到震撼——多年来,他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他把这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80年代末,他写下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是他写得最痛苦的作品。他说,写起来有时候要发疯。别人说,这是王蒙唯一一部家族小说,身心和灵魂全部沉浸在小说中。而王蒙自己也说,这部小说付出了很多个人情感,有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经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