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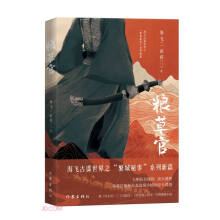






唐高宗永徽年间,京城东门外五里,一个松林密布的小丘之上,矗立着一座三层酒楼。这座被叫作“悲欢阁”的酒楼,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虽不至破旧,但偶有的斑驳已经显露了它的老态。
这里是京城官员们专门用来迎送外放官员的地方,去时的送别,任满后的相迎,皆在此处。荣辱悲欢,生离死别,是这座酒楼里见得最多的场景。
而今,三个男子就坐在悲欢阁的顶楼,各自闷闷地喝酒。在他们可眺望之处,是一条笔直向前的大道。
这是阴雨的三月,已经连下了二十多天的毛毛雨,没有一个晴天。被雨水打落的桃花和杏花,在地上散落成狼藉的花瓣,于这雨天更添几分惆怅。小丘外的一棵古松下,两个赶车人正缩着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等着雨停。
这三人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其中两人戴着主簿的锦帽,他们送行的第三个人则戴着一顶地方县令的黑色帽子。
此时,他们已吃过了简单的午膳,便是离别在即了。他们搜肠刮肚地想要说些合乎时宜的话,可话到嘴边,又觉苍白。
突然,梁主簿重重地放下酒杯,怒气冲冲地对那县令说:“太过分了!完全没有必要!你明明已经得到了大理寺主簿的职位,跟侯兄是同事了,我等本可以继续在京城逍遥度日,而你……”
那县令捋着他那把漆黑的长髯,颇不耐烦,毅然打断他说:“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何况……”他面上突又现出歉意的微笑来,站起来说,“我对你说过,对于那些纸上谈兵的官司,我早就厌倦了!”
“那也没有必要离开京城呀!”梁主簿说,“这里有趣的案子还不够多吗?那个户部员外郎的案子不就很有点儿意思吗?那个好像叫王元德的,是不是杀了自己的下属,还从银库盗走了三十锭黄金?侯兄的叔父户部郎中侯广大人,可是天天催着大理寺要消息!侯兄,你说是不是?”
穿着品官补服的侯主簿一脸担忧,犹豫了片刻,才说:“我们至今都还没有那罪犯的任何线索。狄兄,这可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案子!”
“你是知道的,”被叫作狄兄的人,也就是狄仁杰,淡淡地回应,“这个案子可是大理寺卿亲自过问的。你我能看到的,不过都是些例行公文和抄本,除了文书,还是文书!”说罢,他伸手取过锡制酒壶,给自己满了一杯。
三人尽皆沉默。三人都在京城任职,对每日案牍劳神,都颇为不喜。可不喜归不喜,仕途前程总是读书之人的毕生追求。能在京城任职,已是常人不易修来的机缘,哪有说放弃就放弃的。然而狄仁杰的固执,非是常语能撼动的。
半晌,梁主簿才换了个话题:“就算你要走,也要找个好点的地方去。那蓬莱不过一个小小的海隅边陲,哪里比得上这京城的繁华富足?!更何况还有上任县令被杀一案没有被侦破,别人避之不及,你却毛遂自荐!”
狄仁杰的眼中突然迸发出神采来:“你们想想,我还没有到任,就有一桩大案在那儿等我!那不再是文书,而是活生生的案子!我大展拳脚的时候终于到了!”
“别忘了,这蓬莱县令被杀一案,可是刑部堂官亲自去勘察的。”侯主簿冷冷地说,“他勘察无果不说,带回来的案宗中,最重要的几札信函还不翼而飞了。”
“这不摆明了吗?”梁主簿接着道,“那县令的死,肯定跟京城的官员脱不开干系。你要去蹚这摊浑水,怕是丢了前程事小,丢了性命事大!”
梁主簿趁热打铁地恳切苦劝:“狄兄,我劝你重新考虑考虑,还为时不晚。你只要稍微推诿一下,说自己突发小恙,就可以告上十天的病假,吏部自然会另行委派他人前去。狄兄,你一定要听我一言!你我是知交好友,我才会跟你说这肺腑之言!”
“多谢二位,关怀之语,足见君之高谊。”狄仁杰的神情温和起来。三人相交不久,但这般话语,确是深交之人才能说的。这不由得他不动容。
他和颜对着二人说:“你们俩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我留在京城,必然能有所发展。但这样毫无功绩地一路升迁,却非我所喜。一日为官,就要上对得起天子,下对得起黎民。不仅要勤勤恳恳,更要有所建树。不如此,不能心安。而蓬莱,便是我事业真正开始的地方。”
“也可能是结束的地方。”侯主簿叹息了一声,起身近到窗前,见两个赶车人已经从躲雨的古松下走了出来,开始各种准备工作,不由得叹气道:“雨停了。”
狄仁杰站起身来,拱手辞别:“我该启程了。”
三人携手而行,直到狄仁杰上了驿车,梁、侯二人才摇着头,叹息着离去。
此去,便是山高海阔;此去,便是生死未知。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