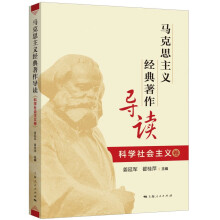《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18)》: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作为真正的财富,其运用是与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由时间一部分用于消费活动以此来恢复劳动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正常消耗,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以此来获得生命在逻辑层次上的跃迁。然而,在这种填充机制的引导下,生命本身变成了一个由某个中心权力所建构而缺乏特定内容的空洞形式。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所预想的自由时间的双重目标全都落空了。阿伦特曾激烈反对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对生命基质的填充。在她看来,这种填充机制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政治后果:“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一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②随着需要的仿真化和虚拟化,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填充逐渐摆脱物质载体而变得无孔不入,从摇篮到坟墓、从身体到灵魂,遍布于生命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填充之物的空前丰裕和生命意义的极度空虚相反相成,资本权力的日益催逼与生命基质的腐化堕落并行不悖。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自由时间填充机制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逻辑和治理方式,一方面实现了工人发展自身社会需要的虚假诉求,并将这种诉求变成价值增殖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缓解了资本家生产过剩的压力,消解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去革命化。这就意味着,填充机制作为侵占机制的补充,将资本与工人之间的零和博弈转变为历史性“和解”,又以二者“和解”的名义在广度和深度上强化他们相互间的对立,最终进一步巩固资本增殖逻辑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资本主义时间管控下,工人犹如一台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不仅在劳动时间内从事机械般的“死劳动”,而且还在自由时间中享受着机械般的娱乐消遣,一切都依赖于资本逻辑的运作。
资本的文明是以工人的野蛮为代价的,工人自身发展的社会需要始终得不到满足。资本为了得到驯服的劳动力,不惜钳制工人的生命基质。自由时间,在工人那里,只是劳动时间的延伸和变形,只不过是资本统治权固有的世袭领地,其作为自由个性展现境域的原初含义被遮蔽住了。随着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剧,工人日益沦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其个人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劳动时间长短的区别。由此,工人的政治想象力日益变得贫瘠,再无暇也无力去想象可能的生活方式。工人自主性的日益萎缩,意味着资本统治权的愈发强大。资本统治权不仅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监督工人有纪律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而且使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超出自身生活需要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与直接强制劳动的野蛮暴行相比,资本通过侵占和填充自由时间这一文明暴行,获得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学揭露了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隐性暴力,理应作为当代生命政治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与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相比,马克思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学具有三个特性:第一,无论是福柯所揭示的监狱,还是阿甘本所分析的集中营,都是生命政治所发生的非典型性场所,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工厂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性场所;第二,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以整个人口为对象,侧重于对安全机制的分析,而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生命控制;第三,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权力侧重于刑罚和法律,而时间管控则侧重于对人的生命基质的钳制。一言以蔽之,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关注的是主权权力(政治权力)对生命的规训和管控,而马克思则关注的是资本权力(经济权力)的统治。相对而言,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更具隐秘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