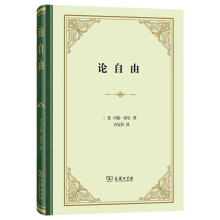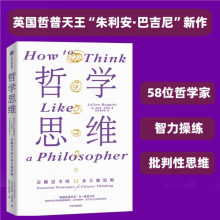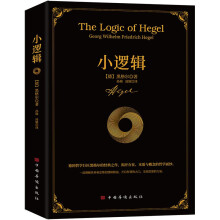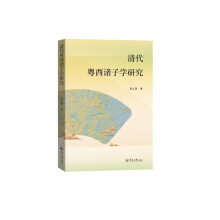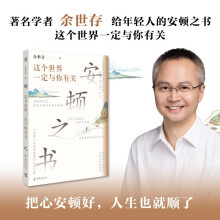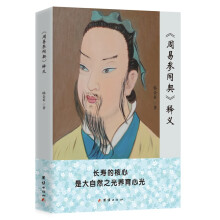《舍斯托夫文集(第3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哲学》:
《手记》的序言严重地影响了正确理解《死屋手记》。为什么需要这一部分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呢?好像《手记》是由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良奇科夫先生,一个因杀死妻子而服苦役的囚犯写成的。是为了检查吗?然而,要知道,《手记》中丝毫也没有隐瞒,戈良奇科夫是由于政治问题而被迫服苦役的。例如,当他忽然想参加囚犯们的意见时,其他的政治流放犯就提醒他,他的参加只能把一切都弄坏。“他们对他说,请想一想吧,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还有其他的地方也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手记》的作者不是一个刑事罪犯,而是一个政治犯。一句话,序言不可能蒙骗检查。如果说它欺骗了谁的话,那么就是欺骗了读者,使读者对说书人戈良奇科夫本人有一种不真实的理解。从序言部分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生活而已经永远死去的人。他没有同任何人说过话,甚至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他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的日子。他走出自己的小室只是为了用劳动来获得可怜的几个戈比。他在孤独地死去,他被大家所遗忘,他也忘记了大家。当然,还有一些被活埋的人不仅在监狱里,而且是在外面。然而这些人一般不写自己的回忆。如果写的话,也大概不会用《死屋手记》的腔调。他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可以看见囚犯欢乐的眼睛呢?他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可以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中找到的各种“善”的感动的生命力呢?戈良奇科夫也许可以去描写暗无天日的永恒地狱(我重申,即便开始描写,这种人也写得很少)。他没有希望——难道这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希望都完了吗?这我不想作为一个原则来引用(读者还没什么可以异议的),我暂时仅仅“从心理学上”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写《手记》的时候,在服苦役的时候,就曾是戈良奇科夫的直接对头。他首先是一个充满希望、伟大希望的人。所以他认识世界的方法,他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这就使他的心免于生锈,这就是他之所以能原封不动地保持服苦役前的那个完整的“博爱”思想的原因。如果他的心灵和戈良奇科夫的心灵一样总是在诅咒,那么博爱能帮助他吗?是像他自己所说,“信念”的精神在鼓舞着他,还是相反,无论它多么崇高,“信念”本身需要支持呢?这一问题提得非常恰当。戈良奇科夫没有写成《死屋手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成了。如果在这部小说中有时能发现明显的不一致,如果有时你看到一些个别的场面和意见突然破坏了“博爱”情绪的总的和谐,这就应该被看成是希望的表现。要知道,希望是最变化莫测的。因为它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许,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的时候,希望不止一次地抛弃过他,甚至长时间地抛弃过他。就在他感到自己确实永远和最后一个人一样的时刻,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后来应该发展成完全是另一种哲学,一种真正的苦役哲学,没有希望的哲学,一个地下室人的哲学。所有这一切我们还不得不费许多口舌来说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