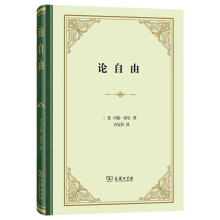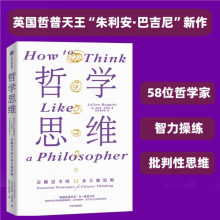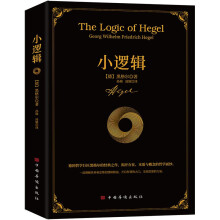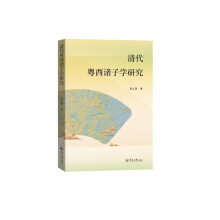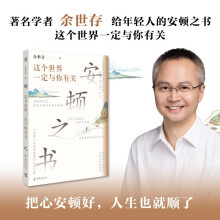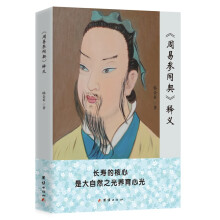第一讲 不确定的漂浮尘世,心安何处
在当下热火朝天的后现代或者全球化时代,一切似乎都欣欣向荣,但一切又都是那么的不确定。我们似乎漂浮着,不知落脚何处、心安何方。
当下的社会,消费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狂热地流行着,我们的消费和功利比任何历史时代都更加盛行。人们害怕政治剧变而遭受损失,害怕私人财富一夜之间就会贬值而一钱不值,害怕食品药品环境污染而害上不可治愈的疾病。于是,人们四处投资力图挣得更多的财富,人们移民海外努力寻找所谓的安全之地。各大传统“复兴”了,各种新兴宗教诞生了。只是人们不知,在全球化的时代,哪里才是绝对的安全之地。我们似乎不知道,或者害怕知道这种不确定的境况。我们敏感于那些追问自我的深奥哲学问题,我们敏感于巨大的开放性,我们敏感于那些带来范式骤变的宏大但却关乎个人命运的问题。我们寻找一种安全而免受伤害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努力于精修、禅修、瑜伽、内观等等“时尚”活动。这些遍布全球的运动之兴起,除了现代人对于身体健康、体形健美等诉求之外,更多的原因应该是,在这个漂浮的尘世中、在以消费和功利为主要生存状态下人们对自己的本性或灵性的诉求。在看似全球化的瑜伽、静心、禅修等运动表象下,实际却是人的某种“回归”。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人们广泛参与灵性时代的实践,也是人自身对宇宙伦理和地球危机的某种自觉回应。
确实,在这一不确定的漂浮尘世中如何安置自己是个大问题。不过,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就已经向前进了一步,因为这一意识的种子已经在生命中成长。
1966年我出生在浙江兰溪。年少时,似乎并不像现代人一样十几岁就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一直到上大学,我的自我反省意识很少。当时入学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我是坐火车从兰溪出发到杭州的。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坐过,到了学校好几天头都晕乎乎的,一直感觉床在摇晃。早上起来也不知道人在哪里。我迷失在了城市中。后来,我去北京讲学。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北京城很大,我就像蚂蚁爬到了一个巨大的轮盘里面,没有了东南西北。有时候人在宇宙中确实没有方向,不知道可以到哪里去。事实上,方向完全是你自己规定的或者说是被你规定的。你说你要干什么,你会成为什么。这就是意志,英文里叫will,是你的意志决定着你的方向。所以,你本来没有方向,是你自己的意志创造了方向性的东西。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人都是在一个自己自以为然的创造性中度过的,甚至浪费掉了。
人在世上生活,很多事情是偶然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佛教里讲“因缘”这个词,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偶然,即因缘巧合,刚好就发生了。
偶然是个大问题。因为偶然,我们不知落脚何处、心安何方。今天我到这里来和你们交流也是因一个非常偶然的意念。你们的禅师偶然有这样一个念头,然后他就发出这样一个邀请。因为他的邀请,我就看到了另外一个新世界。这是很偶然的。这里没有太多的必然性。因为是偶然的,此行就不会再重复了。人在这个世上,没有东西是可以重复的。这一切发生了就发生了,不可能重复。《百年孤独》中有一段话,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这是不是很悲凉呢?
我上了研究生以后,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读书。读书仍然只是我的一个习惯。读完研究生以后,因为没有工作,就继续读博士。读博士是要做研究的,我就跟着做研究,也写一些文章。有人告诉我,作为一个学者,你应该专注在某个方向研究点东西。那是1993年,我们那个领域在大学里也没什么资料。真是偶然啊,有位意大利的学者来中国做访问,送给了我们研究机构几本书,碰巧我在资料室就碰到了这几本书。其中有几本是基督教的宣教书,于我没什么用,但有一本不是,它是本学术书。我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写了很多书,书中涉及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写到了中国的道教。我觉得这书好,作者的研究领域很宽。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我要研究这个人的学术思想。1995年我贸然给这位作者写信,寄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当老师。但有人告诉我,他已经退休回英国伯明翰了,那人是好人,他把信转寄到了英国。这位作者收到信后,立即就给我寄来了他的书。我写信给他说,我要研究你十五年。果然,我就研究了他十五年。由于这个原因,我还去英国见了他好几次,在他身边待了将近一年。他就是著名的希克教授。看到他的那本书是非常偶然的,碰到那位好心的美国教授(他就是著名的过程思想家格里芬教授)也是偶然的,而当时中国还没有人研究如何处理宗教间关系这样的学术问题,我就决定研究他。于是,在这一连串的偶然下,我写了三本关于他的学术思想的书,翻译了他的八本著作,吃他的饭一吃就是这么多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