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 师
他挥毫。山川逶迤,藏在几棵垂柳的
斜对面,一个渔翁等待着将傍晚拿走
事实上,花鸟虫鱼都是
黑色的,画家难以将不可理解的世界
变成佛。我相信诸事诸物都在方寸间
窗外停泊的孤帆不可能
离开渡口,一如我,不会离开自己的
困境。他止了毛笔,端详,整幅画在
一杯茶中走动,里面蓄满静谧和滂沱
山川颂,或一种受难
整座西山一滴滴陷入夜晚,大雨滂沱
空气中弥漫着草木和台阶,以及河流
一般哗哗的喜欢
越喜欢就越悲伤
在人间,庄稼是唯一的受难者,而我
一个被雨拦住的人,回家是如此困难
山川不忍心细看。云朵中,目力难以
企及的神,怀抱日出日落,辗转难眠
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
我爱这悲怆的大地,爱一只大鸟自傍晚
掠过黎明,爱树木静静地站在微水湖畔
不谙世事。当然
我也爱灯火和废墟,爱它们历历在目的
尽头、不可磨灭的起始,爱这种空洞的
踏实
——一些事物注定消失在相爱里
我爱这种状态:人人互不相识,又胜似
旧友,他们抬头仰望星辰,低头便落入
尘埃,他们不生不死
替时间熨平人世的一些起起伏伏
我也会悄悄爱上伤心,爱上鲜有的快乐
爱上这个凡尘中属于人的泪眼,和它们
浩浩荡荡的收集者:
哪一种泪水还没有流过
每日每夜,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
今则天各一方,风流云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非所谓“当日浑闲事,而今尽可怜”者乎!
万物均匀地分布在不规则里,除了爱
爱你的人在不安中
塌陷。当一座水塔是我们的暮年,你
无法理解它的垂直和荒废,夜莺在它
身上唱歌,我们在
它的阴影里转移着
噪杂。匮乏面前,我们就是匮乏本身
水塔基座的水泥,一脸斑驳兼有不屑
当两个孩子围着它
转圈,已注定他们的生活将沿着圆柱
深入不测:若干年后,命运一墙之隔
却没办法理解彼此
——命运就是圆柱型的漩涡,推你的
则是一个陌生的缺席者。也不必悲伤
这水塔终有倒塌的
一日,如同你我,毁于无知和不可知
四
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
一条马路在寻找着自己的尽头。城市
和我们并排而立,没有谁会站在原地
除了台阶。大楼
试图繁殖
自身。行人也会盲目,黑暗递过来的
光一时无人识得。搅拌机、中央空调
都源于一种疑问
没有答案
人类就练习出卖自己:水泥是俗世中
最大的隐喻,它的逻辑和我们的肉身
如出一辙。借助
各种石板
钢筋,以及日夜轰鸣的潜意识,生活
已经无法攀登,一部电梯将我们送到
高处,又拒绝自
原路返回
置身虚空中如同脚踏实地。没有人会
觉得不可思议,一条新修的柏油路在
寻找着尽头,大楼似是而非,缺少了
不可多得的敌意:饱含世人如同遗体
五
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
如此清晰,玻璃杯、玫瑰、钟声以及
一条被马蹄击碎的道路
得得声中
墙壁长满青苔:一种失而复得的生物
我习惯了在世界的一侧沉沦,厄运和
我有一种默契,而时间
不忍卒读
却充满清规戒律。有人
喃喃低语:我这张脸已经风化,缺少
营养和同情者。他佝偻着身子,举着
一个没有蜡烛的纸灯笼
恭候大雨
罪恶只供人欣赏,牢狱
是虚设的,那些蝇营狗苟之人曾屈从
俗世,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十年前
一只孤鹜自落霞中出发
日光回转
钟声喂养过的玫瑰,又悄悄躲过一劫
——一些不确定的事物忠于某种衣服
六
夏月柳陰浓处,菡萏香来,载酒泛舟,极有幽趣。余冬日往视,但见衰柳寒烟,一水茫茫而已。
每一棵树都住着一个神灵,当它们被
砍倒,一些会成为光的知音,一些则
装着同样被砍倒的
殉道者,做蚯蚓的
好邻居。此时,不必要担心鸟巢或者
在树杈间追逐光源的松鼠,它们来自
草丛,和一把轰轰作响的电锯刀一样
操蹩脚的人类口音
刀斧和倒塌不过是
生活中最平易近人的一部分。当我们
将树木砍倒,那些行将枯萎的叶子也
会兔死狐悲。一个
最为日常的情景是,在树桩上坐下来
点一根烟,舒适、疲倦和戛然而止的
年轮将会沁入身体
慢慢成为一种顽疾
树木胸怀鸟鸣,我们怀揣刀斧和慈悲
动 静
整个庭院浮在黄昏之中,万物和彼此
道别,即将回到
黑暗。此时,一声虫鸣唧唧
而响,我们迅速想起与对方的关系及
面目。静谧里总有一种闷雷包藏祸心
蒲松龄
客栈、破庙、荒宅,有人自墙壁下来
影子是个好的去处。铜镜不懂得疼痛
山川不懂得
留宿,将眼前的面具视为
一生,拿滚落的石块当作加冕。聊斋
先生例外,他笑,他哭,他家的窗子
有几个破洞,但不属于他
一个人的。鬼神都在尘世领众生之苦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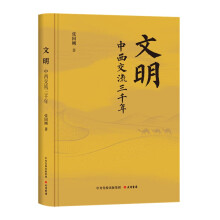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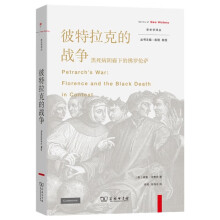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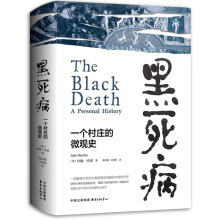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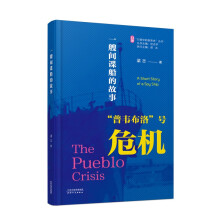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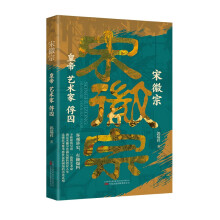


日前,……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李瑾诗歌创作所取得的成绩,认为他一方面将现代诗与各种文学体裁结合起来,创造了戏剧体、日记体、书信体、年谱体、回忆录体等样式,拓展了现代诗叙事和抒情的空间;另一方面,他善于借鉴经史子集、古典小说和散文等经典和名篇,将古典资源整合成为新诗的内在元素和外在修辞。——《光明日报》
李瑾创作中的“古典”“日常”都是一种母体,他真正表达的是时代、当下及其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深刻烙印。尤要指出的是,李瑾作为一个抒情主义者,拒绝用晦涩的词句、玄奥的意象,他在营造意境,以情动人的同时,惯于锤炼“问题意识”,展开“生命之问”。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