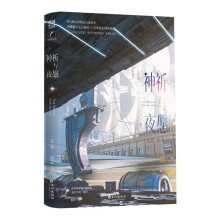《那时候——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记忆》:
我们村的大白菜,个大,形圆,菜心包得紧绷绷,出菜多。吃起来除了特有的白菜香,还有淡淡的甜味。无论是凉拌、炒食还是包饺子,吃过的人都竖大拇指。
吃起来的美味,种起来却不易。大白菜是水菜,一生离不开水,尤其是包心的时候,几乎一天要浇一遍水。
那时候机械少,一家一般也买不起水泵。就是买了,菜地像老和尚的百衲衣似的,也派不上用场。浇菜,都用水车,那种管链式的铁水车。
自留地一般都在靠近村庄的地方,方便于活。那时候水井比较多,大都是青砖垒就的,井口用石头砌成,井壁的青砖湿漉漉的,砖缝里三三两两地长着苔藓或细长的荒草。井水幽深清凉,夏天水位高,一场大雨过后离井口也就一尺多,冬天则相对深一些,有时井口冒着袅袅蒸气。
几乎每个井口的上面都安着一架水车,集体统一配的。水车上面的铁榔头上横插着长长的粗木杠,推水车用的。
一架水车,附近有自留地的几家共用。时间长了,谁家哪天用都熟悉了,默契了,用不着再相互打招呼。反正没听说过有因为争水车生闲气闹乱子的。
推水车,刚开始是比较轻省的,因为水位高,一个人就可以。后来水位慢慢下降,越推越沉,一个人推就吃力了。最让人丧气的,是由于水车齿轮的老化,提水的铁链与齿轮咬合不紧,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哐啷一声滑落下来。这时就需要停住,提上铁链重新挂好,再推。这就有些耽误事了。也怪,越是着急,怕耽误事,就越掉链子,让人无可奈何。
那时,我八九岁。父亲在百里外的邻县上班,家里就我、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母亲要强,什么活也不落在别人后面,自留地里全都种上了大白菜。母亲忙完了地里又忙家里,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实在忙不过来了,就喊来二舅帮忙。
“白露”过后,大白菜进入了旺盛生长期,几天就要浇一次水。天气早晚凉爽,中午还是热辣辣的。
给白菜浇水的活儿基本落在了我和二舅身上。二舅左胳膊残疾,一条腿还有些瘸,四十好几的人了还是鼻涕邋遢的,当然也没成个家,在姥姥家不大受待见,却和我拉得来。
我和二舅一边一个,共同推水车。一开始,我把水车推得飞快,弄得二舅一瘸一踮地跟不上趟,边擦鼻涕边骂我。直到铁链子哗啷一声滑落下来,二舅才停住脚,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上链子。上链子这活只能我干,二舅使不上劲,我吃力地提起铁链,听着皮钱在长长的铁筒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一点一点挂在齿轮上。挂好铁链,我的力气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懒洋洋地推着木杠。这时,二舅吸着鼻涕,挤眉弄眼地望着我说:再跑哎,再能哎,怎么不撒欢了啊?我把头别向一边,不理他。二舅也不和我一般见识,用力推着越来越沉的水车。
推到井底快见干的时候,二舅就说:“仇小,歇会吧,等井水长长再推。”
我飞快地松开木杠,一腚坐在垄沟边。二舅猝不及防,被倒转的水车带得后退踉跄几步,无奈地咧着嘴,不知嘟囔着什么。
我坐在井边的垄沟上,看着井水顺着垄沟缓缓流淌。靠近水车簸箕的地方,被水冲出了一个小坑,泛出了细碎的沙石。清凉的井水仿佛听话的孩子,在垄沟里乖乖流着,碰到拐弯处急速地拥挤一下,又轻轻荡回来向前走,顺进菜畦里,慢慢洇湿、蠕动。地里的白菜们见到水,如同遇见亲人,张开每一条根须吮吸着,像婴儿含着乳头,不吸饱不让水流向别处。我似乎听到它们细微到无声的吮吸声,望见清澈的井水在每一条叶脉里汩汩流动。
太阳很好,暖暖地照着大地。吸饱了井水的白菜们叶子挺拔,绿莹莹的,如同一匹匹精神抖擞的小马驹。那些没有浇上水的白菜则有些没精打采,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仿佛在恳求:别老歇着了,推吧,我们渴啊!白菜们的这些神情语言,少年的我,能听得懂。
我站起身来,望了望井口,水已经长到井壁半截了。二舅说,别紧歇着了,越歇越不愿干活,推吧!
又继续推水车。此时的我有些心不在焉,一边推,一边望着阳光下碧绿的白菜,远处大片的玉米地。水车一圈圈地转着,橙褐色的皮钱带着井水缓缓地从井底升上来,注入车簸箕,清凉凉地淌着,稍微有一些腥气。这时最烦的,就是水车掉链子和菜畦“打漏子”。“打漏子”还好,一个人推着,一个人飞快地拿着铁锨去堵漏子。掉链子最可恶了,越到后来越掉,提链子时,水链攥在手里冰扎凉,勒得手生疼,不小心还会咬伤手。一次次地上链子,让我有些气急败坏了。再推时,半个身子伏在杠子上,像“尥蹶子”的驴,半干活半罢工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