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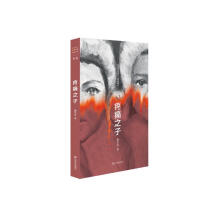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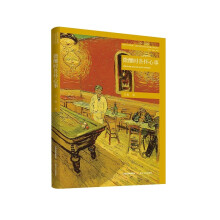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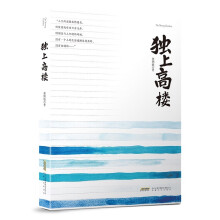


本书卖点
1.作家实力值得期待——焦冲是一位年轻而绽露锋芒的80后作家。作家石一枫认为:“他总能把生活写得像生活本身一样鲜活,焦冲的小说有着强烈的生活质感。”
2.阅读的趣味性——焦冲的小说善于描摹人物的动作、神情,并在其中赋予了意味深长的人物关系,叙述中未曾说破的潜台词呼之欲出,具有极强阅读趣味性
3.丰富的内容——本书精选了焦冲近几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内容丰富,意蕴饱满,从父女家庭关系到热恋的青旅关系等,展现了成长的隐秘、另类的“朗读者”故事、自我救赎等,丰富了作品集的意蕴,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阅读选择。
编辑推荐
力派作家焦冲中短篇代表作结集——人与人的狭路相逢在焦冲笔下凡俗而真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犀利的描摹下,又有体恤与包容,让他的小说极具可读性,并且后劲十足。
《时间的秘密》是作家焦冲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些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8篇,包括《天灯》《独立日》等篇。其作品贴近现实,着眼于小人物的日常和悲欢,以鲜活的物质细节与绵密的生活质感取胜,因而血肉丰满、形象生动。如《吴焦氏》以孙女的目光回顾了奶奶的老年生活,勾勒出一位淳朴、善良、隐忍、坚强但重男轻女的乡村女性形象……这些作品多数为女性视角,贴近当下的现实生活,侧重展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成长,焦冲既写一个断片,也大跨度地写人的一生,为文学园地贡献了丰富的女性形象。
从北京四惠长途汽车站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便能抵达老家县城。饶是如此方便,我也没有经常回家,只在法定长假和小长假和我哥一起回,有时他会带上女朋友。离婚后半年多,实在无法再瞒下去,我先告诉了父母,没过多久,亲戚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催我再婚或是张罗对象让我回老家相亲,这让我感到纳闷。后来有一次和妈妈聊天,才获知我大姑、二姑等人都曾要给我介绍对象,却被我奶奶拦下了,她说小玲现在过得挺好,她要想找对象早找了,在外面见的男人肯定不少,还用得着你们?再说,你们介绍的那些男人肯定配不上她,让她自己找吧。难怪奶奶从来不问我离婚和再婚的事,就像并不知道我恢复了单身似的。每次回家她只问我工作累不累,过得开心不开心,且非那种笼统的询问,是真正出于关心,比如一些不懂的名词和事物,她会让我给她解释清楚,并竭尽所能去理解和想象外面的世界,次数多了,她好像多少弄清楚了我的工作是怎么回事,总结道,看来还是跟人打交道,难怪嘴皮子比以前厉害多了,你觉得舒心就行,别管别人怎么说。
说这话的时节,奶奶已开始在我家和二妈家轮住,三个月换一次。她的身体逐渐出现各种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虽然吃着药,也经常头晕、手脚麻木,走路越来越慢,颤颤巍巍,似乎下一秒就会摔倒,后来不得不拄上拐杖。晚辈们都担心她一个人在老宅里住会出事,便劝她在两个儿子家轮住,可她一开始并不同意,只说到了冬天再议。那个夏天,我堂哥终于找到对象,且议定等到秋后天凉了办婚礼,那女孩也在县城工作,她希望堂哥在县城买套两居室。堂哥没有固定工作,开出租不过是私下里拉活儿,也就是所谓的黑出租,因此无法从银行贷到房款,只能四处借钱。二伯和二妈从各自的亲戚那里东挪西凑了一部分,加上积蓄,刚刚够。买了房就要装修,再加上置办家电等也需要几万块,再想从亲戚们那“搜刮”显然不太可能—凭什么让人家为了你儿子结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时奶奶发了话,她同意轮住,好将老宅卖掉,以便解堂哥的燃眉之急。老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宅基地和院子,加之位置不错,因此很快被村里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妻买下了,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已结婚,急需一套房子安身养老。堂哥靠着这两万多块钱装修了新房,娶上了媳妇。后来我哥跟我说,奶奶曾让他不要计较,说他比堂哥赚钱多,且不着急结婚,让他别怨她。
奶奶不想轮住主要是不想看别人的脸色,儿子不管怎么样都是自己的,怎么着都可以,主要是儿媳妇,更准确地说是担心二妈不待见她,毕竟这对婆媳失和多年,早年间甚至大吵大闹撕破了脸,后来虽然有所缓和,却始终貌合神离。但事已至此,她只得搬了,先搬去了我家,三个月后又搬去了二妈家,就这样轮换着住了两年多,最终在二妈家去世。不管她住在谁家,都是一个人住着大房间,可她的气场似乎撑不起如此宽阔的空间,她一动不动地坐在炕沿,仿佛舞台角落里的道具,她仅有的贴身之物也放在旁边,比如被褥衣服等,她和它们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小旮旯,她不想或是没有能力去占据更多的空间,只在需要出去的时候才走动走动,更多的时候她只是看着房子的主人们(舞台的主演们)在这里行动自如,说说笑笑,而她根本插不上话,这时她又从道具变成了观众。
晚辈们对她都不错,把她照顾得挺好:她喜欢吃软的就给她蒸馒头,做面条,用高压锅炖肉炖鱼,连鱼刺都是软烂的,在她生日时,我哥还给她买生日蛋糕;她怕冷,就让她睡在热炕头,挨着暖气片,不烧炕时就给她插上电褥子;她爱看戏曲节目,她房间的电视机便基本定格在央视戏曲频道。我回家时若是赶上她刚好住在二妈家,自然会去看她,她会跟我说最近有谁来看过她,给她买了什么,若是二妈不在旁边,她会跟我说二妈一些含沙射影的言行,她怀疑那是针对她的。我当然不能附和她,即便真是如此,我也让她装糊涂,她说她知道,她什么都没说,只是跟我唠叨唠叨。其实,就算是我妈,她对奶奶好也只是尽一份孝道和义务,或是单纯觉得奶奶是长辈,理应尊重,婆媳关系再好,也始终存有天然的隔阂,不可能如同真正的母女那般亲密无间。
奶奶后来便不再抱怨,反而说起了二妈的好,那时她已行动不便,吃喝拉撒虽然还能勉强自理,但其他事基本干不了了,甚至连梳头都因为胳膊抬不起来而做不来。二妈把她伺候得很好,不仅为她梳头、洗头,天气热了以后还给她洗澡,使得奶奶的身上不至于有汗味。奶奶生命中的最后两个多月是在炕上度过的,我妈和二妈轮流伺候她,她虽然瘫痪,脑子却清醒,话也说得利索,只是气力比以前小了许多。我妈跟我说,每当她和二妈为奶奶翻身、擦身时,奶奶的眼睛里都会充满感激,还有一丝无奈。她对我妈说,不会麻烦你们太久了,三媳妇啊。我妈自然也知道奶奶的大限将至,但还是宽慰她,让她不要多想。在奶奶去世之前一个多月时我回了一次家,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清醒的她,后来再次看见她时,她已被穿戴好停在了门板上,只剩一口气迟迟未咽。那次她还能吃东西,我带了她爱吃的糕点,喂她,她只吃了一口就不再吃了,我让她多吃点,她说,吃得多拉得多,又得麻烦。我说,没事儿。她闭起嘴巴,盯着我,像是有许多话要讲,又像什么都不说也没有关系。她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她正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死亡的最终降临,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黑暗和虚无。她的人生已经谢幕,只剩最后一个仪式,不仅她,就连我们这些至亲其实也在暗暗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因为现在的状况对于她和我们而言都是一种折磨。
半个多小时后,大巴驶出北京城区,高楼大厦和各种建筑逐渐消失,高速公路两边皆为田野,秋收早已完成,空旷的野地在阳光的笼罩下显得稀薄、轻盈,泛着忧郁的光辉,周遭一派非同寻常的静谧。接到我哥的电话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几天前和家里通话时得知奶奶已米水不进,即将进入弥留状态。我和我哥坐在一起,他闭着眼睛,也许睡着了,不知是否梦见了奶奶。到站后,堂哥已在那里等着,于是三人直奔老家。亲人们都在二妈家,奶奶整个人被套在寿衣中,显得干瘪、无助,假牙已被摘去,嘴角塌陷,嘴唇几乎消失不见,两只眼睛尚睁着,暗淡无光,犹如剥了皮后放置许久的葡萄粒,无法逆转的结局笼罩着她的脸。我们几个在她耳边大声喊了两句,她的嘴唇动了动。我们到家时大概是下午四点,直到晚上九点奶奶才停止呼吸。她在这世上活了八十六年,按照习俗,天一岁,地一岁,因此命纸(类似讣告)上写的是八十八岁,爷爷走了之后,她又活了七年。
次日夜里守灵,我和我哥、堂哥、堂姐四个被安排在上半夜。吃过晚饭,我们便来到灵棚里坐着,不时烧纸添油。不一会儿,堂姐才过两周岁的儿子被姐夫抱了过来,这是老二,老大是女儿,六岁了,在家和她奶奶待着,这个小的离不开妈,就把他带来了。姐夫将孩子放到堂姐腿上说,你哄吧,一个劲儿闹,非要找你。堂姐拍了儿子的屁股两下,吓唬道,你想干啥?你再闹,大马猴抓走你。孩子没有被吓到,但噤了声,扎进他妈怀里撒娇。我哥对我说,小娟刚才那表情,那口吻,就连那句话都跟小时候奶奶吓唬你时差不多。堂姐笑道,那时候咱们赖着不走,奶奶还爱吓唬咱们,说日头没红眼过,让咱们家去。我哥说,上次公司组织出去玩,晚上分组生火烤羊腿,我很快就把火点着生旺了,其他组一直冒烟,有个同事问我怎么弄,我就叫他支起柴,留有空隙,随口说,火心要空人心要公,话一出口我才想起那还是小时候我帮奶奶烧火,她告诉我的。堂姐道,到现在我熬粥都要放碱面,干活戴套袖,都是受奶奶的影响。堂哥道,还说呢,有一次我拉活,见一个老太太摔倒了,本不想扶的,怕她讹上我,后来还是扶了,就因为她长得和奶奶有几分像。我哥说,奶奶虽然死了,可她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堂姐道,呸,这话说的,就好像奶奶的鬼魂要附身了。
我们几个便笑,我明白我哥的意思,他是说奶奶的一些习惯早已注入了我们的日常,某些不经意的瞬间,她就会被记起。对我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比如我的那次婚姻,我觉得换一个城里长大的女孩也许就能和我的前夫过到一块,能够忍受甚至推崇他妈的做派,因为她所崇尚的“生活要有仪式感,要为自己而活”正是目前大多数人追求和信奉的,他们一方面要尽量满足私欲,一方面要活得体面、光鲜,这是给外人看的;他们既要金钱和物质,又要虚荣和面子。可我奶奶那一代人不是这样的,那个时代的人不会刻意追求财富,并不以金钱为标准来衡量生活,在他们看来,人应该将贫穷置之度外,靠自身的天赋和努力而活着,对那些不劳而获、以享乐为人生目标的人表示深深的鄙视和淡淡的羡慕;要自尊自爱,不要靠恭维和谄媚他人而生存,他们为此感到羞耻。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就是天气、食物、情感和生命,一代又一代……当生命走到尽头,会有一种收获和丰饶感。
经过一系列程序,终于到了出殡的吉时。墓地在村北的二道渠旁边,我爷爷也埋在那里。
队伍犹如一条白色巨蟒,缓缓前进。墓穴上午已由挖掘机挖好,到达后,吊车提起棺材,徐徐落进方方正正的坑中。众人行礼,奶奶的三个儿子各填了一铁锹土后,便由他人代劳。一座新坟很快落成,花圈盖住坟头。人们脱掉孝服,按照风俗,翻过来,叠好。其他人纷纷回去,只剩我们这些至亲还站在那儿。这时,我爸指着墓碑道,名字怎么刻错了,二哥,你找的哪个人?我们上前查看,只见墓碑右边有一行新刻上去的铭文,本来应该是“焦吴氏”结果刻成了“吴焦氏”。我二伯说,我找的就是上次给咱爸刻字的那人啊,我都让小川(我堂哥)把要刻的字发到他手机上了,怎么还弄错了?我爸说,他准是让他儿子来的,赶紧打电话问问。二伯让堂哥打电话,这时我哥阻止道,算了。我爸道,不能算。我哥道,这要改的话,肯定把墓碑弄得很乱,我奶奶本来就姓吴,跟着我爷姓了这么多年焦,临了就让她回归本姓也没什么。我爸道,可她到底是老焦家的人,让人看见像什么话。我二姑道,谁吃饱了撑的来瞅这个?我哥道,没有我奶,就没有咱们,是她养活了一大家子人,我看咱们都跟着姓吴也不过分。我爸道,胡说八道。我大伯道,算了,反正都是那仨字,顺序差了而已。大伯发了话,我爸不再言语,算是默认。一阵秋风吹来,黄叶纷纷落下,当我们转身,眼前是一片露头不久的秋麦,半黄半绿,柔嫩中透着坚韧,在夕照中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