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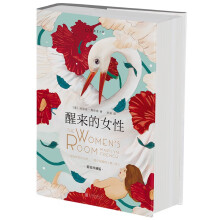





★全球累计销量20,000,000册,出版22种语言版本,一部真正意义上影响一个时代、改变世界的小说,改编电影获戛纳3项提名,英国BBC改编为广播剧,著名作家安妮·泰勒作长评!
★中文版累计近10万读者,豆瓣8.9高分好评,被读者誉为“改变我一生”的女性成长神作!
★杨澜、崔璀、戴潍娜诚挚推荐,国内外媒体一致好评,推荐给每个女性,带你“突破逆境,自由成长”。
★全新升级精装珍藏版,装帧工艺、内文用纸全面升级,阅读体验更好,更适合长久收藏,一部可以留给女儿读的经典女性文学。
我们来认识一下米拉。
她是一位喜爱读书的小镇女孩,从小就是个独立而聪明的孩子。她十四岁读尼采和潘恩,开学第一天就学完了全部课本,学校只得让她跳级。可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女性最常见的职业是“打字员”,人生的主题则是“家庭”。母亲对她最大的期望就是“嫁个好人家”。在 一个封闭的小地方,她的聪明和独立却使她成为异类。久而久之,她屈服了。她像其他女孩一样草草结婚,穿紧身褡,学做饭,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生下两个孩子,努力让自己做一位“贤妻良母”。丈夫有体面的工作,她也住上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大房子。她举止优雅,总是面带微笑。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在生活的平静表象之下,她正在默不作声地崩溃……
【瓦尔是不会屈服的】
瓦尔看着她,米拉从瓦尔脸上看到了令瓦尔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一刻,她的表情里包含了一切:理解、同情、对痛苦的了解、意识到那些我们年轻时视为幸福的事物的难得,以及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快乐—幸存下来的人才明白小小的快乐是多么珍贵。
米拉摊开手。“没有解决办法。”她耸了耸肩。
“问题是必须得做出选择。”
米拉疑惑地皱起眉。
“你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在一起,要么分开。要么结婚,要么不结。要么生孩子,要么不生。”
米拉心里一沉。“我就是无法选择,”她问瓦尔,“如果我们在一起,但不要孩子,你觉得他将来会原谅我吗?”
“如果你们在一起,生一个孩子,你将来会原谅他吗?”
米拉笑了。她们一同哈哈大笑起来。“去他妈的将来!”瓦尔喊道。米拉握住她的手,她们坐在那儿,望着彼此不再年轻的脸庞,在岁月的洗礼下,添了些许皱纹,在生活的历练中,多了几分豁达。在这个满是年轻人的地方,她们这些幸存者因为一个只有她们能懂的玩笑而开心着。米拉想起几个月前,在一场化装舞会上,瓦尔出场的那一刻。她穿一身性感的黑色衫裤套装,上面缀饰着羽毛,她的头发闪着银色的光泽,眼睛上涂了绚烂的蓝色眼影,手拿一根长长的黑色烟斗。她走进来,摆了一个浮夸的造型,大家都停下来,看着她笑了。她也笑了。她站在那儿,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此刻,体形和年龄又算得了什么呢?她摆出一副诱惑的姿态,得意地笑着,她是在笑自己,笑自己的幻觉和欲望,笑她这种妖艳的模样—但若没有这些,这个世界岂不索然无味?我们中有一些人懂她。我们都将是被嘲笑的对象。人们都看得出我们的脖子变干瘪了,下巴变松弛了,走路姿态不再轻快,发际线也后退了。年轻人也一样,尽管他们还不承认自己会变老,不承认他们想象的美好生活不会实现,但他们已经知道,有些东西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比如身材不够修长,膝盖上的皮肤不够光滑。就连我们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人都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比如眉形不好、鼻孔太大。所有我们这些漂亮的、上了年纪的人,都在迈向死亡之际打扮着自己,用生命来装扮自己,试图摆脱死亡的阴影。她让我们看到了这点。她进来的时候神采飞扬、笑靥如花、艳光四射。啊,瓦尔是不会屈服的!
【米拉得知怀孕之后】
五月,她的月经没来。她很紧张,因为她平时周期很规律,还因为在她第一次尝试用子宫帽失败之后,诺姆坚持用以前的老办法。他不喜欢在欲火焚身的时候,还要等她在浴室里鼓捣十分钟。她怀疑他是想自己掌控局面。她担心避孕套有风险,可有时避孕套破损严重时,诺姆就什么都不用,只是在高潮前抽出来。她觉得那样很冒险,可他向她保证说不要紧。
多年之后她才觉得,在这方面,她对他言听计从,这很奇怪,可能因为她讨厌戴子宫帽。到后来,她干脆完全不喜欢做爱了,因为他总是让她“乘性而来,败性而归”;如今,手淫的时候,她也能到高潮。回溯从前,她才意识到,她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他,就像她当年必须将人生托付给父母一样。她只是将自己的童年转移了过来。尽管诺姆比她大七岁,还在战时参过军,也有过几次冒险经历,但他这个年纪,还不足以去当一个孩子的父亲。或许,在潜意识中某个隐秘的角落,她是想要孩子的。也许,她所等待的,她所谓的成熟,就包括生一个孩子,将他抚养长大。也许吧。
可在当时,这完全是一场灾难。他们要怎么生活?她面色苍白、眉头紧锁地去找妇科医生。那天晚上她带着这个消息回家时,诺姆正在准备一场重要的考试。一天的工作、舟车劳顿,在医生办公室漫长的等候,已经令她疲惫不堪。从汽车站走过两个街区回来的路上,她想象着,也许诺姆已经准备好晚餐了。可是进门之后,他仍在学习,在吃着奶酪和饼干。尽管他知道她去了哪里,也知道她干什么去了,他还是因为她回家晚了而生气。她走进房间,看着屋子里的他,他也无言地与她对视。三个星期以来,他们很少讨论什么别的事。无话可说。
突然,他把手里的书从房间那一头丢过来。
“你毁了我的人生,你知道吗?”
她在一把摇椅边上坐下来:“我,毁了你的人生?”
“现在,我不得不退学了,要不然我们怎么生活?”他紧张地点燃一支烟,“你回来告诉我这些,我还怎么准备考试?如果我考不及格,就会被退学。你知道吗?”
她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派超然。她想指出他最后一句话的逻辑错误。她想指出,他这番抨击多么不公平。可他觉得这么说没错,觉得他有合法的权利像对待调皮的孩子般对待她,这让她不知所措。那股力量让她无法抵抗,因为他的合法权利是整个外界所支持的。这她是知道的。她试图说服他,于是探身过去说:
“我在床上逼你了吗?你说你的方法是安全的。是你说的,学医的先生!”
“是我说的!”
“对啊。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怀孕了。”
“就是安全的,我告诉你。”
她看着他。他脸庞发青,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似在狠狠地谴责。
她声音颤抖地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这孩子的父亲?你的意思是这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
他愤恨地瞪着她:“我怎么知道?你说除了我你没和别人上过床,可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我听过不少关于你和兰尼的事。大家都在谈论你。那时候你自由惯了,难道现在就会改了?”
她又跌坐回椅子上。她和诺姆说起过她对性的恐惧、对男人的恐惧,以及对她所不了解的那部分世界的胆怯。当时他温柔地听着,充满爱意地抚着她的脸,紧紧抱着她。她曾以为他能理解,因为尽管他在军队时有过一些冒险经历,但他和她有一些共同之处—害羞、恐惧和胆怯。她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但她所做的一切只是引敌入室,让他进入她的身体。它就在那里生长。他和他们的思考方式一样;他,和他们一样,认为他对她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他是男的,她是女的;他也像他们一样,相信他们用于形容女人的,称之为贞操和纯洁,或是婊子和荡妇的东西。但他很绅士,值得尊重,他已经是男性中出类拔萃的人之一。如果他也和他们一样,那就没有希望了,就一点儿都不值得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了。她又向后靠了一点儿,然后闭上眼睛,轻轻摇晃着椅子。她的意识进入了一片安静而黑暗的领域。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此刻她不必想这些。她所要做的,只是找到一条出路,而她已经找到了。她终究会死,这一切终会结束,都会过去的。她再也不会有现在这种感觉,多少年来,她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只是现在更为强烈,仿佛火箭在她的全身炸开。她的胃,她的头,比心更痛。身体里迸出火与泪,那泪水如愤怒之火一般灼热、刺痛。没什么可说的。他就是不明白。这种伤痛太深了,好像她是孤身一人,好像她是唯一有此感受的人。一定是她错了,尽管她丝毫不觉得。没关系,什么都无所谓了。
过了很久,诺姆走近她。他跪在椅子旁,“亲爱的,”他温柔地唤着,“亲爱的?”
她仍然摇着椅子。
他把手放在她肩头。她颤抖了一下,躲开了。
“走开,”她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说,“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他拉过一个脚凳,坐在她旁边,抱住她的腿,头靠在她膝盖上:“亲爱的,对不起。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完成学业。或许家里人可以帮帮我们。”
她知道他说得没错。她知道他只是害怕,和她一样害怕。但他觉得他有权利责怪她。她得知消息的时候也很心烦,但她并没有责怪他。她只把它看作两人的共患难。她把手放在他头上。那不是他的错,只是诸事不顺。没关系,她终会死去,会远离这一切。她碰到他的时候,他哭了。他的确和她一样害怕,或许比她更害怕。他把她的腿抱得更紧了,他啜泣着,道着歉。他不是有意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幼稚得可笑,他很抱歉。他紧紧地抱着她,哭泣着,她缓缓抚摸他的头。他振作起来,看着她,抚摸她的脸颊,他讲笑话逗她,擦去她脸上的泪水,把头靠在她胸口。这时,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从她眼眶中落下来,惊吓之余,他一把拥她入怀,不住地说:“对不起,亲爱的,天哪!对不起。”她想,他以为她是因为忠诚遭到怀疑而哭吧,他不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永远不会明白。终于,当她不再泪如泉涌时,他对她笑了笑,问她饿不饿。她明白了,起身去做晚饭。一月,孩子出生了。过了一年半,她又生了一个。诺姆的父母借钱给他们,还写了借据:借八千美元,于工作后还。这之后,她又买了一个子宫帽。可是从那时起,她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