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我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在这个年纪背井离乡,选择去大城市打拼的年轻法国人不在少数。对那时的我来说,这无疑是最棒的冒险:我来到了那个原本只出现在小说里的地方,行走在福楼拜和雨果笔下的人物走过的路上,内心犹如巴尔扎克小说里的少年般意气满满。
我很喜欢那些去圣热纳维耶夫高地漫步的岁月。
但我不得不说,我虽日复一日地刻苦学习,同样的课程,我在亚眠时可以在班里名列前茅,在这里我就暗淡多了。我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的佼佼者,他们中有些是数学天才,而我只能通过加倍努力去弥补与他们之间的差距。同时我必须承认,在初到巴黎的那几年里,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享受生活和爱情上面,无心加入同学间的竞争。
我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和我的爱人一起过梦想中的生活,并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
巴黎高师的大门最终未能向我敞开,在几次尝试之后,出于对哲学的热爱,我进了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大学。之后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入读了巴黎政治学院。
那些年是美好的,我能够自主选择实践机会,探索未知,并有机会结识不同的人。我很喜欢曾停留过的这些校园,正如我热爱那些曾给予我谆谆教诲的人。这期间,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哲学家保罗·利科,他当时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协助他整理文件的助手,而这次相遇得益于我热心的历史老师和保罗·利科的传记作者。
我永远忘不了我和利科在沙特奈马拉布里市的白墙公馆一起度过的那几个小时。我听他侃侃而谈,并未表现出面对名人的胆怯。我必须承认,这份坦然源自于我对他的一无所知。我从没读过他的着作,自然也就意识不到他有多了不起。夜幕降临,我们都没有去开灯,而是在一种逐渐建立起的默契中继续我们的谈话。
从那晚起,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我的主要工作是研读和评论他的文章,以及协助他阅读参考资料。我就这样在他身边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收获良多。其实,我的资质本不足以胜任这个工作,是他的信任促使我不断提升自己。在他的影响下,我每日不间断地阅读和学习。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内容只不过是研读经典着作,而这一定义源自于他谦虚地把自己比作一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那几年里,我还有幸接触到了奥利维尔·蒙甘、弗朗索瓦·多斯、凯瑟琳·戈尔登斯坦和特雷兹·杜芙洛,他们待我亦师亦友,并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利科的指引下,我对上世纪的历史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也学会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他教我怀着敬畏之心去看待某些问题和某些历史悲剧,以及通过文章解读生活。保罗·利科笔耕不辍,每日在理论和现实中往返,虽伏案工作,却志在照亮世界变迁之途,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是他告诫我,千万不要被情感摆布,也不要道听途说,更不要将自己封闭在一个脱离现实的理论空谈之中。在这种看似冲突不断、实则激发灵感的失衡状态下,才能迸发出有意义的思考,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变革。
有其师必有其徒,这段以利科作为精神导师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我认识的利科性格严谨,擅长观察现实生活,同时对他人充满信任。我明白,遇到他是我这一生莫大的运气。
在那几年里,我愈发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想做的并不局限于学习、阅读或理解,而是要行动起来,切切实实地做出改变。于是我决定换专业,转学法律和经济,并最终选择了社会决策。于是,我同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一起,着手准备国立行政学院的入学考试,这些朋友至今仍在我身边,不断给予支持。
进入这座学校不久,我就立即被派往政府部门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学生在这里完成职场初体验,而年轻公务员则是在实践中完成了自我培训。
我很喜欢这一年的实习和培训,从未主张取消国立行政学院。如今制度中的问题在于,高级公务员的职位过于稳定,而与此同时其他人都生活在不安之中。
我的为国效力之路始于法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六个月间,我有幸在一位出色的大使——让-马克·西蒙——身边工作。之后,我被派往瓦兹省的省政府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国家机构的另一面——地方政府、地方代表和社会政策。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度过了这段时间,并与很多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米歇尔·罗卡尔。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不久前刚刚去世的亨利·埃尔芒,他后来对我的期许很高。从一开始,他就待我亦父亦友,我们也有着相同的政治取向和观点。这位杰出的人物曾经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是几十年来法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正是借由他的关系,我结识了米歇尔·罗卡尔。
他们两人在2016年相继离世。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来往,或谈论人生,或谈论政治,度过了很多亲密的时光。米歇尔·罗卡尔和我除了年龄、经验和曾担任的职务有所不同外,还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与我相比,米歇尔·罗卡尔拥有更深厚的党派文化背景,以及穷尽毕生力量改革其所属政党的意志。他的严谨、决心和友谊都深深影响了我。无论是在历史根源深远的重大国际问题上,还是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气候事业上,他都为我树立了忧患世界的榜样。
在国立行政学院学习的这段经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想。我当时并不真正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也没有方向。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学习时获得的名次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让我可以自由选择毕业去向。开始接触财务检查工作时,我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虽然也是政府工作,但对我来说多了种未知的吸引力。在那四年半的时间里,我学会了以严谨的态度进行核查工作,在基层的走访也让我收获颇丰。我在对公共事业有了更深入认识的同时,也学会了团队合作。
我有机会走遍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曾往返于特鲁瓦、图卢兹、南锡、马罗尼河畔圣洛朗和雷恩市之间,并度过了几周的时间。这段时间拉近了我和同事之间的距离,我们在交谈中学会了层层剖析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各种政府机制。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被任命为“提高法国增长委员会”副报告人。该委员会当时的委员长是雅克·阿塔利。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与委员会的40名成员一起工作了六个月的时间,与其中不少人成为朋友。通过委员会这个平台,我结识了一些非凡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分别是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并有幸求教于他们,接触到了不同领域的问题,且心系至今。
几年的政府工作之后,我决定离开人们口中所说的“服务”机构,进入私有企业。
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了解私有企业的运行规则,观察国际局势对私有企业的影响,然后再回到政府部门。在这期间,我一直保持着对政治的关注。在《精神》杂志工作期间,我先是与让-皮埃尔·舍韦内芒的朋友短暂来往,然后加入了社会党,后因观念不合而随即退出。其间,我有机会察访了加来走廊加来海峡省地区,并逐渐积累了一些社会关系。
我就这样离开了政府部门,进入罗斯柴尔德投资银行工作。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从业界内最年轻和最有经验的人那里学到了这个行业的工作方式和技巧。然后,在经验老到的银行家带领下,我体会到这一行业的非凡之处——它要求你搞清楚整个产业块及产业现状,说服一个企业负责人做出正确的企业战略决策,继而陪伴他带领整个技术团队执行这个决策。在此期间,我了解了商业的奥秘,见证了它巨大的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个行业被某些人吹捧到无法企及的高度,而另一些人则仅仅在其中看到了金钱的肮脏和对人的剥削压榨,我既不认同前者的得意扬扬,也不认同后者的负面刻薄。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既幼稚又不合时宜。
我同一些出类拔萃的同事相处了不少时间。大卫·德·罗斯柴尔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将原本很难一起共事的精英人物聚集在一起来为他工作。因为这个行业的关键不是摆弄金钱,也不是拿钱去借贷或投机,而是提供咨询。在这里,真正有价值的是人。
我从未后悔在银行工作的这四年时间。但我的这段经历却常受人诟病,因为不了解这个圈子的人会把这里想象得十分不堪。无论如何,我在这里真正了解到了一个行业的运作,而我认为所有的政治领袖也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熟悉的领域。我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好几个领域和不少国家,受益匪浅。与一些决策者的来往也使我增长了见识。我也有可观的收入,但没有多到足以让我从此悠闲度日的地步。
2012年,我听从自己的内心,离开了这家银行,重新回到政府机构。在离职前两年,我就已经决定应弗朗索瓦·奥朗德的邀请,参与到左翼政党的经济改革议题和方案的准备工作中。奥朗德当选总统后,我接受他的邀请前往爱丽舍宫,并以总统府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在他身边工作了两年,主要负责欧元区和经济方面的议题。
那几年我在为国效力,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地进言,至于能否被采纳就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了。我希望自己提出的建议中,起码有一些是中肯的。当然我肯定也提出过错误的建议,对此我也不会回避——我在任职期间并非面面俱到。两年后,我提出辞职,并于2014年7月离开爱丽舍宫。
我没有像多数人一样试图在政界或商界谋求个好职位。我更倾向于自己单干——创业或教书都可以,当时也丝毫没有重返政坛的打算。更何况,当时有一个狂热的“道德规范”委员会,他们几乎禁止我与总统再见面。这种过激且不现实的做法令人捧腹,但我全然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之后不久,总统又召我回去任职经济、工业和数字经济部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公众所熟知的了。我尝试在政府内部做些改变,并得到了支持。有一次在国会,我花了几百个小时的时间说服人们通过一项我认为有效的法案——它有助于解开周日工作禁令,放宽运输条件,鼓励市场竞争,重新刺激购买力,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我勾画出一幅以创新和投资为基础的工业计划蓝图。在持续多年的经济衰退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积极有力地保护工业,重振一些大型企业,例如标致雪铁龙集团和大西洋造船厂等。我幻想引导一场“头脑清醒,敢想敢作”的运动,为工业振新和经济独立付出努力,并且收获成效。比方说,作为政府,我们要知难而进,对类似核能和石油配套那样的行业进行重组,或者对法国钢铁业予以保护。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天真地认为政府干预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绝境。当然,我必须承认,在这条道路上我也曾经历失败。我希望通过支持投资、号召企业家务实和倡导“科技法国”这三种途径,为明日工业做准备。说到明日工业,在法国已经有一股新兴的力量正在萌生了。
接下来就是那段充斥着僵持和意见分歧的日子。
2015年秋天的恐怖主义事件之后,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国家没有抓住这个全新的经济机遇,通过改革建立强大欧洲的决心日渐崩塌;人们围绕国籍话题进行毫无意义的辩论,而这场辩论除了分裂国家,并没有对恐怖袭击给出任何对策......在我看来,这些政治决策都有失妥当,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误。就在危机和绝望助长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的同时,我们的邻国却已经找到降低失业率的可行性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刻不容缓。
针对这一事务,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担任经济部长期间,我的改革则因接二连三的形势判断失误、同事的无法胜任以及一些人的私下中伤而受阻。于是,我决定提出一项新的政治主张,并于2016年4月6日在我的家乡亚眠市首次发动“前进”运动,它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对抗”什么,而是“支持”什么。马尔罗说得好:“对抗并不存在。”我就是一个为“支持”而存在的人。我支持不同的政治派系能够超越对立,共同存在;我支持在重建国家的征途上走得更远;我支持将辉煌的历史同进步的动力重新连接,为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我支持让法国人民参与变革;我支持重用新的面孔、新的人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想法越来越清晰——我必须离开政府。唯有这样才不会违背我对形势的解读、我的追随者的意愿,以及我对国家的期待。
有人说我忘恩负义,并且闹得沸沸扬扬。我要就这件事反驳一次,只此一次。我认为这一说法恰恰反映了当代政治的道德危机。有的人说,既然我经济部长的职位拜总统所赐,那么我就应该像机器一样服从他,放弃个人观点和事业,与他共进退。当他们说这些的时候,真正想表达什么呢?是想说国家利益应该让位于私人恩惠吗?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些中伤我的人竟然无知地承认,对他们来说,政治也有潜规则:只要乖乖服从,就能分到一杯羹。在我看来,如果说今天的法国民众已经放弃政治,或者正在走向极端,就是出于对这类官僚之风的本能厌恶。
至于后来共和国总统说我欠他个人情,我权当这是无心之语。因为我深知他十分在意维护政府公职的尊严以及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价值,绝不会(哪怕是一瞬间也不可能)认同这种施恩图报的观念。正因如此,我虽不得不痛心离开,却仍对他满怀敬意。不管是最初在总统府内为他出谋划策,还是后来作为政府内阁的成员为国家献计献策,是他给了我为国效力的机会。
我忠于的对象仅限于国家,而绝非某个政党、某个职务或某个人。我之所以接受这些公职,是因为它们为我提供了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机会。从接受政府职务的第一天起,我便一直保持这一观点,从未改变。后来,我的变革之路上出现了阻碍,这些阻碍包括冥顽不灵的思想、老人当道的政府、匮乏的想象力、笼罩社会的精神麻木等,一切迹象似乎都在向我表明时局不再,我斟酌再三,随后提出了辞职。在我的观念中,政府的举措既不是用来美化个人政治生涯的,也不应成为论资排辈的资本,而是以服务为出发点,发动所有人出谋划策。其他的所有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批评和诋毁更不能动摇我,何况那些中伤者并非忠于国家,而是忠于一个可以确保自身利益和薪俸的官僚体系。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过去这些年里,布丽吉特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们于2007年结婚,这段最初要遮遮掩掩、不为人接受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备受阻挠的关系,在与命运和伦理的较量中,我应该算得上意志顽强。但我必须说,是布丽吉特给了我真正的勇气,以及包容一切、平和而又坚定的信念。她当时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而我只是个学生。她和我在一起不图财、不图名分,也不期望我带给她舒适安逸的生活。恰恰相反,为了和我在一起,她放弃了一切。当然,孩子始终是她的牵挂,她没有强迫他们认同,而是慢慢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关系虽然很难接受,却已成定局。
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正是布丽吉特那份决定拉近我和她家人关系的心意,造就了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她的孩子渐渐理解并接受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建立起了一个专属于我们的家庭(至少我这么认为),一个显然不能以常规眼光来看待的家庭。但也正因为这种非比寻常的关系,我们之间的纽带更加坚不可摧。
我一直很敬佩她身上的那种坚定和勇气。
首先,作为一名法语和拉丁语教师,她始终兢兢业业,对这份从30岁起就开始从事的工作充满了热爱。我曾亲眼见证她不遗余力地帮助有困难的青少年,她的敏感使她能捕捉到这类学生细微的精神裂痕。因为在她充满活力的坚定外表之下,有一方敏感的净土,一方只有脆弱的灵魂才能进入并找到知音的净土。
作为母亲,她也表现出了同样充满关爱的坚定。她在生活和学习上无条件支持每个孩子,是他们的坚实后盾,同时又对他们有着清晰明确的要求。塞巴斯蒂安、劳伦斯和蒂芬娜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或者去见她,征求她的意见。布丽吉特就是他们人生中的指南针。
渐渐地,我的生活被她的三个孩子和各自的配偶——克里斯黛尔、纪尧姆和安托万,还有他们的七个孩子——艾玛、托马斯、卡米耶、保罗、伊丽兹、艾莉丝和奥莱力所填满。他们是我们努力奋斗的意义所在。家庭是我的根,是生活的基石。我们的经历赋予了我们绝不因循守旧、随波逐流的顽强意志,让我们相信只要足够坚定、足够虔诚,一切都有可能。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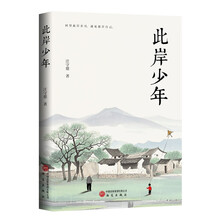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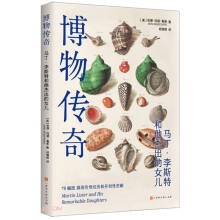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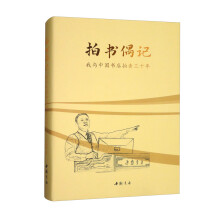

——美国《时代周刊》
与一个陷入内部分歧的德国,以及脱欧影响下的英国相比,马克龙可能是欧洲具有说服力的公众形象了。在美国退出气候协定的时候,一些人认为这位39岁的前投资银行家甚至可以成为自由世界的真正的领头羊。
——美国《华盛顿邮报》
马克龙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他发现很难摆脱“富人总统”的标签,他在去年12月的民众支持率大幅上升。这是近年来法国总统少有的一次转变。他的支持率在老年选民和高收入者中仍是zuigao的,同时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zui近有所上升。
——英国《卫报》
但在国际上,马克龙在短短6个月造成的影响力比奥朗德在5年任期里的影响力更大。如果说有一件事是马克龙成功做到了的,那就是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抗。
——英国《国务新人》
透过共和国新总统的体制变革提案,以及其中提出的未来展望,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龙效应”是切实存在的。
——法国《十字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