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回忆录》:
我也逃过学。上小学时有一次怕上数学做不出来题就逃了学,饿了就吃地瓜,晚上不回家,睡在野地里。找几个大的土坷垃,垒起来,再支些小树干,上面盖满了红薯叶子,就睡在里面。不敢回家,怕我妈打我。大概两天后熬不住了,回家去,看妈妈正在院子里引被子,很平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以为没事儿了,一溜就进屋去了。那时家里的长工叫王大个儿,我喊他王伯伯。王伯伯说:“明天早晨我带你去河里挖沙子。因为马上过年了,香炉里的沙子要换新的。你跟我去玩玩儿吧。”第二天,我满心高兴地和他去挖沙子。到了小河边,正要挖沙子时,教导主任王沧洲突然出现在河对面。教导主任喊我:“你是王明庭吗?”我说“是”,心想糟糕了。他说:“王明庭啊,你跟我走。趟河过来。”我不敢不去啊,只好趟河过去,跟着教导主任回学校去了。第二天开周会时,教导主任训话。把我叫到台上,他说:“你爸爸妈妈希望你成龙变虎。你逃学,像你这样只能变个老鼠。伸出手来!”我被打了手板。那个板子是杨木削的,打了以后痛得不得了。打了多少板子我也没算出来,就是记得痛得不敢再逃学。
四十多年后,在我第一次回老家前,教导主任还健在。我和他通过一封信,提起打板子的事儿,他还记得。他信上说:“你们这些孩子不打还行?还像个样子吗?”我回复说:“我要感谢你那几板子打得好。后来我有点成绩,就是你打板子的功劳。”可惜没等到我回乡,他便过世了。他是我爸爸简易乡村师范的同班同学。
我父亲念的学校全称是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人称“简师”。那时人们老实,取学校的名字都很本分,不像现在,连补习班都叫“学院”,动不动都是“大学”。简易师范是公费的,毕业后要当几年老师。简师对南阳当时文化教育的贡献很大。我父亲毕业后做了很多事情,做得最久的是南阳民众教育馆的馆员。我们住在县城里租的房子里,父亲走路就可以去上班。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机构的名字都显示出它们的功能。教育馆里展示着人体结构图、动植物标本等等,也有图书馆,可以借书。馆长是王新光。王新光是个画家,画画得很好,当时已经有些名气,后来因为这段历史被管制。他的女儿王临冬在1949年前去了越南,又从越南到台湾,嫁给了一起流亡的同学、研究英国历史的专家刘岱,后来去美国发展。临冬姐比我大几岁,她在台湾时我们常见面。在她的印象中,我是一个流着鼻涕、在教育馆里跑来跑去的傻小子。大陆改革开放后王新光还去过美国,他到美国发现美术界曾经的朋友们都成了大画家,都颇有建树,心里也很酸楚。教育馆前面是图书馆,也有一个小的聚会厅,后面是汉画馆。
我父亲负责管理汉画石和图书。甲骨文和汉画石是河南的两个“特产”。汉画石就是汉代陵墓的墓门、墓壁、棺椁上雕刻了图像的巨石,图像有人物、怪兽等等,有些汉代建筑里也有。刘秀是南阳人,当时的皇亲贵族死后都埋在南阳一带,因此有很多画像石。那个时候已经发现的汉画像石大概有四五百片。最早是老百姓犁地时发现的,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交到县政府。县政府怕丢,就将汉画像石镶在一个园子的墙上。园子里种着花,还有军阀石友三的题字“片石千秋”。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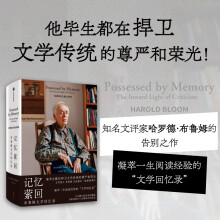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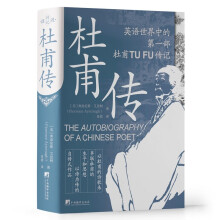
——摘自《从军记》
★我妈妈病危时,曾对她的好朋友四娘说:“你如见到我娃明庭(我的小名),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硬是彻底的绝望!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长、这么残忍的隔绝,绝对的隔绝,连书信都不通的。战争的惊心啊,小孩子不懂。到了中晚年,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悲痛。尽管从军后的六十年在台湾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顺,但想到老家、想到亲人,那伤痛是永远无法痊愈的。
——摘自《创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