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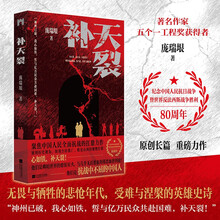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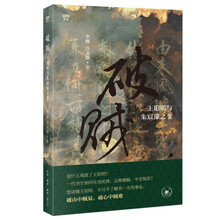

一、在这里,寻根中国
冯积岐笔下的渭河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并无二致,《渭河史》试图告诉读者的是,在渭河两岸这些虚构的村庄里生活的人们既是渭河平原这个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也具有普遍意义
二、《渭河史》,告诉你阅读苦难的价值
苦难的价值,在于给予我们感受,让我们避免成为那个狭隘的、没有同情心的自己。
保持对世界的感受力,珍重对人间的同情心。
从这一点上来说,阅读苦难是一件必须且必要的事。
三、陈忠实写了《白鹿原》,冯积岐写了《渭河史》
他是继陈忠实、贾平凹之后,陕西作家又一位领军人物
有学者预言:他将是下一位引发世界瞩目的中国作家
他,就是——冯积岐
渭河,黄河宽广、忠诚的支流,养育了两岸的人民,谱写了动天地、泣鬼神的诸般故事。眉坞县,一条河流隔开两座村庄,几段绵延不绝的家族故事,八百里有始无终的浩然秦腔,这一切犹如盘桓于中原大地的滔滔渭河,一段故事被叙述慢慢拉伸开出,拉了一百年那么长——
田方伯、罗天龙、段五魁……渭河南岸北岭的庄稼人,一生为土地而奋争,最终为土地所掩埋,这是所有中国农民的悲喜剧。渭河争滩、兄弟相煎、孝亲落草、连旱饥馑、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乱世图景上遗落的墨汁点儿大的眉坞百姓,只想保持一方宁静,在宁静的土地上耕种、收获、生儿育女。他们以为,守住了土地就等于守住了宁静的生活;他们以为,宁静像日头一样挂在蔚蓝的天空,当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们依旧不愿放弃自己对于土地美好的愿望。
第十五章
古城村又要唱大戏了。
古城村每年要唱两次大戏,一次是在正月里,一次是在忙毕——收罢麦子的时节。民国十八年和二十一年因为年馑,没有唱戏。地里收成好,就年年唱。古城村的戏楼建在村子东边的关帝庙内。
田方伯把黄姓、李姓和其他两个姓氏的长辈召集到一块儿商量唱戏的细节问题——请哪里的戏班子,唱多长时间,花销需要多少钱,等等。几个老者商量的结果是:请省城里易俗社的戏班子。唱三天四夜。至于花销,其实不用发愁,关帝庙有六百亩地,这六百亩地租给村里人耕种,庙内历年来余的的粮食有三百多石。几个老者提议,用一百石麦子的钱唱戏。田方伯提出,他捐三十石麦子的钱。田方伯的话一出口,其他几个姓氏的长辈们都很难为情——不捐吧,好象面子上过不去;捐了吧,又觉得心疼。田方伯一看,便知道,这几个老汉是怎么想的,他一再说,大家就不要捐了。田方伯这么一说,这几个老汉反而非捐不可,每人捐了十石麦子的钱。大家推选田方伯为总会长,其他几个老汉为会长。田方伯便给大家分派了活儿——谁负责招呼戏班子,谁负责采购,谁负责安全,谁负责接待各村的绅士,大家一一领了任务。
五月二十六日晚上挂灯——唱第一台戏。吃毕晌午饭,卖麻花的、卖面皮、卖豆花、卖油茶、卖臊子面、卖蜂蜜粽子、卖包子、卖锅盔的从庙门外一直摆到了古城的几条街道上。卖农具、铁器、竹器、布匹的小商贩在前一天就搭好了棚子。到了晚上,都点上了菜油灯,灯火闪闪,叫卖声悠长,十分热闹。
第一天晚上唱的《诸葛撑船》、加演折子戏《斩华雄》。开戏前,田方伯给几个会长一一交待了一下,从戏台上下来,回家去了。
进了门,田方伯一看,齐云仙还在灶房里忙活着。田方伯说,你把手边头的活放下,叫王妈看戏回来收拾,你去看戏。齐云仙说,我不去,我看门呀。田方伯说,你去看戏,今晚上我给咱看门。齐云仙说,那咋行呢?田方伯说,咋不行?齐云仙说,你是会长,会上离不开你。田方伯说,能离开,我死了,古城还不唱戏了?再说,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齐云仙说,你看看,说着说着,就管不住嘴了,我去,叫我看戏哩,又不是上刀山。齐云仙解下围腰,掂了一张凳子,走出了院门。
田方伯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走进了偏院里的喂牲口的牲口房里。他一进去,卧在圈里的牲口都起来了。田方伯点着了菜油灯,给牲口拌了一糟草,拌草时,比平日里多撒了几把料面。几头牛和骡子一边揽草,一边摇动着缰绳,好像对他表示感谢。唱罢戏,天落了雨,就要犁麦茬地了,要给牲口吃好一些。田方伯是这么想的。
从牲口房里出来。田方伯坐在了楼房的房檐上,慢悠悠地吃着水烟,慢悠悠地摇着扇子,动作缓慢,心脏的跳动似乎也慢下来了。他身后的房屋,整个院落都黯淡了,安静了,光线在夜色中暧昧了,可是,夏夜并不是漆黑一团,他能明确地捕捉到院子里的房屋、家具、树木,能感觉到天光的温和。粗犷激昂的秦腔戏不时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卖吃食的叫卖声很微弱,但很亲切,黑夜里低沉的嗡嗡声,树叶的摆动声以及渭河的涛声,隐约可见。只有在如此恬静的夜晚,田方伯才意识到他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活着。在他的内心,这时候的古城村仿佛一头卧在圈里的耕牛,安安静静的。当一村人沉浸在欢乐中的时候,田方伯独自享受着这静谧。麦上场,女看娘。忙毕,是庄稼人的又一个节日,庄稼人相互走动,传递着收获的喜悦;忙毕,也是庄稼人小聚的一个日子,亲戚、儿女、儿孙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享受天伦之乐——这时候,田方伯未免想起了河田。尽管儿子不孝,不守规矩,可毕竟是他的亲儿子。如果儿子在人世间,孙子都几岁了,他将带上孙子去后台里看戏子画脸穿衣服,孙子用疑惑、兴奋的双目看着那些还未出台的戏子……田方伯想着想着,竟然鼻子发酸了。他又装了一锅水烟。从他记事起,古城村年年唱大戏,但是,从未招过土匪的祸,土匪在这个时候不会来骚扰庄稼人的。作为族长和会长,田方伯很放心。
唱了三天三夜的戏,古城村一派祥和,而且热闹非凡。到了第四天晚上,田方伯和会长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晚上,易俗社拿出了他们的拿手戏《下河东》,戏唱到半酣,突然,一阵机枪声猛烈地响起,戏台下大乱了,看戏的人争先恐后地向庙门外跑。人拥人,人踏人,喊爹叫娘声,求救声,哭声、骂声搅成了一锅粥。田方伯失急了,从戏台子上的乐队里提来一面锣,他一边敲,一边高声呐喊: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他的喊声如渭水中的一枝柴草,即刻被淹没了。田方伯一看不行,他吩咐其他几个会长去组织年轻人,几十个年轻人不一会儿就到齐了。田方伯领着这几十个年轻人果断地推倒了关帝庙的三堵土墙,看戏的庄稼人才涌了出去。人们一出庙门,便四散而逃,那些卖吃食的摊子被惊动了的庄稼人踩了个稀烂。
第二天,田方伯听村里人说,打枪的是县自卫队和保安团的人。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来消息,说是段志松回到了古城村,他们穿着便装去段家捉拿段志松,没有捉到段志松,误伤了三个看戏的庄稼人,两个被打死了。那天晚上,在戏台下和街道上踏死了三个老汉,两个娃娃。踩伤了两百多人。
这是古城村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前一天还热热闹闹的古城村陷入了哀伤之中。田方伯把会长们叫到一起商量解决善后之事。田方伯提出,无论是枪打死的,还是踩踏而死的,都由古城村赔偿。会长们都觉得田方伯说的有道理——人都死了,还在乎那几个钱吗?其他的会长提出从关帝庙的地租中拿钱赔偿。田方伯说,这样做不妥,庙上的钱财不能动。发生这件事,我的责任最大,我太粗心,没有组织年轻人守夜、巡防,我拿五百石麦子赔偿。其他几个会长一看,田方伯自动承担责任,他们每人拿出了十石麦子。
事情了结了,齐云仙抱怨道:“段五魁真是没做好事,养了个土匪儿子,害得一村人不得安然。”田方伯说:“这事未必怪段志松,我听有人说,那天晚上打枪的不是自卫队和保安团。”齐云仙说:“那还有谁呢?”田方伯说:“可能是土匪。眉坞县的土匪有几十股子,也不知道是哪一股子。”齐云仙说:“土匪从来没有遭害过咱唱戏。”田方伯感叹道:“世事难料啊!渭河里翻船也在一眨眼间。”
田方伯迈开步子走出了古城村,走上了渭河上的木桥。木桥歪歪扭扭的,像似不来得的女人手底下的针脚一样。这座木桥是渭河南岸和北岸的人近几年自己凑钱修建起来的,一旦遇到洪水,这木桥就仿佛在水中飘摇了。田方伯从桥面上走过去,脚下发出 了空空洞洞的响声。麦子刚收毕,渭水已经很汹涌了,胆子小的人宁肯坐船过河也不敢从桥面上过去了。田方伯依然挺着胸,迈着稳健的步子,行走在木桥上,仿佛脚下昏黄的渭水是一片云团,他正在腾云驾雾,向天庭而去。
过了桥,不远处就是锣村。
田方伯是去锣村找罗天龙的。他想了又想,必须去找罗天龙,即使罗天龙冷落他,不给他面子,他也要去找。
国民党秦西省政府要在渭河南岸办一个占地三万多亩的农场,古城村、孙家塬、槐芽、街北等几个村农民的土地要被征用。县政府到各村去贴了一张告示之后,保甲长便挨家挨户通知征用的土地面积。田方伯在古城村子北边的一百亩土地要被征用。田方伯已联合了被征用了土地的几个村的大户人家或村里的绅士,准备一起进城抗征。争滩那年,罗天龙在渭河南岸得到的那三十亩地也全部被征用了。田方伯到罗天龙家去,就是想联合罗天龙一起抗征。
田方伯走进了罗天龙新建的四合院子。四周的房屋虽然是新盖的,但院子里给田方伯一股死气沉沉的感觉,四合院子的影阴倒下来全部压在院子中间,砖漫的院子里好象发出了一缕沉重的喘息。自从被段志松袭击以后,罗天龙至今元气没有完全恢复,面部的阴气很重,他一看,来的是古城村的绅士田方伯急忙拱手施礼:“稀客呀,田老兄咋有时间到河北来?”田方伯一看罗天龙很客气的样子,说道:“来看看兄弟最近咋样?”罗天龙把田方伯让进客厅,手里给他塞了一把扇子,给他泡茶,取水烟锅。田方伯吃了一锅水烟,抿了两口茶水,开门见山:“今天来找兄弟,是为了农场征地的事,不知兄弟是咋想的?”罗天龙说:“还能咋想?这伙狗日的和段志松是一个球样子,明伙执仗的抢人地。一亩地只赔一石谷子,这和抢人有啥区别?不知道河南的弟兄们准备咋弄?”田方伯实话实说:“我已把几个村的人联合好了,准备进县城找县长。”罗天龙说:“就像民国十九年那样去缴农?”田方伯说:“这次去,咱不吆车不拿农具,咱在渭河滩上拉上十几车石头,把县政府门给他堵了。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去?”罗天龙说:“你这话咋说出口呢?你小看我罗木匠了。不要说是我自己要丢三十亩地,就是锣村任何人的地,也不能叫他们白白的讹去。咱是庄稼人,咱的每一分地都来的不容易。”田方伯说:“实话给你说,我来的时候,心里还没底,还真不知道兄弟愿意不愿意干这悬悬的事。和政府对着干是要挨洋锉的。你这么一说,我打内心里服你罗木匠了。”罗天龙说:“兄弟不是没向况(德行)的人,这你知道。你田老兄能高看我,我还怕啥呢?咱们进城去闹,闹他个渭河倒流,他们把我拉去五马分尸,我也情愿。”渭河北岸和渭河南岸两个村的绅士第一次把话说在了一块儿,第一次觉得彼此都很高大。
六月十四日清晨,田方伯和古城、孙家塬、街北、槐芽等几个村的绅士们一起带领着六七千庄稼人,罗天龙带着锣村的上千口人从不同方向涌向了眉坞县县城。他们把拉来的石头沙子倒在了县政府门口。一个年轻小伙子举起手高呼:“县长出来!”后面的农民跟着喊叫。“我们要土地!”“我们要活命!”呼喊声不绝于耳。县长张源东一方面叫自卫队去弹压,一方面派人去齐家寨把段志松的队伍拉过来——张源东的这一手是很毒的,他知道,段志松的那六七十个人中大多数是渭河南岸的人,叫他们回到县城来自己对付自己人,看他们究竟怎么办?这是一箭双雕的事情。
段志松接到命令后向县城赶,他只知道县城里发生了骚乱,不知道这些人大都是渭河南岸几个村的庄稼人。等赶到县城,段志松一看那些闹事的庄稼人,感到很棘手,这些闹事的人,大都是他的弟兄们的亲人。他的弟兄们怎么能向自己村里的兄弟叔伯们开枪呢?尽管,他们抢劫富人时杀人不眨眼,那毕竟是在黑地半夜里干的事,他们抢劫的对象都是财东,和自己的弟兄们不沾亲带故。他就是有豹子胆,也不敢对六七千庄稼人开枪。县自卫队的队长命令他开枪,段志松把自卫队长拉到一边说,这么多人,咱可不敢轻易下手。我去找县长,叫他亲自下口喻。段志松借口找县长趁机溜走了,段志松的那五六十个人名义上是国民党的队伍,要叫他们开枪打自家的叔伯兄长,他们绝不干。自卫队长一看,他指挥不动段志松手下的人,自卫队的队长就命令自己的人开枪,枪一响,前边的十几个庄稼人倒在了血泊中,段志松的弟兄们一看,打倒在地的全是他们的亲人,他们举起枪,朝自卫队的人开了枪,双方打起来了。田方伯指挥着他的人抬上打死的或受伤的庄稼人撤离了现场。段志松手下的人和自卫队的人对打了一会儿,段志松手下的人撤走了。
县自卫队开枪打死了五个打伤了十三个庄稼人。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第七部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他在闷着头却又是义无返顾地进行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体验的实践,既不轻易吹牛式的表态,更不向任何时兴的流派靠拢,而是执意要创造出自己艺术理想里的长篇小说景观。
——陈忠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冯积岐是我陕西省一个重要作家、优秀作家,因为他的创作在新世纪以来,不但没有衰落,反倒很坚挺。他在陕西作家里是吸收现代小说成分较多的一位,而他又是极传统写作的一位,他的写作是用心写的,事关痛痒,是一个不断追求的人,他的思考不停止,包括社会思考、艺术思考。他是有几套笔墨的人,写实写得很到位,人物刻画得细腻动人;议论则有哲理,闪动着泥土一样的智慧;抒情又出乎意料,有诗人气质。
——贾平凹(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