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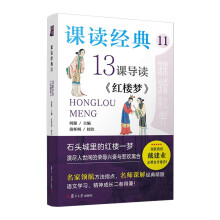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白痴》是他的重作品。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白痴》的读者还是观众乃至读者兼观众,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将十万卢布一捆钞票扔进壁炉付之一炬,恐怕任谁的心灵都会经受一次强烈的冲击。这一堆烧钱的烈火,象征着陀氏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不仅在星光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当之无愧地堪称经典。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白痴》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描写19世纪60年代出身贵族的绝色女子娜斯塔霞常年受地主托茨基蹂躏,后托茨基愿出一大笔钱把她嫁给卑鄙无耻的加尼亚。就在女主人公的生日晚会上,被人们视为白痴的年轻公爵梅诗金突然出现,愿无条件娶娜斯塔霞为妻,这使她深受感动。在与公爵即将举行婚礼的那天,娜斯塔霞尽管深爱着公爵,但还是跟花花公子罗果仁跑了,最后遭罗果仁杀害。小说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上层社会作了广泛的描绘,涉及复杂的心理和道德问题。善良、宽容的梅诗金公爵无力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也不能为他们造福,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的徒劳努力,表明作者企图以信仰和爱来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白痴》:
“是啊,人家说我相貌比较年轻。至于怎样可以不妨碍您,我很快就能学会,很快就会懂得的,因为我本来就很不喜欢妨碍别人……。还有,我觉得从很多方面看来……我们是大不相同的人,恐怕我们不可能有太多的共同点;然而,最后那句话我自己并不相信,因为往往只是表面上看来没有共同点,其实共同点很多……。人们光看外表把他们自己分成不同的种类,看不到任何相通之处,这是人们的懒惰造成的……。不过,也许我已经开始讨人嫌了吧?您好像……”“我想问一句:您有没有钱财,哪怕是一小笔?或者,您是否打算从事某项工作?请原谅我如此冒昧……”“不必客气,我十分欣赏和理解您提的问题。目前我没有任何钱财,暂时也没有任何工作,不过应该做些事情。我花的是别人的钱,是在瑞士给我治病、指导我学习的施奈德教授给我的路费,也只够路上花的,所以现在我剩下的钱总共才几个戈比。是的,我有一件事情需要跟人商量,可是……”“那么请问,眼下您打算靠什么维持生活?您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设想?”将军截住了他的话头。
“我想找些工作。”“哦,原来您是位哲学家;不过……您是否知道自己有什么才具、本领?大小不论,只要是能换衣食的一技之长,有没有?我再次请您原谅……”“哦,您不用道歉。不,我认为,我既没有才具,也没有特别的本领;相反,因为我是个病人,所以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至于衣食问题,我觉得……”将军又把他的话打断,又提了一些问题。公爵把已经讲过的情况又讲了一遍。却原来将军听说过已经去世的帕甫里谢夫其人,甚至认识他本人。帕甫里谢夫为什么关心公爵受教育的事,连公爵自己也讲不清楚,——不过可能纯粹由于跟他已故的父亲是老朋友。双亲去世时留下的公爵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他一生都在乡下度过,在乡下长大,因为他的身体需要乡下的空气。帕甫里谢夫把他托付给自己的亲戚——几位女地主;先为他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后来换一位男教师;公爵说,他虽然什么都记得,但很少几件事能讲清来龙去脉,因为很多事情他自己不理解。经常发作的癫痫把他弄成了一个白痴(公爵确实用了“白痴”这个词语)。最后他讲到,帕甫里谢夫有一次在柏林遇见了施奈德教授,这位瑞士人是专门研究这类病症的,并在瑞士的瓦莱州设有机构,用他的冷水疗法、体操疗法既治痴呆,又治癫狂,同时对病人施教,全面指导病人的精神发展。于是,帕甫里谢夫大约在五年前把公爵送往瑞士教授那里去,可他自己两年前突然死了,事先并没有作好安排。施奈德让公爵在他那里又继续治疗两年,尽管没有彻底治愈,但毕竟大有好处。最后,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加之还冒出一个新情况,现在教授把他送到俄国来了。
将军大为惊讶。
“您在俄国没有熟人?一个也没有?”他问。
“暂时没有,但我希望……而且我收到一封信……”“至少,”将军没有听清楚末了那句话就打岔,“您是否学过点儿什么?比方说,您的病是否会妨碍您在某个机关里担任某项并不繁重的职务?”“哦,想必没有妨碍。要是能有个职务,我甚至非常欢迎,因为我自己很想看看自己究竟适合做些什么。我曾经连续学习四年,尽管不太正规,而是按照教授的一套特别方法学的,同时还读了好多俄文书。”“俄文书?这么说,您是有文化的,能正确书写?”“哦,完全能够。”“太好了;书法怎么样?”“我的书法出色当行。在这方面我也许有才华;我简直是个书法家。请让我马上给您写点儿什么试一试。”公爵劲头十足地说。
“那就偏劳了。这甚至是必要的……。我喜欢您这种直爽的态度,公爵,您的确非常可爱。”“您此地有这么讲究的文房用具,有这么多铅笔、鹅毛管笔,有这么结实、上好的纸张……。您的书房真是太漂亮了!这幅风景画我知道,这是瑞士的风景。我相信画家是实地写生创作出来的,我相信我见过这个地方——这是在乌里州……”“完全可能,尽管这画是在此地买来的。加尼亚,给公爵一些纸;这是纸和笔,请到那张小桌子上去写。这是什么?”将军问加尼亚——他刚从公文包中取出一张大尺寸的相片递给将军。“啊,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这是她——她自己派人送给你的?”将军热切而又十分好奇地问加尼亚。
“适才我去道贺的时候她给的。我早就请她送一张给我。不知这是不是她暗示我在这样的日子空手前去,没带礼物。
”加尼亚脸带苦笑添上末了那句话。
“不,不,”将军很有把握地打消对方的疑虑,“你怎么想到这上头去了,也真是!她怎么会暗示?……她完全不是那种贪财图利的人。再说,叫你拿什么去送礼?那是要花成千上万卢布的!难道你也回赠一张相片?对了,我倒要问你:她还没有要你送相片给她吗?”“没有,还没有要过;也许永远不会向我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您想必没有忘记今晚的聚会吧?您是在特地邀请的客人中间的。”“没有忘记,当然没有忘记,我一定去。今天是她二十五岁的生日,怎么能不去!嗯……听着,加尼亚,我来向你透个信儿吧:你得作好准备。她已向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我许诺,今天晚上将在自己家里宣布最后的决定:是或者不!所以你得注点儿意。”加尼亚忽然着了慌,甚至脸色都有些发白。
“她的的确确是这样说的吗?”他问的时候声音好像颤动了一下。
“前天作的保证。我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一起缠磨了好久,总算逼了出来。只是她要求先别告诉你。”将军定睛注视着加尼亚;见加尼亚慌成这样,他显然有些不悦。
……
总序
正文
译后记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