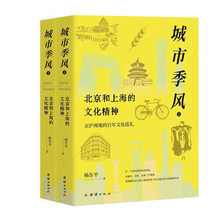《新民说 鹅城人物志》:
陈石
《城市之光》编辑部的办公室分里外两间,那些年来,陈石一直坐在外间右侧的窗下。书似青山常乱叠,在他的办公桌上层峦叠嶂的却不只书籍,还有文件、照片、名片、药片、光盘、盆景、手套、围棋子、烟灰缸、硬币与钞票、一盒快发霉的望海茶,以及横行无忌的蟑螂等。保洁阿姨见此,不由职业病发作,屡次准备出手,都被陈石断然拒绝。有一回趁他出差,保洁阿姨花了大半个小时,才把鸡窝一般的办公桌收拾干净,从中翻出的零散钱币,加起来约有三十元,换来两个洞桥八戒西瓜。不想翌日陈石回来,看到纤尘不染的办公桌,竟不落座,反把保洁阿姨找来狠狠训斥了一通。我与他同事一年,只见他两次发脾气,这是第一次。
不出一周,陈石的办公桌便恢复原状。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他的棒球帽上,阴影遮住了半张脸,紧绷的嘴角愈显凌厉。他端坐于明暗之间,往往半日不发一语,静默如石佛。每次办公室的小可走进来,都要惊呼:陈老师,您入定了!
2007年立夏,我第一次推开《城市之光》编辑部的门,见到的陈石,便是如此光景。2008年夏天,他离开杂志社,我拍了一张照片留念。形容憔悴的他蜷在电脑椅中,静默如故,浓浓的倦意从他身上弥漫开来,身后错落的书堆,仿佛随时都会倾倒。
那时编辑部除了陈石,还有两位诗人:一个天天给政府部门及官员写赞美诗,一个天天给鹅城大学一个属兔的女生写情诗,二人互为读者,并在网上使用马甲相互吹捧。陈石不胜其烦,不过依他的性格,却也只能沉默。
我进入《城市之光》编辑部,恰因两位诗人先后离职。主编为了省钱,遂压缩编辑部的人力,令两个人负担三个人的活。月底开例会,我抱怨不堪重任,提议招人,面如满月的主编呵呵而笑,却不表态。陈石正在纸上乱画,抬头白了我一眼,忽然打了个呵欠。主编急忙道:散会,散会。
陈石出身《鹅城日报》,熟谙体制与办公室政治。他对世情常有极明澈的洞察。至今我犹记得他的两个论断。有一次谈及主编喜欢摆谱,他说,其实最爱摆谱的人,一是领导的秘书与司机,二是财务人员——这不是狐假虎威,而是权力的代入感在作祟。还有一次,我俩去采访一位贸易局的官员,那厮递来的名片上面密密麻麻,这个长那个长,大约有十来个显赫的头衔,其职务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号,标明行政级别:副处级。回到办公室,陈石把官员的名片丢进垃圾桶,笑道:看一个人的名片,头衔要是超过五个,此人便无足观矣,真正的大人物,名片往往十分简单。后来听说,虞洽卿的名片仅七字:浙江镇海虞洽卿;宋霭龄的名片仅三字,即其名。
陈石从来不用名片。由此可知他的为人:世事洞明,却不趋于流俗。2002年,他从鹅城大学中文系毕业,即被招入《鹅城日报》,据说是名人推荐,社长特批。彼时日报门槛高不可攀,一般非硕士不要,本科则非名牌大学新闻专业不要。鹅城大学不过二流,它出产的本科生能被日报垂青,不啻是天赐的福分。可惜,对此福分,陈石毫不珍惜,弃若敝屣。他在新闻部仅仅工作一载,便自我放逐,调到了组建不久的鹅城网。原以为远离了指令与红包、废话与谎言,办公室生活会安逸一些,哪知鹅城论坛的日常运作依然要周旋于政府的禁令与网民的怨言之间,左支右绌,两头受气。半年后,他直接挂断了宣传部的指示电话,随即递交辞职信,只写了五个字:老子不干了。
回忆记者生涯,他说写文化新闻比写政法新闻更令人恶心。他曾推荐我读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针尖上的天使》,书中一位记者的话,道尽了他当年的不堪:“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离开鹅城网之后,他去北大旁听了两个月的课,结果无比失望:北大已经不是他从纸上读来的那个自由、开放、圣洁的北大。回到鹅城,他致信授业恩师、鹅城大学中文系的剡教授,述说苦闷,剡教授回邮,言辞恳切,建议他放弃理想主义的高蹈,回归地面,物来顺应。他给我看过那封邮件,解释道:我不是理想主义,我只是有所不为。这句话,如今我常常引用,以掩藏自己的犬儒。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