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到尼采(第3版)》:
基尔克果的吸纳具有“清除1800年,就好像它们不曾存在过”、内在地与原初基督教“同时”的任务。但是,这只有在自若干世纪以来就现存的基督教由一个普遍的历史的现实成为一种各自独特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一种“公设”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以这种方式,上帝当然成为一个公设,但并不是在人们通常接受这个词的那种休闲意义上。毋宁说变得清楚的是,一个实存者进入与上帝的一种关系之中所采用的惟一方式就是,辩证的矛盾带来绝望的激情,并以绝望的概念帮助(信仰)把握上帝。这样,公设绝对不是任意的东西,而恰恰是紧急自卫,以至于上帝不是一个公设,而实存者公设上帝则是一种必然性。”
与此相反,基督教字面意义上“绝对的”、完全客观的真理是无法把握的,因为他的绝对性的“关节点”恰恰在于对他的“绝对态度”之中。与此相反,基督教历经1800年的客观持存“作为赞成的证明”在裁定的时刻“等同于零”,但作为“否定的惩戒”却是完全“出色的”。因为如果真理就在吸纳中,那么,基督教的客观有效性就仅仅意味着它相对于我自己所是的主体的无所谓性。
但是,在对真理的这样一种规定内部,如果妄想和真理都能够证实同样的“内在性”,那么,人们应当如何还在二者之间作出区分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热情的反基督徒是“真的”,并不多于也不亚于一个热情的基督徒,但是,任何别的实存激情作为激情也都已经有它的真理。基尔克果清楚地发现这种两难处境,但却只是以注释的方式付诸言表。他用一种限制来保证自己的命题,即人们必须把“无限性”的热情的内在性与单纯“有限性”的内在性区别开来。但是,真的可以据此来区分内在性自身吗?基督教内在性的根据不是其自身,不是根据其主观性,而是其对象,是上帝的无限性。但在这种情况下,无限性的内在性,即对上帝的激情态度,却只是鉴于上帝,从而是违背自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限的激情才可以与这样一种对某有限物的、作为激情的态度而是一种妄想的态度区分开来。与此相反,如果激情中的实存确实是“终极者”,是“消失着”的客观的东西,那么,一般来说在有限的内在性和无限的内在性之间、从而也在妄想和真理之间作出区分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事实上,当基尔克果把真理设定在内在性之中的时候,他就得出了这一结论:“当客观地追问真理的时候,也就在客观地追求作为一个认识者与之相关的对象的真理。追求的不是关系,而是它就是真理,就是他与之相关的真东西。只要他与之相关的东西是真理,是真东西,那么,主体就处在真理之中。当主观地追问真理的时候,也就在主观地追求个人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如何是处在真理之中的,那么个人也就是处在真理之中的,即便是他与非真理相关。”
如果重要的“仅仅”是个人“与某物”如此相关,以至于他的关系在真理中(即主观地)是一种与上帝的关系,那么,是否有一个上帝存在,就必然是无所谓的了。沿着这条通向真理的道路一在那里,道路自身就已经是真理了——在客观性方面所能够达到的最极端的东西,就是“客观的不确定性”。因为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是否是客观的,即从上帝方面来看是否是一种真的关系,人并不能自己来确认。对于一个信仰中的“实存者”来说,最高的真理恰恰是在各自的吸纳中的客观不确定性。因此,按照基尔克果的说法,一个人尽管事实上崇拜一个异教的偶像,也可以“在真理中”向上帝祈祷,而反过来,一个人虽然在一个基督教的教堂中崇拜真正的基督教上帝,也可以“在真理中”向一个偶像祈祷。因为真理是“内在的”如何,但并不是“外在的”是何。但由于对基督教的主观性来说重要的不是任一“某物”,而是真正的基督教,而且对它来说,只要真理不应当是妄想,重要的就必须是基督教,所以信仰的真理就不仅仅在于主观的吸纳,而是在于这种吸纳“坚持”“客观的不确定性”自身。因此,信仰的客观性虽然不是就自身而言,但却作为一种拒斥性的客观性对于独特的吸纳的真理而言是建设性的。二者共同使信仰成为“悖谬”。“如果内在性的主观性就是真理,那么,这种主观性客观地来规定也就是悖谬;而真理客观地是悖谬,这恰恰表示,主观性就是真理,因为客观性是排斥性的,而它的这种排斥或者他的表述就是内在性的张力或者测力计。”…因此,主观性是通向就自身而言永恒的真理的真正道路,但这种真理在与~个实存者的关系中却必然是悖谬的,并且仅仅以从自身排斥的方式是向自身吸引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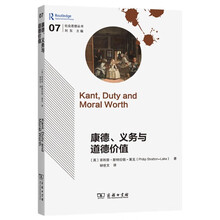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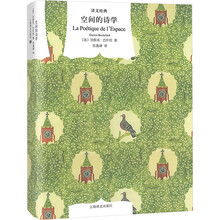








——列奥·施特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