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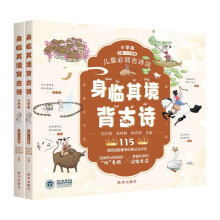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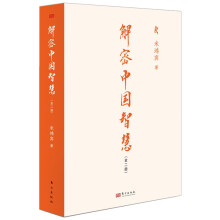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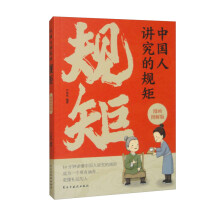







1. 围绕华夏制度文明,回溯儒学的源头,深挖先秦儒家思想精髓。周振鹤、刘强、鲍鹏山、吴钩等一致推荐。
2. 呈现一个全面立体的先秦儒家思想体系。全书分为“政论”“经济”“文化”三编,从孔孟原典出发,全面剖析先秦儒家的政治、经济、刑罚、福利、统筹分配等制度构建,尽可能展现先秦儒家思想为解决政治文化问题所提供方案的全貌。
3. 主题新颖,理趣不凡。围绕原始儒学的核心精神,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并且发人深省的观点,比如:臣子并不总是将君主视为最高价值;储蓄思维能够启发教育,是家族经久不息的重要条件;劝酒的实质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灌酒不是礼,而是礼崩乐坏的产物。
4. 知识结构开阔,汇通古今中西。从经济学、法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切入,将古今中外的知识、文化、思想等融会贯通,深化和开拓了“原始儒学”话题的探讨。
5. 揭示原始儒学精神对于滋养现代文明的时代意义。回溯先秦时代原始儒学的源头,挖掘其现代意义与生活价值,凝练原始儒学旨在实现个体完善与社会和谐的精神与举措,为当代婚姻家庭、市场分工、社会救济等问题提供借鉴与养料。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在阅读过程中令人一会儿抓耳挠腮,一会儿又拍案叫绝的有趣小书。抓耳挠腮是因为深深地被它的内容吸引,被来自两千年前至今不衰的争鸣与论辩激发得百感交集;拍案叫绝是因为书中有许多脑洞大开的观点,加上幽默诙谐的论述,可以启发许多新知。
这是一场激发想象力的知识之旅。初翻目录,可能会惊讶于孟子与打地鼠游戏之间的奇妙联系,或是禅让与汤武放伐的惊人相似,甚至是传统文化对食肉的推崇。别急,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类比,正是本书魅力所在。这本书从孔孟原典出发,融合了古今中外各种知识与理论,兼容并包,只为肃清“原始儒学”的本来面貌。
在这个创意与规范并行的时代,我们渴望阅读那些能够激发思维、拓展视野的佳作,却又往往对创新之作持保留态度。这本书将向你证明,好书是敢于突破常规、引领思考的。它不仅能够激发你的理解力和联想力,更会以文化史论的深度,锻炼思辨性。本书的核心议题“爱有差等”,乍看之下似乎颠覆传统,实则深藏玄机。很多人将墨家的“爱无差等”误解为儒家理论,忽视了《孟子》此句中紧跟的“施由亲始”——从最关心、最亲近的人开始实践,激发恻隐之心。到底理想的爱的序列是什么样的?就请大家跟着本书,去一览先秦文明的缤纷色彩吧。
围绕华夏制度文明,回溯儒学的源头,深挖先秦儒家思想精髓。全书分为“政论”“经济”“文化”三大部分,从孔孟原典出发,融合多学科知识,归纳并阐述先秦儒家对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主张,全面剖析了原始儒学在政权组织形式、刑罚、税收、资源分配以及社会福利等多维度的制度构建。作者认为孟子的爱有差等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不仅深入挖掘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还特别强调家庭、家族和社区在文明社会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揭示原始儒学在铸就现代文明制度方面的深远影响和滋养现代文明精神的重要意义。
文章探讨了古代中国对最无助个体的救济问题,强调了孟子关于仁政应优先救助鳏寡孤独的观点。在古代,这类个体主要依赖家族和社区的救济,但当失去这些支持时,他们就变得极为脆弱。孟子认为,仁政应从救助这些最无助的人开始,而周文王时期的政策也体现了这一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在救济这些个体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官僚机构也出现了弊端。孟子主张适度的国家介入和税收,以确保既能提供救济,又不会过度增加社会负担或导致政府机构过于庞大。
——编者按
“哀哉鳏寡”:首先拯救最无助的原子个体
在古代社会,社会救济更加依赖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而人一旦在小共同体领域出现缺失,成为没有父母、配偶、子女的原子个体,虽然也可能得到更外围共同体如村社之类的救济——如《诗经·小雅·大田》:“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就描述了周代村社共同体将田地中的稻穗留给寡妇,这就是村社共同体对不幸个体的救济方式。但是,丧失了亲人成为了血缘意义上的原子个体,在当时看来是属于最悲哀的类型。在孔子的时代,没有兄弟的司马牛为此忧虑不已:“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这些不幸者没有“家”,是最悲哀无告的群体。孟子谈到,有四种人最悲惨,所谓“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梁惠王下》),即老年没有配偶、儿女的男性、女性,以及幼年没有父母的孤儿,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人共同体,以社会边缘人和原子个体的身份悲哀地生活,是这天下最需要帮助却没有话语权的“穷民”。孟子指出,周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是先从拯救这四种最无助的弱者开始。顾炎武曾据《诗经》、《越绝书》等文献考证,“有妻而于役者,则亦可谓之鳏”,“有夫而独守者,则亦可谓之寡”(《日知录》卷三十二《鳏寡》)。按照此说,“鳏寡”还包含了因为服役而被迫分离的人们,也是需要得到救助和呵护的人群,也是一种“穷民无告者”的类型。
这四种“穷民”,古人一般省略作“鳏寡”二字代之即可,对于鳏寡不幸的怜悯与关注,在早期华夏时代就是一个重要话题,并被持续关注。周初的《尚书·康诰》中就强调了“不敢侮鳏寡”,不许欺凌这些无告的弱者。类似的语言,也见于西周时期的《毛公鼎》铭文,所谓“毋敢……侮鳏寡”(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表明这是西周时期政治观念中常见的思想。类似的表述,还见于其它一些西周青铜器铭文,如周宣王时期的《四十三年逑鼎》铭文说“虽有宥纵,乃侮鳏寡,用作余一人咎,不肖唯死”(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3期,第20页),李学勤将其读为“乃敢侮鳏寡,用作余我一人咎,不雀死”,意思是欺凌鳏寡者,将“不保官雀(爵)而死”,不但会丢官,还会丢命(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载《文物》2003年6期,第70页)。
在清华简《摄命》中也记载,周孝王在册命仪式中告诫领主贵族,一定要做到“亦勿敢侮其童,恫瘝鳏寡,惠于小民”(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西书局,2018年,第110页)。“恫瘝”即《尚书·康诰》中的“恫瘝乃身”,即孔传所说“如痛病在汝身”。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周王要求领主不能欺辱鳏寡和孤儿,要将他们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属民。降至东周时代,照顾鳏寡的思想仍然得到继承,山东滕州庄里西村出土东周编钟铭文有“哀矜鳏寡”之句(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金文集成》,齐鲁书社,2007年,第104页)。这件编钟,也就是“司马楙编镈”,铭文云“曰古朕皇祖悼公,严恭天命,哀怜鳏寡”(张振谦《司马楙编镈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342页)。这位东周贵族赞美自己的祖先悼公,具有恭顺天命的美德,其中重要的品质便是哀怜和照顾鳏寡。显然,他想表达的潜台词还包括,自己也继承了“哀怜鳏寡”这一古老的家族美德。
从这些周代的金文和竹简材料来看,对于鳏寡为代表的那四类“天下穷民”的悲悯与关照,是早期华夏文明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主题,上至周王下至士大夫也都在努力践行对鳏寡的哀怜与照顾。孟子主张行仁政要首先拯救鳏寡之民,并且宣称这是周文王之政,显然不是自己脑洞大开的产物,而是对此前古拉漫长历史价值维度的继承与发扬。孟子要用王政的力量来拯救最无告之民,这就意味着,在原始儒学中,对于福利和救济手段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必要的国家手段这一内容。原则上来说,原始儒学主张小而强的政府,大量领域被交给各类小共同体,如家族、宗族、村社、乡党之类。在孟子的想法中,通过“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的小共同体互助手段,基本是可以实现互助与社会救济的,国家的触手不需要介入其中。但凡事皆有例外,对于孤儿、鳏寡之类丧失了“家”这一根本核心共同体立足点的边缘人,他们其实已经沦为了某种原子个体,虽然能得到外围村社共同体“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的帮助,但仍然是高度脆弱和无助的。在这种特例下,这些“无告穷民”就需要王政,即国家必要救济手段的介入。
实际上,从后世史书来看,汉代以来朝廷对孤贫不能自存者进行不定期的救济,成为了一种习惯。诸史的“本纪”部分,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从《汉书·文帝纪》以来对“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的“振贷”开始,给“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给谷物之类成为一项长期不定期的制度习惯,见于各代史和帝王诏书。对于鳏寡的救济,也一直是历代发政的重要内容,如西汉于定国的治理就“务在哀鳏寡”(《汉书·于定国传》);北周时苏世长上书周武帝,“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新唐书·苏世长传》)。发展到宋朝,这种从孟子和原始儒学思想中发展出国家对鳏寡孤弱的救济,开始衍生出发达的国家福利制度,也因此导致了带有“现代性”的福利病。北宋以来普遍设立救济孤弱的养济院、慈幼局、施药局、居养院、安济坊之类大量官办福利机构,可以说在儒学人道主义精神下发展出的宋朝救济体系,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其动机当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良善。但是和现代社会一样,经由官僚机构层层过手都是油水的各种福利制度,很容易成为官僚或相关代理企业的“项目学”套钱手段,做成利益寻租链条,宋朝福利制度就已经初显端倪。“诸县奉行太过”、“縻费无艺”、“资给过厚”之类情况十分常见,增加了税收负担,即所谓“常平所入,殆不能支”,甚至导致“不养健儿,却养乞儿”的民谚嘲讽,用现代话语说就是“养懒汉”。所以,国家或官僚机构对福利的介入过深,也是存在陷阱的。
通过孟子的思想和宋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哀哉鳏寡”的救助,除了传统各种小共同体的救助之外,肯定也需要一定国家力量的介入,即孟子所说“文王发政施仁”,但是这种介入又需要审慎和明确的限度,警惕其可能存在的“项目学”陷阱,一旦过头也是过犹不及的。那么国家必要限度的规模,应该大致按照怎样的比例设置较为合适?如果按照一些“奥派”的观点,连“守夜人”规模的小政府国家设置也是多余的,甚至连警察和公共安全秩序这些都可以用私企“安保公司”之类来进行替代,人们通过向各类私企“公司”购买安保等在内的商业服务就可以了。这种思路的出发点,固然为了避免官僚机构的弊端,以及官僚机构的各类寻租利益链条,是为纳税人的钱包着想,但却忽略了无力购买各类“商业安保服务”的那些诸如“哀哉鳏寡”之类的人群。一些“奥派”可能会说,这是基于财产权的“正义”,不同人有不同结局,你无权为了拯救“哀哉鳏寡”去侵犯别人的财产,这样最后一路走下去一定是强权官僚制。
如果脱离现实历史经验,将这个作为一道纯粹的智力游戏论述,只要加以精致化,不但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进入历史语境就会意识到,原子个体意义上的“财产权”预设是站不住脚的,智人二十万年以来的“自发秩序”恰恰是属于某种共同体的,早期时候属于某个家族或部落,近五千年来则出现了超越血缘部落组织之上更复杂的共同体,如早期国家和族群,近几百年还出现了“民族国家”这种庞大体量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安全以及对内部弱者的救济,从历史经验和二十万年以来演化出的智人本能情感来说,都是带有公共性的,不是简单的两个原子个体之间的关系。孟子不需要像罗尔斯那样,首先预设“无知之幕”可能成为“哀哉鳏寡”得需要得到救济,也不需要假设出诺奇克那样沙漠中只有一汪泉水,然后启动洛克限制条款之类的玄思,他的论述其实更多基于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朴素现实感和常识感。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对“哀哉鳏寡”的救济如果更多通过各类小共同体肯定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这一点笔者也表示同意。但即使是在传统社会,也有很多类似司马牛处境的人,所谓“人皆有兄弟,我独无”,李密说自己童年作为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儿,其凄凉孤苦也是普遍存在的。传统的小共同体,虽然也有宋代四明“乡曲义庄”之类资助家族外人群的救济机制,但主要还是以“范氏义庄”之类救济本宗族血缘人群的为主,因此即使是在早期国家的周文王时代,也要通过一定国家手段的介入来救济同属于华夏人群的一些“哀哉鳏寡”,那么就必然涉及到收税的问题。
孟子主张的国家规模,并不是以最低税率为最善。《孟子·告子下》中,白圭就主张一个极小规模税收能力和规模的国家,即“二十取一”来征税。孟子主张的税收能力比白圭方案高一倍,主张“什一而税”。他批评了那些类似现代“奥派”的观点是“貉道”,即回归到国家出现之前的部落状态。据学者考证,“貉”是靠近北方燕地的胡人部族,又称“蛮貊”、“夷貊”、“四貊”等,代指周边非华夏的散乱族群(林沄:《说“貊”》,《史学集刊》1999年4期)。在西周《貊子卣》铭文中,记载周王赏赐给貉人一个首领“貊子”三只鹿(《集成》05409)。这表明,“貉”这样原始扁平的部落状态,虽然也有小范围的首领,但却没有真正发育成熟的国家机制。
政论篇
爱有差等与文明的构建 003
孔门是模拟周代封建关系组建的小共同体 015
存亡继绝:保持众多平行延续的世家 030
缔结婚姻:从小共同体习惯法到近代国家登记048
三年之丧礼与小共同体 054
孟子与混合政体的“打地鼠”游戏 060
性善论:为小共同体自治的辩护 068
古儒认为忠君并不很重要:兼论《忠经》辨析 078
独立于君权的专业性 085
儒学是鼓励平民模仿做贵族的学问 094
天命和民意 110
禅让和汤武放伐其实是一回事 114
经济篇
“哀哉鳏寡”:首先拯救最无助的原子个体 123
父亲角色、婚姻、家庭和市场经济是文明的基石 130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140
孟子、森林使用权与习惯法 150
孟子谈社会分工与市场 156
孟子与自由贸易 163
恒产恒心:克服时间偏好 171
文化篇
朋友:从血缘、姻亲到跨血缘 183
劝酒:从贵族礼仪、自治社区的酒会到服从性测 190
家庭、乡土熟人层面应保留方言 199
传统文化:吃素还是吃肉? 206
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 216
原始儒家的阳刚之气 222
率兽食人和始作俑者 229
先秦战车:外来的技术 237
秦朝尊重女性?你想多了 244
文字和书写的力量 250
后记 259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